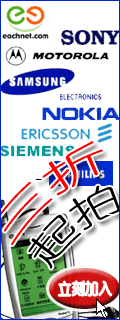|
撰文/包同曾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2001年9月下旬的北京,金风送爽。由驻英使馆教育处组织的“留英学者高新技术代表团”,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展项目发布和洽谈活动。
当我赶到会场时,发布会已经开始了,留英学者们正依次报告着他们各自的项目。在 代表团印发的精美的《留英学者高新技术项目手册》里,我看到了崔占峰教授的名字,他是这个代表团的顾问、留英高新技术项目评审专家及评审委员会主席。由这几个头衔,我想象得到,为筹备这次回国服务的活动,崔教授付出了多少辛劳。
宽敞的报告大厅里响起了掌声,我看到崔占峰教授神采飞扬地走上讲台。又一次看到那熟悉的手势,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与他在英国的一次次交往之中——
“崔占峰,河北任丘人。1978年本科毕业于原内蒙古工学院化学系,后在原大连工学院化工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他到英国做博士后研究。1991年3月在爱丁堡大学任讲师。1994年10月到牛津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Reader(类似副教授)。2000年10月1日,38岁的崔占峰被牛津大学正式聘任为工程系化工专业教授。此外,他还是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法人成员,英国国家工程委员会特许工程师(CEng)。主要从事膜分离、生物加工和组织工程等研究。”
从这份不能简单得再简单的履历中,我们足以看出此人的不简单了。而且必须说明的是,崔占峰教授是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教授,也是目前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说起来,我与留英学子中的这样一位佼佼者,是很有缘分的。1997年9月到驻英国使馆教育处工作不久,就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他。以后,我们多有来往,成了朋友。
记得是我第一次独立带着一个国内考察团参观牛津大学。同事帮我约了一位向导(是位学联干部),说好在工程系楼前会面。我既不认识他,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因为觉得不会有问题。但当我们来到工程系时,却没见到人。
当时是10月底,秋风已经有点冷了。考察团员们坐在车里,我则焦急地在车外来回转悠。这时,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短风衣,个子高高的,年轻的脸上英气十足。在英国,我是不敢随便认老乡的。因为即便一幅中国人的样子,也不排除礼貌地回答你:“我不是华人。”或者即便是华人,也是“我不会说汉语”。但这个人主动向我打招呼,说从车牌号码,知道我是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并说他是从国内来的,与教育处有过很多联系。他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使我顿生“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我急切地说明困境,并询问他是否认识我要找的那位学联干部。他认识,并说到办公室后,马上打电话联系。说着,他就依然是匆匆地走了,我们都没有来得及互通姓名。
过了一会儿,那位学联干部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并一再地为记错时间迟到而道歉。他告诉我是“崔占峰博士”打电话通知他的。我才知道,那位仅一面之交、但好心而守信的同胞的尊姓大名。
我们的向导还告诉我,这位崔博士可不得了。他是牛津大学正式聘任的Reader。能得到大学的聘书(因为各系也可以聘任,但层次显然不同于大学聘任的),在中国留学生以至所有的华人中都是凤毛麟角。
第二次见到崔博士,是在转过年的使馆春节招待会上。我们邀请崔博士与他的夫人出席,但是,他陪着他的老父亲来了。他说,父亲来英探亲,有个愿望,就是看看咱们国家的大使馆。来人的爱国之情一下子感染了我。我对老人说,您的儿子很争气,学问作得非常好。老人很高兴,讷讷地说:“多亏了领导栽培。”饱经风霜的脸上,全是忠厚和朴实。
就是在那次招待会上,崔博士一边殷勤地照顾着父亲;一边简单地跟我述说着他的身世。从那朴实无华的言语中,我看到了一位中国北方憨厚的读书人,从黄土地走来,在异国他乡耕耘,并已登堂入室,在世界的学术前沿奋斗。我清楚地感觉到,那淳朴的话语里充满了机智,那执著的目光时时有闪光。
以后,我们曾多次在留学生的活动中见面,有几次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次,是在1999年中国留学生学者化学学会的年会上。那次,我目睹了讲台上崔博士的风采。
作为主要报告人,崔博士介绍了他的研究领域以及与国内有关部门合作开展科研的情况。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桌上,轻松地走到听众席前,侃侃而谈,挥洒自如。时而是标准的普通话,时而是流利的英文。专业上我虽然一无所知,但与会者的关注,说明着他讲演的博与深;一个个与国内合作项目的具体内容,我不甚了了,但中国科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等熟悉的名字,使我知道崔博士为国家办事,是实实在在的。在这次大会上,他获得了本年度“为国服务奖”。也许这个奖项与他1993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工程院授予的“全英高校青年讲师奖”和1999年获得的“英国皇家工程院工程预见奖”,在学术价值上无法进行类比,但它是崔博士那颗拳拳报国之心的最好证明。
还有一次,是在与国内教育部、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一个考察团的座谈会上。由三部委组成的这个考察团是来英了解和研究英国发展基础科学研究情况的。我们邀请了几位在牛津大学工作的优秀留学人员与考察团座谈。座谈会就在崔博士所在的KEBLE学院举行。暮霭沉沉之中,我们来到了供院士使用的高级会议室。在牛津、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中,院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有各自使用的活动室,严格分开,等级森严。由于崔博士在学院中的地位,我们才有可能在这里开会。会议室布置得典雅华贵,古色古香。一张硕大的椭圆形木桌摆放着舒适的软垫圈椅。在水晶吊灯和烛状壁灯的映照下,墙上一幅幅风景油画仿佛也在发出暖暖的柔光。在那次座谈会上,与会的几位学者对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受到了考察团的高度重视。崔博士反复强调,应当提倡“求实、创新”的学风。他介绍了牛津大学在组织开展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许多建议,充分表达出了那种希望尽快把我国科技事业搞上去的急切心情。
在我离任前夕,崔博士邀请我们夫妇到KEBLE学院出席“高桌晚餐”,为我们送行。当时,他已经正式受聘为牛津大学教授。在高桌上,我们夫妇与崔教授边吃边聊,话题就从“教授”开始。崔教授向我们介绍了牛津大学的“教授席”。在牛津,一般一个专业仅有一个“教授席”(有的一个系只有一席,大系也不会超过10席)。这些“教授席”,是由王室钦定的,或者由某个基金会(或个人)捐赠而命名的,也有的是由大学自己设立的。全校仅有120个左右,不超过全校教员的10%。所有的教授都由大学遴选、聘任。公布聘任教授的名单时,须注明就任哪一个教授席。一经聘为教授,除非本人辞职或退休才能由他人接替。名额既少,任期又长(基本上是终身制),竞争当然激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优中选优,自不必说。以崔占峰博士38岁的年龄,再加上中国人(无论有无歧视,不是本国人总不会占上风)的背景,能够得到牛津大学“教授”的聘书,那种难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那您的薪水一定是天文数字吧?”我夫人不客气地问道。
崔教授告诉我们,他作为教授,年薪是3.5~4万英镑左右,而且还要交税。由于他是属于大学聘任的教授,不能再在学院任导师,也就没有了学院的那份薪金。这样,他的薪金收入还不如当Reader时高。
“那当这个教授有什么好处?”我问。
“教学量小并且自主,”崔教授肯定地说。“在牛津大学,当了教授,学术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就可以更自主地在你的研究领域内做些事情。自己作老板,自己说了算。这对于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于是,崔教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他在自己的化工领域中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事情,其中特别谈到了他要为中国做的事情。那真是丰实溢于言表……
那次,在“高桌晚宴”后,我们还参加了传统的品酒聊天。我以前就听说过这种海阔天空的恳谈,往往会持续到深夜。不知有多少科学的创意和思想的闪光,就是在这种交谈中产生、迸发出来的。我就坐在KEBLE学院的女院长旁边,女院长问起了我中国的教育、来英留学人员的情况,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崔教授。她由衷敬佩他的学识,称许他的为人。她说,他是我们的朋友。
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秋雨,红红的火苗在壁炉里摆放着。看着崔教授与他的同事——那些学富五车的院士们,高谈阔论、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从心底生出一种自豪感。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的一位教授——他是中国人,他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博士!同时,那流洒在窗棂间的秋雨,使我忽然想起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诗句。是啊,不论做出了多么大的成绩,不论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誉,崔教授,他会与千千万万的海外学子一样,永远玉壶冰洁,心向祖国。
……
报告还在继续。崔教授这次带回来的项目是“水及废水处理过程中膜技术的应用”。项目的主要特点和效益是:“开发新一代膜分离技术及装备,应用于饮用水的净化及工业废水的处理。解决农村地区清洁饮用水的供应问题,以及工业污水排放读环境的污染问题。”仅仅从标题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项目的价值;从“饮用水的净化”、“工业废水的处理”等等一大堆“水”字中,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项目提出者那一片“玉壶冰心”了吗……
每月2元享用15M邮箱 中大奖游海南游韩国
| ![]()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