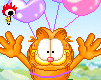| 西行漫记:我在美国的室友们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11/23 10:35 太傻网 | |
|
这是一篇反映美国青年真实面貌的短文,读读这样的文字,可以提前领略一下异域的风 我在萨马维尔镇珍珠街10号的室友凯特和威恩在塔夫特医学院的考试结束了。考完试,一身轻松,凯特带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开车来到波士顿北区,那里原是意大利移民聚居的地区,停了车,走进一条边街,步上阶梯,一扇木门,木门上有镀铜的花瓶饰,十分雅致。我们去的是凯特的一个叫爱默莉的同学的家。房间小巧,一个客厅,中间是厨房 嗨,男子汉,接住!......越过嘈杂的人头,从空中飞来一罐百威啤酒,好家伙,这跟飞越大西洋有什么两样。幸亏我以前练过篮球,易拉罐不偏不移,“叭”地一声落在手心中。爱墨莉在远处笑着,一转身,随着CD唱机的音乐,扭着腰肢,又给别人去倒可口可乐了。这一间一套的寓室到处回响着她的笑声。她是这群医科大学生客人的皇后,是理应笑的。 “嗨,谁去买意大利匹萨饼?” 爱默莉拿出一个小本本,是意大利匹萨饼连锁店“意大利第一”减价奖票。大家掏腰包拿钱出来。殷勤的骑士到处都有。迈克尔,一个卷发的英俊青年,拿了减价奖券和钱去汉诺威大街去买匹萨饼了。 “我不喜欢这张U2的歌,换上一张布鲁斯·斯帕林斯汀的吧。”米契尔说,全身扑在沙发背上,伸手要去换唱片。这姑娘很矮,穿一双高统白塑料靴子,是从纽约买来的。 布鲁斯的歌,《生在美国》,一丝哀怨和怅惘,这是对美国梦的信仰么?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改善他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背景如何,你只要努力,你就能在美国获得成功——好一个美国梦。 雪白的冰箱门上挂着一份日本挂历,与对面墙上一幅中国电影招贴画相映成趣。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却酷爱东方的东西。 “爱默莉,你认得这字么?” “我不认识,我是把它当成是一种艺术。” 东方的字是一种艺术,绝妙的见解! “那钩子是干什么的?”我问,指着白色天花板上的一个铁钩子。 “干什么?”她又哈哈大小起来,“任何人干越轨的事儿,就在那儿吊死他!” “越轨的定义是什么呢?” “哈……” 大家聊啊,笑啊。到了11点钟,青春的精力似乎还没有发泄完毕,大伙儿开上各自的汽车又往“天佑”大楼楼顶酒吧去。沿街霓虹灯的灯光,红的,绿的,桔黄色的,演变成一个个连续的点,映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一闪而过,接着又是无穷的光的色点,变幻着不同的怪异的轨迹。坐电梯登上了74层楼。酒吧墙面全是玻璃,波士顿全城就在你眼下,一条条桔黄色的街灯,像放射出去的光弹,伸向远处渺茫的黑夜之中。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成了小孩手中的玩具一般,行人极细微,跟忙忙碌碌的蚂蚁差不多。俯视下的夜色中的波士顿成了一个奇怪的闪着光的几何图形。明白了吗?为什么有现代派的艺术?那是现代生活怪异的视野和体验的产物。 凯特,一头金发,魁梧壮实,给我买了一杯果汁加威士忌的鸡尾酒,一个古怪的法国地名。他是威尔士人的后裔,当别人穿毛衣时,只穿一件短袖凯弗斯特日带汗衫,好一条汉子。饮酒的桌子隐放在黑暗里,只有玻璃窗外射进来的光和酒柜处微弱的光影,这些大学生们围着桌子又聊起来了。 酒吧的另一端是舞池。舞池上面有一盏摇曳的灯,在舞池上扫出红﹑黄﹑白﹑绿的光。人的脸,服饰,头发,似乎都变得在梦中一般。摇滚乐,迪斯科,疯狂的音乐,爱默莉,凯伦——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姑娘,如琳——一个在美国出生的越南姑娘,米契尔,凯特,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鼓点扭着,跳着,追逐着,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融化在这音乐所造成的疯颠的忘我的境界之中了,仿佛他们真的“携带着威力,自由,大地,大自然的能量,健康,轻蔑,快乐,自尊,好奇”。这些舞着的男女使我想起我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见到的德加斯的雕塑《舞者》的美,从手到脑袋,到那滚圆的臀部再到腿的线条是那么的流畅而饱含生命勃发的力。 下了楼,已经是半夜一点钟了。 在大楼前广场上分手时,我在阑珊的灯下问爱默莉:“你一生的梦想是什么?” “幸福。”很干脆,几乎不假思索地。 她希望个人幸福,社会幸福不就是千百万人的个人幸福组成的吗?她已经有了许多人为之羡慕的幸福,她还向往一生都幸福。有谁会拒绝给这么一个无辜的﹑可爱的﹑达观的姑娘以幸福呢?祝福她吧。 在白雪覆盖着一切的中国除夕之夜,我去了哈佛大学的纪念大厅,一色的黑发、黑眼珠、黄皮肤。中国人,多叫人感到亲热。然而,我又感到那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那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国式的,美国式的旋律。在摇滚乐五彩灯下,黑发的男女青年在狂跳,屋外是零下十五度,室内是衬衫﹑牛仔裤,脸上是汗珠和欢乐的红光。 有一天,凯特和韦恩从学校上课回来,神秘地对我说:“我们今晚要让你瞧瞧美国式的派对是什么样的。” 凯特开上雪白的雪佛莱车一溜烟似地走了,回来时从“星星超市”搬上楼两大桶充气啤酒桶和一些炸土豆片。啤酒是派对的拳头,吃的东西却寥寥无几,这是与中国式的好客不同。没有几个冷餐拼盘,不炒几个菜,能算请客吗?别忘了,这是学生,美国学生的派对。他们大多数上学的学费都是从银行贷款来的,背了一屁股的债,美元有一点儿,但也不多。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穷开心”。 开派对,门就得大开,什么人都欢迎。凯特和韦恩把二楼的起居室和三楼的开阔的楼道都安上了立体声喇叭和适合跳舞的灯,灯不很亮,但一切都还能瞧见。 到晚上九点钟,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什么勃隆代斯大学的,哈佛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新罕布希尔州立大学的,布朗大学的,认识的与不认识。据说,美国人参加派对,越晚越好,叫做“honorably late”。这对我可是一件新鲜事。 起居室音乐一响,人们就开始“摇滚”起来。爱默莉来了,凯伦也来了,还有如琳,这越南故娘总是眯眯地笑,有那么点儿冒儍气。俄裔的后代索尼亚烤了一种墨西哥食品,叫塔可铃,玉米粉做皮,包之以牛肉末、洋葱、奶酪、西红柿和莴苣。韦恩用菠萝汁﹑木瓜﹑甜酒﹑冰淇淋﹑自来水做了一种叫“热带鸡尾酒”的饮料。不跳舞的人们就聚集在厨房里,边喝啤酒边聊天。来自加州的开文这小子很精,在啤酒桶旁边占了个有利位置,就是一个劲儿地足喝,按他的说法,这不是“喝”,这只是“租”啤酒,啤酒喝下肚,要不了多时就排泄去,这不是“租”吗?真有意思! 我走上三楼,那情景那才叫人乐呢。凯特,大卫,爱默莉,光了脚丫子,随着音乐,从东蹦到西,又从西蹦到东,活象在炒蹦蹦豆似的。这些美国人好像永远不知道疲倦,就这么蹦啊蹦啊,喝啊喝啊。 啊我精神的欢乐 —— 打开了牢笼 —— 它像闪电一样飞窜! 只有这个地球和某一段时间是不够的, 我要有千万个地球和整个时间。 惠特曼,啊,生气勃勃的惠特曼啊,我受到感染,也和他们一起蹦起来。这时,我只感到一中极端的欢乐,把世界上的一切忧虑忘却,跳舞,拍手,雀跃,呼喊,就这么蹦,到一个永远年轻的世界去。 文/朱世达 (编辑:飞语)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留学出国 > 出国系列之风情篇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