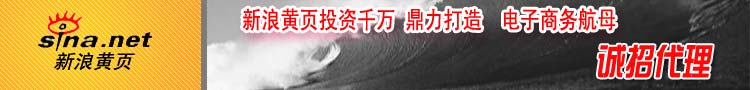
|
|
|
|
出国留学必看:一个失败的留学样本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23日 11:06 中国青年报
尽管有一次不成功的留学经历,李清曦心里还会经常冒出一股“不知哪里来的清高”。回国已经两年多了,不时还会有很多情景和细节,勾起他对澳大利亚的回忆。 2002年,18岁的李清曦中断高中学业,告别父母师友,独自去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后,他疲倦地拖着一个箱子回了国,里面没有文凭,没有居留证明,甚至连在国外买的衣服,也统统没有。里面只装着一个陪他度过大半留学生活的游戏机。他变成一个“海带”(海外归来的待业青年),前途一片渺茫。 经过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将自己的留学生活写成一本书—《别了,澳大利亚》,在书里,他坦言自己留学生活的诸多过失和悔恨。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留学失败者大有人在,而李清曦被视为第一个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人。他自称“脸皮比较厚”,因此不介意成为其他要出国的同龄人汲取教训的样本。不过说起有些事情来,他仍旧会支吾,怕“丢人”。 他的行文透露着孩子气,经常会忍不住在一句话后面打上括号,注上“嘿嘿”这样的语气。他反复问记者,封面上的作者照片帅不帅,如果考虑再版的话,换一张什么样的好。 甚至有读者坚决不肯相信,这名看上有些稚嫩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也听说,已有家长拿着他的书对孩子说,你可别学他这样。“看来我的目的达到了!”李清曦有些得意。 出国留学“太简单了” 2001年,李清曦的父亲几乎毫不犹豫作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决定。而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国外教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古典的校园,很小的课堂,只有十几个人,自由而活跃,周围全是老外的面孔,大家在一起用英语交流学习。”当时,这名不满18岁的高二学生,通过《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各种杂志,在脑海中模糊地构建起国外留学的幻象。 “我很讨厌中国学校的教育方式。”李清曦说。因此,这种幻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除此之外,他对出国留学一无所知。 “想过出去该是什么样子吗?”有人问他。 “太简单了,就像在国内一样,就是学习,不用想别的。”出国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李清曦,想象中的留学就像去一所国外的高级中学。 “多数中国孩子对国外留学生活的想象,都被笼罩在一个由虚假信息创造出的描述里。”他后来反思。虽然现在留学梦破灭了,他却仍然对自己想象里的那种生活感到羡慕。“那样的生活一定曾经有过,只是我们这一批人没赶上。” 而李清曦的父亲李洁,决定送儿子出国的理由更是简单。 “潮流。”他使劲憋出这个词儿来。然后,他开始扳着手指算,不到一分钟,就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不停顿地说出十几个同事的名字。在2002年前后,这些人全都先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 李洁只是感到身边有一股小留学生的潮流在涌动,可事实上,这股潮流早已在更大范围里汇聚成了汹涌洪流。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数量已占到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南方一些城市,办理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甚至占到所有出国人员的70%~80%。 “我生活的圈子里,送孩子出国的,不夸张地讲在80%左右。”李洁说。而他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商界朋友,孩子也多在国外。这让他“几乎不用选择”:有点钱,又有这样一个交际圈子,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要出去的。 还有一个“自私的念头”,李洁没有跟儿子说:希望儿子能移民国外。“那样我老的时候,还可以有个投奔的地方。” 至于儿子想不想出去,以及出去以后是否能够适应,他并没有过多考虑。 在国内也算“见多识广”的李洁,对国外的留学生活同样很陌生,除了同事零星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一名把孩子送出去的同事,成了李洁主要的信息来源。 高一的期末考试刚结束时,李清曦一家请这名同事聚餐,主要目的是请教一些出国留学的情况。 “太简单了。”这是他们得到的信息。这名同事轻描淡写地转述着他所知道的“留学信息”:国外和国内没什么两样,呆下来很容易,读完语言,随便就能念大学;学费不用愁,找工作很简单,想打工就打工,赚得是比人民币值钱的澳元,绝对能养活自己。 这番话说得李洁心花怒放。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过去对国外留学的误区,主要来自这名同事转述中介公司的介绍,以及儿子在国外“报喜不报忧”的电话。其实他完全不了解儿子在国外的真实境况。 李清曦回国以后,在书里也写到父亲这名同事儿子的生活:他为了赚够生活费,甚至三天只睡8个小时。 既然一切被描述得这样美好和简单,李洁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立即开始替儿子办手续。不过这一切,李清曦并不知情。直到半年以后,高二只读了一个学期的李清曦得知,签证已经批下来,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国了。 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李清曦的母亲一度坚决反对儿子出国。她的理由是,儿子从未独立生活过,出去以后肯定“管不住自己”。 从小到大,李清曦的生活和学习完全是在父母管制下度过的。那时的他和同龄人一样,听话,努力学习,生活规律,没事喜欢关上门玩电脑游戏。 在生活上,他也有着同龄人共有的“低能”。在出国前不久,家人让将满18岁的李清曦去邮局寄一封信,他都觉得心里“发怵”。不过,这些并未能动摇父亲的决心。 “那个时候,他的确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把他送出去,是早了点。”李洁反思道。他自称,当时完全被一种憧憬和期待所支配,对自己的儿子认识“不够清楚”。 在很多事情上都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出国的日子临近了。李清曦特意把行期定在自己18岁生日那天。他“豪情万丈”,觉得广阔的未来在等着他。“属于我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他在书中写道。 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未来到底怎么个广阔法”。 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 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李清曦甚至不会填写自己的入境申请表,多亏临座一个陌生人帮助才对付过去。 澳大利亚给李清曦的第一印象,堪称完美。 在此之前,他和父亲李洁对这个国家主要的信息,都来自网络和一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面写着这个国家简略的历史。而现在他可以用眼睛亲自打量这个国家了:天空是从未见过的蓝,空气很新鲜, 别墅掩映在花丛绿树里,路边栽满花草。“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生活,不是像在天堂里一样享受吗?”李清曦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第一堂语言课就击碎了他的梦想。 走进教室前,他又一次想象起自己向往的留学生活:一个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学校,班上只有一两个留学生,课堂气氛浓厚,课下气氛活跃,身处英语的环境…… 结果,他看到了“一张张黄种人的脸”。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且都讲汉语。 “你好,你从哪儿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用标准的普通话问他。然后,大家继续用汉语聊天。 “也许只有这个班是这样吧?”他有些疑惑和懊恼,但心存侥幸。 结果,下课以后他发现,在喧闹的走廊里,除了几个外国面孔的老师外,几乎全是中国人,男女分堆,大声嚷嚷。 除了校园环境优美,这里和他在国内的高中竟然没什么不同。当然,也有区别,男孩子坐在阳台上大大咧咧抽烟,没有老师来管。 他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楼层,也许在高中或大学预科班,情况会好些吧? 答案同样让他失望。他最终发现,这家学院里,97%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剩下的是一两个日本人、一两个韩国人和四五个中东人。中国人互相很少讲英文,而是用搀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交流。李清曦有一个韩国同学,英语不大会说,却会用发音标准的汉语骂人:“我操你妈个×!” 而李清曦也“收获不小”。在这里,从小说普通话的他,却从青岛老乡那里学会了青岛话,甚至还学了一点南方话。有一次通电话,他爸爸李洁甚至听不出这是儿子的声音。 总之,来之前的所有期盼,一下子落了空。他懵了。 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 想病多久就病多久 在国内上高中的惯性,让刚到澳大利亚的李清曦憋足了“好好学习”的劲儿。不过他很快发现,环境变了。周围的小留学生,大多都是在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老师,除了讲好自己的课外,其他的方面很“尊重”学生的选择,听不听课,甚至来不来上课,他们都不太在意。 虽然这所学校对出勤率也有要求,可是身边大多数中国小留学生,天天逃课,不写作业。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很快,李清曦洞悉了这些小留学生的一些“小把戏”:找当地华人医生开假诊断书。“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想病多久就病多久”,只要交了钱,这样一份像模像样的诊断书,就可以成为他们逃课的借口。 而为了钱,这些华人医生已经把开这种诊断书,当成了常规生意。 另一方面,一些澳大利亚语言学校的校方也在纵容,只要留学生们交够学费,就放任自由。李清曦的一个朋友,出勤率只达到了5%,远远低于规定的80%,却丝毫不妨碍他继续留学。 这样的结果是,很多小留学生出国以后,读了几年的语言,英语水平依旧很蹩脚。有一个小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读了一年多英语,平时不上课也不交作业,结果迟迟不能毕业。 有一次,他给学生顾问送去了400多块钱的茶叶“意思意思”,对方很高兴地接收了。结果,这次贿赂还是没能让他通过考试。 李清曦觉得,中国小留学生把太多的坏习惯带到了国外,并因此成为外国人很看不起的一个群体。 比如,澳大利亚的地铁,经常没人检票。据他所知,很多中国小留学生都会借机逃票。 还有一次,在一辆巴士上,他和几个中国小留学生大声地用中文说笑,忽然,一个外国老人很不高兴地用英语大声呵斥了他们。这一声呵斥,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会刻意提醒自己保持安静。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清曦逐渐开始放松自己,他不再坚持听当地英文广播,也不再费力地去搜想英文单词表达,而是开始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直接用中文交流。 他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学到的东西也过于简单。直到如今,回忆起当时的上课内容,他还会把头向上一扬:“那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东西。” 过去在国内堆积如山的作业不见了。每天,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作业,然后给自己留下大段的空余时间。 这个18岁的男生感到寂寞。电脑游戏和聊天成为他闲暇时间的主要陪伴。 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并非只有他一人 滞留澳大利亚26个月,李清曦总共花费,超过了20万元人民币。不过,李洁后来偷偷问过送孩子出国的家长,他们都认为,“你儿子花得并不算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英读中学的中国小留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就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即使去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学酒店管理4年也要花掉30万元。而在李清曦出国前后的几年里,一份调查称,送子女出国的家长如同“背上了高利贷”。以新西兰为例,每个小留学生每年最少要花费16万元。而在加拿大,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要拿到学士学位一般需要5年半到6年半的时间,每年至少需要12万元人民币。 “我的父母不是贪官,也不是大款。”李清曦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境。尽管他的父亲李洁声称,自己供得起儿子在外读书,但省钱仍然是李清曦留学生活的一大内容。 小留学生的家境多半不错,但巨富毕竟很少。一名留学的青岛女孩说,即使是国内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很难为子女在国外提供比较奢华的生活。除非有钱人家的子女,才能几天换一辆车,住比较昂贵的学生宿舍,这都是他们这些人不可企及的。 许多小留学生在外面过的日子并不安逸。李清曦的一位好朋友,迫于生计,只能四处找工作,最潦倒的时候连个面包都买不起,只能饿肚子。为了挣够学费和生活费,他同时兼几分工,连续几天不睡,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办公室趴一会儿。 而在国外打工,也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名曾在德国“飘”了两年最终空手而归的小留学生,因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去铺地板,赚钱买饭吃。 当然,也有些小留学生为了能过上奢华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中国小留学生参与的抢劫、绑架案件,时有耳闻。 李清曦选择的“生钱之道”,是传销。像许多涉世未深又渴望赚钱的孩子一样,他狂热地被发财梦控制,交钱入伙,好友怎么劝他都不听。那时,他认真记笔记,背诵产品资料,虔诚地向“上线”请教真传,然后,不停地邀请同学做自己的“下线”。后来干脆直接到人家住处进行“推销”,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最终,李清曦付出了近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才从中抽身而退。 等他醒悟过来之后,他才知道,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远非他一人。他的室友和他一起进入传销组织。而他的另一个好友,后来也被骗进了这家组织,任凭他苦口婆心劝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还是太小。”他感慨。而这些事情,当然也不敢跟家长说。他花巨款在传销组织购买的“微量元素”,后来托人带回国,当作孝敬父母和长辈的礼物。 打电话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时,李清曦在电话这边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没有妈妈叫醒起床了”。他想家想得厉害。那天,他一口气给父母、亲戚、同学等十几个人写了信。 最初,给家人打电话被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周日的下午,他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向父母简单汇报一周情况。 大多数小留学生和家人的联络,都只能通过电话。因为国内拨国际长途很贵,所以,多数电话都是由小留学生从国外打过来。 一开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比如最近的学习、学校演讲比赛的结果,等等。但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就没话说了。 “每次打电话他们总是会问相同的问题,像能不能吃饱,钱够不够花,学习紧张不紧张等。”李清曦逐渐开始学会应付。 “报喜不报忧”,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数小留学生惯用的方法。他们习惯用一连串“挺好”来回答家人的所有询问。 结果是,很多家长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挺好”:不错的住处,不错的食物,不错的学校,还有不错的前途。他们要做的,就是按时把钱打到孩子的账户上。 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以前干什么总要被管着,现在好容易离开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想再听唠叨。”李清曦说。这也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共同想法。 最长的一次,李清曦有近两个月没跟家人联系。当时,他和几个小留学生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天玩游戏,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根本想不起打电话这回事,更怕打通电话家人听到这边的声音会“露馅儿”。 那一次,可急坏了家人,他母亲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里多次这样想。 他实在是被“过于残酷、高度紧张的”国内高中教育束缚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样经历、一样年纪的小留学生,聚到了一起。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与女友“煲电话粥”,开销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课时就睡懒觉,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从上课变成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他的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晚上玩游戏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坐在床上玩。有一个星期,因为下暴雨,他干脆整周呆在屋子里玩游戏。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回忆起这一天,他总是会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摇下头,然后又笑一下,好像在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尽管这样的失败者,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 上个月,几名从小认识、后来到不同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这些人,有的在国外漂了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最后回国;有的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正在国外读研究生。 他们一起畅谈起自己的留学见闻,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一个男生打趣儿地对李清曦说。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赌钱、不犯罪,只是玩玩游戏。”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没读完时,便去了德国留学。尽管两次进出德国,但他始终连一所正规的语言学校也没读过。 吃喝、游戏、打工,构成了他在德国的生活内容。他的身边,同样有一批混在德国的小留学生。 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他总是借机避开。实在被追问急了,才说出他认为去留学的最大收获:他知道了柏林墙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从柏林墙往哪个地方走有个公共厕所”。只有在闲谈中,他才会偶尔透露一些他留学时打架的细节。不过这些,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了语言。 另一名叫顾云(化名)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新西兰的“身份”。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例子。不过这个过程却很坎坷。尤其使她难忘的,是她3个月的“黑民”经历。 所谓“黑民”,就是没有签证留在该国的外国人。在几名小留学生接触的人群中,“黑着”的人并不在少数。顾云是因为遇到了黑中介,所办签证不是正规签证,而被迫做了3个月的“黑民”。 不过,3个月后,她通过找关系,重新办了签证。用小留学生的话说,这叫“洗白”,而洗白并不那么容易。王洋的两个同学,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国家,等待该国“大赦”,那样就可以摆脱“黑民”身份。结果没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许多小留学生,因为出勤率等原因签证被注销后,往往不敢跟家人说,选择“黑”在国外,按时提取父母寄来的学费,提心吊胆地活着。 “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为了骗父母,会把自己说成在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读书。”王洋说,“在国外,要编造谎言骗家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为得知签证被注销的那一刻,他曾经犹豫做不做“黑民”。“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真那样选择了,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他说。 最终,他选择了与移民局打官司,并最终胜诉。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力再继续自己的留学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选择了回国。 在他身边,还发生过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却在路边看到儿子正陪着别人逛街。 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外欠下巨额赌债,最后偷偷卖掉一个肾还债。回家后一直身体虚弱,家人带他做检查才知道真相。 卖淫、吸毒等有关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在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妖魔化的传说,现实中切实存在着这种现象。顾云所在的市,曾经连续发生过多起中国小留学生杀人绑架的案件,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她身边。 个别小留学生甚至在国外包养暗娼。曾经有小留学生为了斗富,放假时乘飞机到香港红灯区“潇洒”一番,然后带着照片回来比试,看谁找得“更靓最嫩”。 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 在青岛市区的某个路口,来往车辆并不多,李清曦不断左右顾盼。远远开来一辆桑塔纳轿车,他顿时收住脚步,很有耐心地等车过去,才快步近似小跑地过了大约5米宽的马路。 “我已经进步了。”他仿佛在解释。刚从澳大利亚回国时,过马路成了李清曦最紧张的一件事。他只敢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 父亲李洁当时的印象是,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那时候,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过马路要紧紧拉着他的手才行,“有时候手心都出汗”。 李清曦怀念澳大利亚人车互让的交通秩序,并对一切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为深切反感。为了是否从斑马线过马路的问题,一次,他和一个回国后关系很要好的女孩子闹翻了,以后很少再来往了。 同样让李清曦不习惯的还有很多。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坚持要父亲系上安全带,并为此很不快。而在途中,一名同车的人将塑料袋随手扔出车窗,他当时就跟人急了。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多少已经改变了他。“天怎么这么灰?空气怎么这么差?”对着青岛的环境,他不住地抱怨。 有时候,他觉得烦躁,就会不住地用头撞墙,一边大吼,过了很久之后,他才有勇气对父亲李洁承认,“他想过死”。 他下意识地觉得高人一等。在 出租车里,他会故意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跟同学聊天。等着司机问他“你不是本地人啊”,然后,他会得意地说:“我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会的”。回国以后,李清曦曾经试图重新参加高考,但他发现,国外接受的教育,已让他无法再适应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了。 听了补习班老师讲课之后,他愤而离去:“这哪是教学生啊,这不是在毁学生吗?”然后,他开始向人絮叨国外的教育方式。“人家小学的时候,是要学木匠这些手工课的。我们哪里有过?” 结果,他开始参加自学考试。 现在,他在青岛一家文化单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十分认真。他已经能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留学的经历。用他的话说,“留学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让人生也失败”。 偶尔,他和爸爸李洁会一起交流留学得失,然后一起感慨:那时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经历。”李清曦说,不过他补充,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在国内读完一所大学之后,再选择出国。“那时候自我约束力就会强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样的人,实在不少,只是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敢公开说出来。 事实上,他当初身边接触到的11个小留学生里,有9个人已经回来了,而且只有极个别的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都没有念完大学。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连自己的“糗事”也不遮掩。他希望当个“反面教材”。 “有点丢人,”他说,“不过……没关系。”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