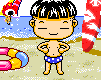| 我的英国导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4/27 14:04 《留学生》 | |
|
文/李庄 2001年来美国之前和Crocker教授互通Email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个特别和蔼的人。他总是用I would like,would be这样非常客气的句式。从他的网页上我了解到,他是英国人,60年代的博士,是奥本大学现在的三个distinguished professor之一。他在照片里慈祥地微笑,唇上的胡须修得整整齐齐。这让我想到《虎口脱险》里那个大胡子机长走出 当年五月份我到北京开会,遇到从美国国家仪器公司回来作报告的钱世锷博士。我们讨论了些技术问题,就聊起我来奥本念书的事情。他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是振动和噪声控制。他便反问我知不知道Crocker教授。我惊讶道:“他就是我未来的导师呀!”他于是说:“Crocker教授是个英国绅士,为人特别nice。”--钱世锷博士的这个评价让我非常高兴。因为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的学校、联系教授,常常是两眼一摸黑,如果不是美国这边有人帮助,谁也不知道这边导师的脾气禀性,然而导师无疑是留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自那之后到现在,我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用nice这个词来评价老先生。这个词虽然简单,却难翻译,因为它包含了“和蔼”、“客气”、“亲切”、“善解人意”、“考虑周到”等等意思,又是一个“好”字难以概括的。听说他以前有个学生学位没拿,找到工作就拍屁股走人了,但是没多久又被解雇了,没地方去,大胆老脸要回来继续念书,我们老先生还是收留了他。 来奥本之后上起课来,我发现他特爱用反意疑问句。比如:“We didn't cover this part, did we?”或者“It is better, isn't it?”这令他的语言非常生动,而且反意疑问句弱化了语气,好像他什么事都是和你商量,而不是教训。有一次留作业的时候,他甚至问:“May I give you some homework?”弄得我们大家都非常不好意思。而交作业时,他反而对我说:“Thank you。” 老先生治学甚是严谨。这首先体现在他批作业上。即使只是解题过程中少写一个单位,他也会给你指出,而且总有些非常精辟的建议,比如怎样怎样也可以,怎样怎样会更好。有时就连单位的写法,比如“分贝”要写成dB,而不是db,单位缩写时和不缩写时应当注意什么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他修改我们的论文也极为仔细。我对英语很多小地方的感觉不好,比如什么地方用冠词,什么地方不用冠词,都被他指出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到美国国家沥青中心去做实验,在车上说起英语中的冠词。他说,一般情况下冠词使用还是比较随便的,其实美国人说英语很多该用冠词的地方都省掉了,但是科技文献中除了标题和图表的说明,一般都不省略。我写的论文每一稿都被他修改得红红绿绿,有很多地方还用荧光笔画出来,连字体、字号都一一订正。这也许是他多年来作《噪声控制工程杂志》和《国际声学与振动杂志》主编养成的习惯。这对我的英语写作大有帮助。比如十以下的整数都要拼写出来,而不要写成阿拉伯数字;公式和符号说明都要用斜体;缩写、单复数怎么正确使用,等等等等。 老先生偶尔会流露出来英国人的优越感。他有时会批评美国人的英语,比如data这个词本身是复数,但是很多美国人都把它当单数用。他说,这是个拉丁词,欧洲人懂得拉丁词多一些。还有一次他提起剑桥大学机械系的一个教授,流露了一点英国人对爱尔兰人固有的偏见。他说这个教授虽然是爱尔兰人,但是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 我们系的一个中国师姐说有一次Crocker教授当一个硕士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问题提得特别尖锐。那学生还是个女孩子,一个回答不上来,两个回答不上来,到后来都快哭了,干脆说:“不知道。”本来一般硕士答辩也就一小时,但是这个答辩会延长了很长时间。当天有一场重要的球赛,大家都急着回去看球,于是另一个教授就打圆场,说:“又不是博士答辩,差不多行了,大家都要回去看球呢。”Crocker教授沉默了一下,说:“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名教授就是这样,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眼光特别敏锐。别看他对你的研究不太了解,但总是能够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经常恰恰是答辩者薄弱的地方。 Crocker教授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发表的论文数百篇,写的书也有十几本,其中包括主编《声学手册》和四卷本《声学百科全书》这样大部头的书。平时老先生除了主编《国际声学与振动杂志》之外,还是国际声音与振动学会的执行主席。我有时候收到他凌晨三四点钟写的Email,心里不是滋味,就主动帮他做些事情。 刚来美国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个博士生和两个访问学者,一共四个中国人,到Crocker教授家里包饺子。他家中养了只黑猫,他说这是他们家的“总统”;他家门口上面结了个很大的蜘蛛网,他说这蜘蛛是他“朋友”。聊天当中他忽然拿出一张照片来给我们看,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他八十年代初在上海交大的毛主席像前面的留影,可笑的是他居然戴了顶绿军帽,帽檐下的笑意透着他英国人的幽默。当他从沙发里站起来的时候,几枚硬币从口袋里掉出来,他夫人说:“这是我的小费。” 当天晚上看到的他的收藏让我兴奋不已。首先是一本厚厚的收藏夹,当中是李斯特、勃辽兹、柴可夫斯基和达尔文等人的亲笔信。李斯特、勃辽兹的信都是用法语写的,他一面念一面给我翻译成英语,解释作曲家写信时的背景。翻页的时候他卖了个小关子:“这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原来那是一封柴可夫斯基的亲笔信。信封很小,上面有柴可夫斯基的签名和当时的邮戳。打开信封,取出一页发黄的小卡片,上面是柴可夫斯基写给他哥哥的信。教授给我翻译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在彼得堡首演之前,他从莫斯科写信给他在彼得堡的哥哥,要他哥哥给他预留某个位子。这封信是从莫斯科用马车送到彼得堡的。过了些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张明信片,是某个歌剧院的内景,教授指着一个包厢说,这就是柴可夫斯基写信让他哥哥留的那个位子。 收藏夹后面是达尔文的十几封亲笔信。他随便拣出其中一封,是《物种起源》出版之前达尔文写给出版商的信,指出印刷的几个问题。 Crocker博士家里还收藏了很多古旧书籍。最古的一本《数学原理》竟然是18世纪出版的,那个时候牛顿还活着呢。这本书深褐色的厚厚的书皮有点斑驳,但是书页还都很结实,除了边上略略泛黄,翻阅起来根本不用担心会不会碎。看到这书也算我的福气,而且这才知道原来牛顿当年是用拉丁文写的。众多的古书之中最多的还是声学方面的。比如一百多年前瑞利爵士自己编订的一本论文集。瑞利是在振动和声学理论里鼎鼎大名的人物,他把当时发表的声学论文装订成册,封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里面间或能够看到他自己的批注。这本册子里有一篇还是发明电话的贝尔(Bell)写的。我记得余光中的散文里面说,也许是因为发明电话的人偏偏姓“铃“,所以电话总是惊人如盗魂铃。我对教授说起这个巧合,他点点头说,是呀,有道理。他家还有一本一百多年前在英国出版的《声学原理》,那时候声学刚从物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在所有古书中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本《声学原理》的两卷光绪皇帝组织翻译的中译本。熟悉的竖排版、小楷,都让人心动不已。书中的插图也都用毛笔重新绘过,注着汉语的(一)、(二),可见当时光绪皇帝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之一斑。 教授家中的CD也有几千张。包饺子的时候,我随便抽了一张EMI出的《艺术家的生涯》,其中演鲁道夫的是毕约林。这部歌剧我很熟悉了,但这个版本我还从来没听过。我们一边讨论这部歌剧一边包饺子。不过教授最喜欢的还是柴可夫斯基和几个强力集团的几个作曲家。有一次在去伯明翰的汽车上他说起几天前的俄罗斯之行。他去拜访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孙女,已经九十多岁了,也是声学家。他们已经认识十几年了。这次老太太把她写的一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传记托付给我导师,让他译成英文。我们老先生居然为此买了一台俄语Windows的笔记本电脑。我们有时出去开会带着这台电脑,别人都会觉得奇怪。 有时候他也会考考我。2002年夏天在奥兰多开会,一天晚上我到他房间里准备第二天的报告。一进屋,看到书桌上摆着一张油画的明信片。他便问我是谁画的。我说是达·芬奇。他很高兴地说:“对了!”于是跟我讲他在七十年代去卢浮宫里看过真迹,还讲了达·芬奇画这幅画的背景。他甚至还告诉我世界大战期间,毕加索为了让名作逃离恶人之手,曾经潜入卢浮宫偷这幅画。 Crocker教授有着英国人传统的幽默,而且他讲笑话的时候常常不露声色,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是说正经话呢。我们去年有一次和渔业系的一个博士后一起去墨西哥湾用声学方法测量虾的产量,回来的路上这位博士后就对我说,听Crocker博士讲话要加点小心,稍不注意你就让他的笑话给绕进去了。美国国家沥青中心有一条三公里多长的实验路线,不同的部分铺了不同的沥青。我们要开着车测量每一部分沥青的吸声效率,就要在每一段开始的时候用一个触发器来控制数据采集。我们第一次去之前没有了解清楚情况,所以没有设计触发器。Crocker教授对我说,你把手放在路上,车轧过的时候你一叫,我们就开始采集数据。 受他影响,有时我也会讲几句笑话。2002年春天我们上他的声学课,学期结束的时候每个学生选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写一篇学期论文。我做的是音乐信号的分析。因为技术水平所限,我选择的音乐片段都不复杂,其中一段是《天鹅湖》里面的《四小天鹅舞》开始木管的那几小节。我做报告的时候开了个小玩笑:“The next piece is from Swan Lake, not Swine Lake。“听罢老先生会意地笑了笑,说:“那可不好,湖里都是猪就不美了。”有一次考试之前我和另外两个智利兄弟在办公室里,因为考试下午两点钟开始,大家都很乏。一个智利兄弟说:“I am too tired to take this exam.“我看了看我们三个人,说:“Actually we are three tired to take this exam.“大家大笑,缓和了一点考试前的紧张气氛。 来美国已经两年多了,我能够遇到Crocker教授这样的导师是我的福气。以后的博士论文《致谢》一节我或许会这样写吧:“Crocker教授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这段时间的学习和科研经历必将成为我一生中重要的财富。”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留学生》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