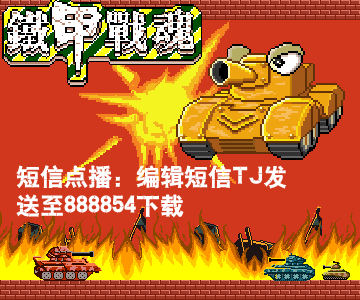在观众的口哨和尖叫声中,我一咬牙就把身上仅有的三点遮羞布拽掉了,赤身裸体任凭画师在我身上涂涂抹抹。这一脱,令我今生衣食无忧;可也正是这一脱,我脱绝了所有的亲情——
从“绿豆芽”到美女
在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下岗了,和妈妈一起辛辛苦苦摆起了小饭摊,靠一碗一碗的小吃维持生活,每天早出晚归……我的心里酸酸的,一遍又一遍发誓,一定要考上大学,挣好多钱来报答父母。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高一时,我的身高达到1.78米,人长得又白又瘦,同学们给我取了外号叫“绿豆芽”。由于没日没夜趴在书桌上,我的背渐渐有些驼了。为了矫正这个毛病,我悄悄报了社会上一个以培养模特儿为主的美体班。在美体班,我发现了女人身上有许多的美。然而不久爸爸就知道了,把我一顿恶骂,勒令我退出美体班。
我乖乖地退出了美体班,努力不去想在美体班的时光,学习更加努力、专心。2000年,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华东一所重点大学,全县轰动。爸爸自豪地从银行里取出辛苦攒下的1万元学费,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在大学校园,没有人嘲笑我的身高,女同学们反而羡慕我搞挑的身材。我心情也渐渐明朗起来,人也更加自信,业余喜欢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来展示自己。我参加了健身操队,人也越来越出类拔萃,有时候我忍不住偷偷地在镜中看自己。
被“星探”发掘做模特
到了大二,一次,我随同健身操队去另一所大学搞联谊,被模特儿公司的“星探”发现,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女人,有着和善的圆圆的脸,她盯着我看了半天,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然后眼睛亮亮地对我说:“你的身材一级棒,不做时装模特儿,那就太可惜了啊……”游说我从事时装模特。她留给我一张名片,说如果考虑好了就给她打电话。
我顿时陷进了犹豫不决之中。我知道,时装模特儿收入都不菲,如果再能获个什么奖,那就不用父母一碗一碗地卖饭为我攒学费了,做模特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一想到那个贫穷的家,我就一阵心痛,我实在是想早点自食其力,减轻父母负担。犹豫了几天之后,我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
当了时装模特儿,我才知道这一行的艰苦。这里的训练强度比在健身操队大好几倍。为了练出标准的三围,我节食、瘦身,用塑料布裹住身子在地上翻滚。有了一定的基本功后,我开始不时地参加演出,在演出的场次安排上,我尽量不误学习。大二整整一年,我都是两头兼顾,在校园和演出公司之间奔波,尽管累,但我心里非常快乐,因为我已经半年不要家里的钱了,并且站在T型台上感觉也比较良好。随着艺术修养和对服装鉴赏力的提高,我越来越像个都市女孩了:一头光滑的长发,廉价而时尚的衣饰(我常去市场“淘服装”),丰满的胸部,轻盈的步态,尤其是我的皮肤,“像宋瓷一样细白,像丝绸一样光滑”。老师和同学们惊讶于我的这些变化,他们说我有种脱俗的气质。
为了100万我全裸演出
2001年,人体彩绘开始流行。2001年4月中旬,我随队去东北一座大城市演出,一连演出十几场,都是局部彩绘。演出效果还不错,人们争着来看新奇。没想到,一件令我悔恨终生的事情就要在那里发生。临走那天晚上,一家商场经理突然来找,说观众要看全裸的呼声很高,询问与我们签约的当地礼仪公司女老板,能否搞一台全裸彩绘表演,他愿意给表演的模特出价100万。
100万!女老板和全体模特儿眼睛一亮,可片刻就都黯然了,那可是全裸呀!我低头思忖,心咚咚急跳。这时妹妹打来了电话,说爸爸的胸膜炎又犯了,妈妈停了饭摊,天天陪着爸爸去医院输液。而且,妹妹刘银夏天就要参加高考,她也是个学习尖子,如果考上大学,又须一笔学费。放电话,我一阵难过,不能再给父母增添压力了,做姐姐的我应该尽这一份力。有了这100万,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还能为父母买幢小楼,让他们也像那些退休干部一样悠哉游哉去遛鸟、去扭大秧歌,而不是每天顶着星星摆饭摊。
整个晚上,眼前晃动的都是那烫手的100万元,我一夜不寐,第二天清早便黑着眼圈找到女老板要求全裸表演。女老板一阵欣喜,拿出合同书:“决定了,你可不要后悔。”“我决不后悔”我一脸的视死如归。
大幅海报贴出去了,这个大胆的演出消息宛如8级地震颠覆了全城。演出那天,商场外人山人海。
上午9时整,演出开始,画师开始做准备工作。我和另外3个模特儿身穿泳衣端坐在舞台上。台下突然有人吼了一嗓子:“快脱呀,怎么还穿着那几片布?”当时,我一咬牙,大脑一片空白,三两下便把泳衣除了下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在轻柔的音乐中,画师开始工作,打线、上油彩、修饰,这个过程整整用了1小时50分钟。画毕,按合同规定,我必须在舞台上走3个来回。我平静地迈着优美的猫步去做了,合同生效了,我得到了那100万。
亲情爱情友情弃我而去
如何支配这笔钱,我在全裸之前就想好了,可钱真正到手了,才明白并不容易花出去。我先试探着给家里寄去1万元,结果爸在电话里盘问了老半天。2001年8月,妹妹考上了省里一所综合性大学,我又汇去两万元,不知为什么爸竟没有详细问。我胆子大起来,跑回去在市里为父母买下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当我兴冲冲地把房门钥匙交给爸爸时,爸爸的脸都青了。
原来,爸爸已知道了一切,伤心欲绝,他要我跳到家乡大渠里死掉算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大渠边的。大渠里流的是黄河的水,混浊而湍急。我在渠边一直呆坐到天黑。繁星满天的时候,四周静极了,从百里外黄河滩上刮来的风,抚摸着我的头发,叩问着我做模特儿以来塞满物欲的心:我真错了吗?如果我能预料100万能摧毁爸爸做人的尊严,能割断比大海还深的父女之情,我绝不会全裸……
我无处可去,学校不能回,我逃课太多,已被学校除名。相恋的男友在我全裸的第二天便与我分了手:“干什么都得有个度,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超过界线我不能容忍……”
失去朋友,失去亲情的我,盲目地坐着火车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2002年夏天,我去了沿海,在一座有着美丽港口的城市安顿下来,想找份工作。可我除了会走猫步之外,一无所长。思忖良久,我决定重干老本行,于是与模特队的小姐妹阿雯创办了一个“女子美体中心”,集训练、休闲为一体。
爸爸已经去世,临终留下话来,不许我回去奔丧,妈妈依然住在昏暗潮湿的老房子里,说什么也不住新房。小富姐打扮的我,内心却极其苍白凄迷。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培养学生上面,除了练形体,还练她们的心,不要她们在金钱面前迷失……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