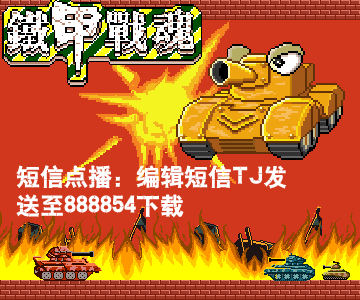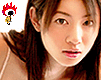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
李清川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
□杨东平
大学校长的“谱系”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等等。另外一批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和李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安波和马可,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还有一些是政工干部,如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等。无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逆境之中,他们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努力依靠和保护知识分子,尽量减少“左”的干扰,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竭尽心力,并在“文革”期间备受迫害。他们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大学校园留下许多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谢希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大连工学院院长钱令希等等。然而,时移代易,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变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了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新一代大学校长的胸襟、抱负、视野和理念,决定着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对新一代大学校长群体,也许我们尚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本书的采访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大多出生于1940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1980年代后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他们基本是学理工科的,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此外,他们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这赋予了他们一种共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就治校而言,他们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他们的不同个性,或深沉或挥洒,或智慧或诙谐,皆跃然纸上。
对新一代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这不仅因为他们更为年轻(最年轻的山东大学校长展涛为37岁),而且因为他们正在经遇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现行的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视听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强烈挑战,处于一个文化范式更新转变的时代;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急于赶超的高远目标,以及人们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转化为对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这一理想恐怕是大大高于西方大学或以往中国大学对校长的要求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表现在校长群体上的外在特征之一,是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不久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耶鲁大学校长助理莱温对谈时就说道:“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自一些大型企业。而欧美大学的校长多是学文科的,像经济、法律、哲学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北大的校长也是学文科的。”我想,这一落差同时也表现为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也还没有被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没有落实。
因而,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
|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