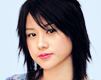| 南方周末:追寻昔日神童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7/21 18:54 南方周末 | |||||||||
|
 在当年的合影里寻找自己 本报记者王轶庶/图 □本报记者 李海鹏 隐藏者
“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即使在其母校的校园内,关于宁铂的信息也多不确切。他在近代物理系的一位前同事告诉记者说,宁铂出家去了云南。另一位老师则说,他去的是峨嵋山。事后记者向宁铂的父亲求证,两种说法都被否定。在近代物理系,更多的宁铂前同事们持一种避讳的态度,不愿提供有用的线索。 5月19日,记者找到了宁铂出家前位于中科大北区的住所,不过很快就被邻居告知,宁铂的前妻程陆华早已搬走。记者通过程陆华的一位好友的父亲,辗转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很显然,他们的态度非常警惕。 次日,在中科大东区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记者见到了程陆华,同来的还有她与宁铂的儿子。这位戴着渔夫帽的母亲始终保持着礼貌的微笑,几经劝说之后,终于同意坐下来吃完午餐,但是拒绝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 “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她说,“已经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对她来说,平静的生活指的是,自己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收入不多,但带一个孩子也够了。搬离中科大北区内的宿舍,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买房,远离人们的议论和注视。不再婚,至少暂时不作考虑。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接受任何采访。一年前,她拒绝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的约请。她说,也许自己老了的时候会说出过去的一切,但是现在还没有心理准备。 她的孩子在中科大附中读初三,显而易见的特征是非常有礼貌,记者每次劝他吃菜,都会得到一声郑重、洪亮的“谢谢”。男孩的长相颇有乃父之风,个子不高,额头硕大。在母亲谈及父亲的时候,他安静地喝下一杯又一杯饮料,保持着与母亲一模一样的笑容。“宁铂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程陆华说。 在嫁给宁铂之前,程陆华是他当年的众多崇拜者之一,曾与其通信联络达数年之久。对于1980年代早期的追星青年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举动。不过在宁铂的少年班同学们看来,这恰好体现了二人在文化和地位上的差距。因此,几位少年班同学猜测说,程陆华对于“时代悲剧”的体会更多地来自她自己的遭遇,而非来自宁铂的命运。 “对于女性来说,宁铂本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她嫁给他,也许冲的就是他的名人身份,头上的光环。可是后来这一切突然幻灭了。”他们说。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关于前夫的事程陆华说得很少,对于记者提起的话题也很少响应。相比之下,她更愿意谈论合肥的风景名胜。 她表示,自己对宁铂的现状一无所知。“很久没有联系了。”她说。 出家之后,宁铂确实切断了与俗世的联系,除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宁恩渐与儿子一样,也在躲避着原本熟悉的世界。 在电话中,江西冶金学院的几位老师先后告诉记者,宁恩渐离开了赣州,“据说”去了杭州,大多数原来的熟人都没有得到新的电话号码。后来证实,宁恩渐确实移居杭州,住在女儿家里。最终,记者询问到了他新的电话号码,但刚刚在电话中提出采访意图,立刻就遭到拒绝。记者随后赶赴杭州,不过对于寻找宁铂来说,此行仍旧毫无成果。 宁恩渐在电话中第二次坚决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如其所说,只是出于“对善意的回应”,对记者讲述了一点儿宁铂的大体现状。 在6月,宁铂受邀到湖南一带的几个寺院里讲授佛学。在父亲和姐姐的帮助下,宁铂购买了电脑,随身携带。他可以上网,偶尔通过网络与父亲联络,有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这台电脑还被用于编写一些佛学文章以及相关“教材”。 在昔日的同学中,有传言说宁铂在佛学方面颇有造诣,如今“已经是高僧”。宁恩渐对此说,儿子只能说“取得了一点儿成绩”。很明显,这位父亲对于宗教世界中的前途并不认可,在谈话中语气沉痛,多次叹气。 他还在希望儿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科大工作,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对科大充满了不信任,矛盾之下只好尽力不去想未来的事。他承认,自己不得不追随着儿子,在逃避中度日。 “离开赣州就是为了离开老环境。”宁恩渐提到了自己作为父亲的羞耻感,“现在不是我自己抬不起头来,是我们整个家族都抬不起头来啊。” 事实上,干政逃避得更为彻底。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相当多的科大老师,包括谢彦波和当年少年班的第二任班主任朱源,都错误地认为干政已经回到安徽省巢湖市老家。5月18日,记者就此赶赴巢湖市,试图通过巢湖市公安局的搜索系统查找,最终一无所获。 事实上,干政的隐居地就在合肥,在一处离中科大东区不远的居民小区,多年来与母亲相依为命,几乎与世隔绝。 5月21日,他拒绝了记者的见面约请。事实上,干政几乎不见任何人。在7月初的同学聚会期间,昔日老友们多次与之联络,希望“见个面或者吃顿饭”,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在聚会次日的座谈中,老友之间交换了一些关于干政的零散信息,不过,聚会召集人之一的王永教授决定,那次座谈“谢绝任何外人参与”,具体情况因此不得而知。 “我的生活天天如此,没有工作,非常单调,没有任何好说的。”干政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外部世界没有关于干政的消息,干政也没有外部世界的消息。当记者告诉他宁铂已经出家了时,他说:“是吗?我不知道。”语气平淡,似乎在意料之中。 “破案”者 “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谢彦波同样不知道宁铂的行踪,尽管他们是多年好友。在连续3次推托之后,谢彦波终于同意与记者见面。 这位39岁的副教授似乎完全不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记者刚刚走进他家,谢彦波立刻以相当突兀的动作,把一个盛满浓茶的大瓷杯塞到了记者手里。由于这一动作没有伴随任何解释,记者不得不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主人的待客之礼。从客厅陈设的简单程度看,这里很少有正式的客人到来。谢彦波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摆好两把木椅,然后自己在其中一把上面坐下来。 整个场面显得非常严肃。当记者也坐下去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参与1950年代的元首会谈。 类似的表现,确实会让人联想到天才的某些特质。在少年班时期,谢彦波一向以知识丰富著称,但自理能力之差才是更为显著的特色。从童年时期起,他就有诸多奇特的表现,比方说,他似乎会以另外一个身份旁观自己。那时他从不说“我”,而是像别人一样称自己为“彦波”。饿了的时候,他对妈妈讲的话似乎是在说另外一个孩子,“彦波要吃饭”。 当类似的特征出现在39岁的中年人身上时,问题就放大了。谢彦波如今颇为苦恼。 “跟别的同学比,我算混得比较惨的。”他承认说。不过他又表示,这其实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别人总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就让我很吃亏。” 在此前的电话中,他也一再向记者重复,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他而言,这种感觉意味着,自己的思维可以被别人察觉,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小的想法,还是科研领域里的一个灵感。结果是,他在科研上无论取得什么突破,都会被别人捷足先登。别人想窃取什么的话,就像在自己抽屉里拿出一只钥匙扣那么简单。更多的困扰来自于日常生活。他感到自己成了透明人,而别人都深不可测。 谢彦波承认,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次数太多了,”他说,“我注意了多次,都是这样。” 在记者的坚持下,他举出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有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运算错误,本来谁也不应该知道,可是第二天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个人看了出来。那人走过我身边,冲路边吐了口痰,他用这种方式责备我。” 当那人吐痰与他的运算错误之间的必然联系受到记者的质疑时,谢彦波犹豫了一下,表示自己也不是特别肯定。 记者认为这种不自信是个好的征兆,于是委婉地建议他“也许该去看看心理医生”。谢彦波略显紧张,不过立刻说了声“谢谢”。 他说,他的母亲也曾给过他相同的建议。事实上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但是医生“没说出什么来”,使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去。 “我也觉得自己的心理有点儿问题,”他说,“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我的计算工作。” 在中科大近代物理系,谢彦波向学生们讲授群论和广义相对论。不过,他本人对物理这门学科却越来越怀疑。过去他认为科学是神圣的,但是最近几年来,他开始怀疑整个科学体系。他试图查找一些漏洞,进而证明科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他正在从铁接触磁铁后会产生磁性的问题入手。他认为,如果用现有的理论加以推导计算,并保持过程的诚实的话,那么计算出的磁性应该比实际的磁性小。这意味着,要么有超自然的力量介入了磁铁,要么现有的关于磁力的理论一直存在错误。如果问题在于后者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明,科学一直就是一种充满谎言的学问。 因此无论哪种可能得到证实,谢彦波的这份私下里的工作都可以促使自然科学瓦解。更重要的是,它还将证明人们一直在欺骗他,尤其是那些科学界的人。 “我就是想向他们要个说法,”他以一种被冤屈者的倔强说,“有时我觉得自己像秋菊似的。” 几年来,他在使用计算机进行相关计算。他说,主要的工作是写程序,不需要什么创造性,但是很烦琐。他孤军奋战,无人帮忙。“系里的同事都劝我不要搞这个,他们也没说为什么。”他说。 在记者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信任的人时,谢彦波回答说,没有。有几个学生在帮助他计算,但是他一直担心学生在程序里故意加些东西,破坏他“破案”。 “破案”是谢彦波对自己这种计算的一个叫法。另一种叫法是“斗争”,或者其英文“fight”。 如果他确有心理问题的话,那么一个好现象是,他对自己的各种想法缺乏信心。“其实我也不是很确信这些。”在受到质疑时,他常常会主动退缩,“我也觉得自己这么做挺无聊的。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就一个中年人来说,他有着一种淳朴而纯真的笑容。放松下来时他的声音很有中气,站在窗口叫女儿的名字时,也颇有父亲的慈爱与威严。 不过,在心底里,他的惶惑与愤慨同样多。“我必须破案,”他一再重复说,“我要跟他们fight。”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教育信息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教育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227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