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北大记忆”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先生。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了解一下吴慰慈先生与北大的故事。
口述:吴慰慈
记者: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7级硕士生曹雪盟
北京大学药学院16级本科生刘博涵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16级本科生贺依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6级硕士生毕梦静
编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15级本科生田淼
摄影:刘学红

教授简介:吴慰慈,男,1937年生,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1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市图书馆,1973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2005年被评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第一部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的主要执笔者和第一部示范性教材《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参加中美图书馆界高层论坛并担任组委会副主席,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华盛顿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讲学。一生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320余篇。2017年12月出版《图书馆学文稿:吴慰慈自选集》,入选“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大学四年从没逃过课”
记者:得知自己考上北大之后,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吴慰慈:1957年是我的进校年,那一年北大在我们枞阳县就录取了我一个人!当时的县长还特意到我家去祝贺,说我为家乡争了光。所以当时我非常高兴。1957年9月,北大开学,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就自己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坐上了从合肥开往北京的火车。
记者:担子里装了些什么?
吴慰慈:担子的一边放着一床被子,另一边放了一个小箱子,大概有三四十斤重。当时的火车停在前门火车站,北大派了校车迎接新生。我一看到北大校车,心里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很兴奋很兴奋!上了校车以后就感觉好像到了我的第二个家了。
记者:您当时住在哪个宿舍?
吴慰慈:我记得我在北大住的第一个宿舍是30号楼,当时叫30斋,123室。这个楼现在已被拆掉,盖起了新的。当时听说要拆,我心里还很留恋。回想起当年,宿舍很简陋,很拥挤。三张双层床,一间屋子住六个人,一个人有一个小桌子,桌子很小,每人床底下有个放衣服的抽屉。
记者:当时的食堂怎么样?
吴慰慈:食堂就主要是大饭厅和小饭厅。我比较喜欢吃新疆的抓饭,里面有菜有饭还有点肉沫,菜主要是白菜、菠菜、胡萝卜,很便宜。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拿助学金,我拿的钱最多,每个月12块5,但生活也很艰苦。
记者:学校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吴慰慈:老师讲课好。北大老师讲课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围绕专题来讲,讲得很生动。我在北大待了四年,从没有逃过课。因为老师讲得太好了,少听一节课都是很大的损失。
记者: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
吴慰慈: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科技概论,都是一些著名的教授来讲。生物学名家沈同、还有化学家张青莲等都讲过这门课。数学系的陈铎教授不仅讲课娓娓道来,仪态也很好。那个年代人穿西服的人很少,但是陈铎教授每次上课都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有鲁迅先生的好友川岛先生(章廷谦),讲课慷慨激昂,资料丰富,论述很全面,让我印象深刻。
记者:您在中学时英语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时是如何学习外语的?
吴慰慈:那时候学校要求学俄语,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也不应该把它丢掉,多掌握一门外语总是好的。所以我经常去英语系蹭课旁听自学。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不满足于老师课上讲的知识,求知欲很强烈,所以经常自己去图书馆找一些外国的书来看。当时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向苏联学习,所以我看的也主要是苏联图书馆学方面的书籍。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我先走了一步。虽然最开始看俄语原版书有困难,但是大概过了三个月,我就基本没障碍了。英语和俄语就像我的两条腿,让我能够看懂许多外国文献。
记者:您当时每天的课多吗?
吴慰慈:每天都有很多课。我当时从没想过要当专家,只想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在北大的四年里,我学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怎么学专业课,那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多看文献;另外一点,就是怎么搞科研。在这一点上,王重民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教会我如何收集资料、建立资料档、分析资料、提出观点,告诫我们做研究要谨慎,不能轻易下结论,结论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当时做了很多小卡片,用来收集资料,全是一笔一划手写的,现在都还留着。可能短期内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时间长了以后,特别有助于提高对文献的熟悉度,也就为搞科研奠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
记者:您是如何在四年里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的呢?
吴慰慈:其实在高考之后报志愿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是比较盲目的。但是等我来到北大之后,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来到这个专业,就要在这个专业里做点事情。北大是中国的高等学府,我能考上北大,就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校徽,我只要出门就必然要戴上这个校徽,感觉非常自豪。我决定努力学习,不能给北大丢脸。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记者:毕业之后您是如何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的呢?
吴慰慈:当时我们毕业之后是组织上分配工作,也要填志愿。当时的话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当时都想着要到边疆去支援建设,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兰州,但最后却被分到天津去了,在天津干了十二年。
记者: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吴慰慈:我当时在研究辅导部工作,主要是研究和培训,以培训为主。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天津全市范围内授课,培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才。那时候为了准备讲稿,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天津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天津的每条街道我都认识。一周六天工作日,我一般有四天都在外面做调研,晚上才有时间写文章写讲稿。讲稿写完以后我不会马上拿去讲,会找几个老馆员做听众,在他们面前先“排练”一遍,然后再修改,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记者:您最初做培训讲座时会紧张吗?
吴慰慈:我属于听众越多越激动的那种,最多的时候给几千人讲过课。我还曾经把北大图书馆系的老师请到天津,听我讲课。就这样一点一点,我和同事们一起把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搞上去了。当时好多领导和前辈都喜欢和我开玩笑,叫我“小专家”。
记者:这段工作经历对您日后的治学和科研有什么影响?
吴慰慈:这段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做图书馆实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点书本知识、不结合实践经验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让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在天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凭着工作给我的启发,我先后编写了《小型图书馆分类表》《区、县图书馆图书分类范例举要》《图书馆藏书建设概要》《小型图书馆藏书清点法》等小册子。当时我还很年轻,出版一套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而且这套书的社会效果也说明研究图书馆学不能单纯从抽象的定义、概念、模式出发,要不断和实践相结合。

“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
记者:您是何时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的?
吴慰慈:1973年10月,我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能重新回到母校,我的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我学习在北大,能回来为母校的发展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感到无比光荣。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个转折点,那么1973年回到北大,毫无疑问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记者:您主讲的“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在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吴慰慈:1977年9月,我开始独立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这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有学生反应“教学内容单薄”“没有学科的理论高度”。所以我就和教学小组一起,对这门课进行改造。1985年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新编教材,这本书现在依然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必读教材之一。除了新编教材,我还把国外图书馆学的发展引入课堂教学,并且激励年轻教师投入本科教学工作。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很团结很努力,合作非常默契,遇到问题都是集体讨论解决。这门课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这门课我从1977年讲到2012年,每年的讲稿都有新调整。我觉得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分析问题的能力才是能影响学生一生的东西。
记者:对于刚接触这个专业的同学,您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慰慈:最重要的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所谓理论把它通俗化就是理念。我收集了好多典型的案例,和理论结合起来,课堂就比较生动,学生也能听进去。
记者:您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
吴慰慈:我的做法是用教学引导科研,用科研促进教学。科研的题目或灵感常常来源于教学实践,而科研的理论成果可以使教学水平提升。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现在技术的发展很快,北大信息管理系也正在筹备开设图书馆技术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新技术和新趋势。挪威、瑞典都研究出来了智能排架,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好处。我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培养实践的能力很重要。所以我既是教学人员,也是研究人员。我觉得不能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
记者:您平时的休息时间都喜欢做些什么?
吴慰慈: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篮球和乒乓球。上中学的时候是校篮球队的主力。考上北大以后我在系篮球队打右边锋,投篮很准。现在上了年纪就散散步了。好身体是基础。我在讲台上一直站到75岁,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大年三十我也在工作,而且从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一直都这个样子?
吴慰慈:是的,我从中学开始就很勤奋,非常勤奋。夏天一般凌晨三点或者三点半就起床,读一会儿英语,再去吃早饭、上课。那时候吃得也很差,一年到头能吃一两顿猪肉就不错了。但是大家都很勤奋,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工作8小时,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一天不看书就全身不舒服。

“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
记者:1996年起您就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博士研究生。您是如何培养博士生的呢?
吴慰慈:学业上从严要求,生活上悉心关怀。每年我招的博士生一进校,我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从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给他们提出要求。博士生的选课是很重要的,我给他们选的课程一类求精专、二类求实用、三类求广博。并且我会为鼓励他们从事科研活动,专题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不能马虎。如果学生做得好,我会充分地肯定他们,但做得不好我也不会客气。
记者:您在生活上是如何关心他们的?
吴慰慈:我经常和学生们聊天,学科发展的动向、新情况、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都会一起聊。所以我和他们能打成一片。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工作,但她丈夫在上海工作。两地分居,心里很难受。我就开导她,然后帮她协调调到上海工作。所以有的学生跟我说,“您就像我爸爸一样”。我有很多学生现在在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工作。我们都还保持着联系,过年的时候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大家的感情一直没断。
记者:您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是也很严格?
吴慰慈:我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我想可能与受到北大这个氛围的熏陶有很大关系。她们从小就是在北大里长大的。生活上注意营养,要吃好饭,学习上我给她们创造条件。比如说老二小时候数学上有点困难,我就请当时北大附中数学教研室王主任帮忙给她辅导,成绩很快就有了提高。老师的水平太重要了,好老师一点拨你就会了。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让她们继承您的专业?
吴慰慈:我不干涉他们的选择。大女儿现在定居美国,小女儿在中国民生银行工作。我觉得孩子的选择需要她们自己决定,从小我就告诉她们要自立自强,勤奋努力。北大人都依靠勤奋才能获得成绩,也就是时间抓得紧,不轻易浪费时间。
记者:在您看来,“勤奋”是不是北大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吴慰慈:是的。我一直说北大人不偷生。他们不一定追求高官厚禄,但是对于自己所钻研的领域一定是坚持又坚持,勤奋又勤奋。我从我的老师身上就看到,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学问,这是北大的长处。北大人不吹牛、不夸张,说话都是有根据的、实事求是,这就是北大人的风格。
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从没有动摇过。我一辈子生活在北大,是北大培养了我,我不追求别的,只希望为北大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只要做,就总会对北大的发展有所帮助。我应该感谢北大,到现在我还是这种心情。北大给了我很多很多,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什么时候结束,再说。只要我还能干,就会一直干下去。


- 145.15分
- 139.85分
- 132.06分
- 109.23分
- 99.75分
- 93.06分
- 89.66分
- 87.25分
- 84.74分
- 83.32分












 有钱,才是孩子们的核心竞争力?
有钱,才是孩子们的核心竞争力? 导师制弊端不除 研究生难逃活地狱
导师制弊端不除 研究生难逃活地狱 IB、AP等课程,我的孩子究竟适合学哪个?
IB、AP等课程,我的孩子究竟适合学哪个? 日本企业为啥不怎么喜欢硕博毕业生
日本企业为啥不怎么喜欢硕博毕业生








 选择国际学校如何帮孩子抢占先机
选择国际学校如何帮孩子抢占先机 新浪2017“中国教育盛典”
新浪2017“中国教育盛典” 2017全国特别报道:40年,新高考
2017全国特别报道:40年,新高考 第六届诚信移民机构评选获奖名单
第六届诚信移民机构评选获奖名单



 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王俊凯谈环保
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王俊凯谈环保 台湾大学爆笑爱情课
台湾大学爆笑爱情课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开讲金融市场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开讲金融市场 你不知道的日本传统文化
你不知道的日本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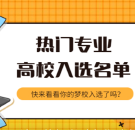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指南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指南 2018年考研报名
2018年考研报名 直击2017年6月大学英语四六级
直击2017年6月大学英语四六级 2017全国高考特别报道
2017全国高考特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