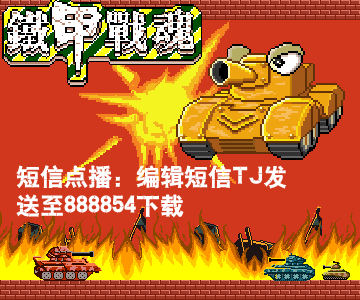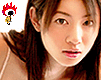每个上网的人都有接触超链接文本的经验,那些访问过的链接往往变了色,友善地提醒你,我们之间已经不是陌生人。马不停蹄地经过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旅行中,我也能体会到这种超链接的感觉:在一个全新的目的地,却发现了一两处变了色的链接,只消轻盈一点,便把我拽回了那个才作别的地方。于是,从巴黎到阿姆斯特丹到科隆到回旧金山的飞机直到家里,这些鲜少交集互不搭界的地点,因为这个超链接的无处不在,使他们之间成为那种经常串门,并时而在邻舍家里落下东西的近邻。
比如才在出发前重温了《天使爱米莉》,转身便已晃晃悠悠地转到了巴黎蒙马特的圣文森特大街,电影《爱米莉》的第一镜就在这里,画外音适时响起:“九月三日傍晚六点二十八分零三十二秒,一只一分钟可以振翅一万四千六百七十下的蓝色果蝇降临在蒙马特的圣文森特大街”,电影里一条铺了台布的餐桌开始如果蝇振翅般地乱颤,天使爱米莉不久之后就诞生在我脚下的蒙马特。
比如才告别蒙马特的勒皮克大街五十四号,那个文森特·凡高曾经谦逊生活着的公寓,24小时后我便已降临在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扑面而来的是凡高1887年的布面油画:《从文森特在勒皮克的房间看巴黎》,画面呈现的正是勒皮克大街五十四号三楼望出去的巴黎天线。新印象主义的点彩风将蒙马特大抵灰蓝的面目解析成细碎的色彩斑块,蒙马特的上半身因此流光溢彩。
比如才将离凡高博物馆不远的JORDAAN区印象交付给记忆保管,从阿姆斯特丹到科隆的列车便把我引到了和科隆大教堂毗邻的路德维希美术馆,美国现代写实绘画的代表人物埃德华·霍珀(EDWARDHOPPER)的画展正在该地举行。霍珀画很多高速路边的旅馆,很多预示变故的火车,很多动荡片刻的滞留,很多两人之间的寂落,他还画很多惊鸿一瞥的夜窗。在他1928年的那幅《夜窗》前站定,三扇毫无遮掩的窗户里,有半个女人的模糊背影,粉红睡裙下的肢体如层峦起伏。那一刻,那窥视中既亲密又疏离的定格,怎不把我带回阿姆斯特丹,JORDAAN区运河边小望窗扉的水都之夜?那个十七世纪蓝领阶层的聚居区现已是艺术家和引领风尚的年轻人的阵地,游走JORDAAN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便是张望运河两边的人家,他们都有一扇扇顶天立地的窗户,用上海话里的“窗门”命名顶合适不过,即使夜已落下,JOR鄄
DAAN的居民却不急着卸下窗帘。
屋里通常也有一个女人的影子,背对着窗,好像在准备晚饭,或者只是一个茫然无措的意象。
比如旅行的尾声,从法兰克福到旧金山的夜机上,我重又拾起那本从未能读完的阿兰·德波顿的书———《旅行的艺术》,当看到他在书中一次次地提及霍珀的画:自动售货餐厅里独守咖啡的黯淡女子,旅馆里正在读信的独行女子……我对这种空间时间人物之间的交叉来回超链接早已不再诧异。
最后到家,《天使爱米莉》那张青青红红的碟片尚躺在凌乱的茶几上,再也不用将它放入DVD机,只消轻轻一点,我脑筋里的超链接文本就已经打开这样一段话,电影里那个从不出门的,象玻璃一样易碎的画家老头对爱米莉说:“……就像环法自行车赛啊,久久期待,转瞬即逝。”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