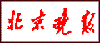| sina.com.cn |
| ||||||||
|
|
由余秋雨揭露盗版集团是"文化杀手"所引起的"谁是文化杀手"的争论,前一段时间逐步升级走调。北大学生余杰突然宣称余秋雨三十年前是"文革余孽",萧夏林等主编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则称余秋雨是"四人帮文胆";更有甚者,有人发表文章称余秋雨是"四人帮""帐中主将"、是"文化流氓",号召天下知情人出来作证,揭露余秋雨。几经炒作,全国报刊、网站上的批余文章已经数不胜数。这场突如其来的"批余热"显然已远远超越了文化批评的范畴,直接指向了我国当代早已完成司法程序的第一政治大案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对余秋雨人身、名誉的任意攻讦。因此不能不引起包括法律、新闻等各界人士的注意。 怀疑,从常识出发 在这场大批判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异音发出,可惜没有引起大家注意。例如苏州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尹卫东先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些疑问:如果余秋雨在文革中问题严重,上海文化界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那些泰斗都应该知道,但为什么闻所未闻呢?第一,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早是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连载的。那时巴老还头脑清醒地在写《随想录》,在狠批文革。他连听到一句样板戏都会作恶梦,怎么会容忍一个文革余孽在自己主编的杂志里长期开专栏?怎么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多次正面提到了余秋雨? 第二,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著名导演谢晋似乎也没察觉。八十年代中期,谢晋公开请比自己小二十岁的余秋雨担任艺术顾问。这条新闻在当时各地媒体都有报导,也没见有人出来提醒过谢导。 第三,戏剧大师黄佐临在文革中受尽磨难,而黄佐临与余秋雨保持的忘年佳话,文坛共知。他发表于八十年代的某些重要论文,也郑重注明由余秋雨执笔。 巴金、谢晋、黄佐临三位,是上海文化的一代良知所在,与文革中的邪恶势力不共戴天,难道他们全都闭目塞听?这可能吗? 当然这种凭常识的判断总显得不够严密,于是记者就从上海戏剧学院这个余秋雨毕业直至担任院长的单位开始,进行"余秋雨文革问题"的调查。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余秋雨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主要行政领导。上海戏剧学院是个正局级单位,一直受上海市委和国家文化部双重管辖。如若余秋雨在文革中真有问题,要蒙过上海和文化部两个组织部门的严格考查,难上加难。一方面,当时考察干部时,对当事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是重中之重的审查内容;另一方面,余秋雨自1963年开始,大约30年时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全院上下对他知根知底,只要有人递上一个条子,能指证余秋雨是"文革余孽",那肯定一票否决,连个科长都当不成。但是余秋雨当了多年的院长,在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现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葛朗先生说: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是完全的捏造!我参加过上海戏剧学院对文革"三种人"的清查工作,也知道上级对余秋雨进行干部考查的内容,余秋雨是清白的。上海戏剧学院在文革中曾有全国闻名的"革命楼",是"重灾区",上级组织部门对上海戏剧学院干部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记者没有权利将组织部门对余秋雨的干部考查内容在媒体上发表,但可以从其它调查来进一步说明问题。 巴金先生的女儿、现任《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是余秋雨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这一届非常特殊,1963入学至1973年分配,在校时间近十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小林回忆说:"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们都才20岁左右,余秋雨家里受到冲击,他在学校里一直是造反派的对立面,是老保(即保守派)。1968年底我们都下到军垦农场劳动去,直到1970年底才回上海。由于学校一直在搞运动,我们这个班到1973年才开始分配。当时中央号召复课,要各校联合编教材,余秋雨这个时候被学校推荐去了后来才知道是"写作组系统",学生毕业总得要个工作,编写教材在那个时候对余秋雨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知道他在那里并不开心。那时他经常到我家里来,来看望我父亲,每次新的《摘译》(一种译介外国人文动态的出版物)杂志出版,他都带来给我爸爸,我爸爸也经常托余秋雨买一些书,当时我爸爸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而这个时候我爸爸是被张春桥点名"不枪毙就算落实政策"的"反革命",对我们这种家庭,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余秋雨经常来,还一起发牢骚,可见他与造反派是不一样的,那时他就表示要离开那地方和那些人。后来他得了肝炎,很快就到外地养病去了,直到文革结束,这前前后后的事是我的一位老师安排的,余秋雨如何被分配到那里,他也知道,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你可以去问他。 李小林所说的老师盛钟健曾是浙江省作协的负责人,现退休在家。1974年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等余秋雨这个班分配完毕后,就去了宁波文化局工作。盛钟健先生在电话中对记者说:"1975年夏天,我回上海,得知余秋雨生病了,我前去探望。记得那时余秋雨住在虹口区一个朋友一间临时搭的小屋内,非常闷热,肝炎病人怎么能这样养病呢?他如果当时受到上面重视,怎么会这个处境呢?当时我就在宁波奉化一个山上给他找了一间房子,余秋雨就来这里养病。余秋雨去写作组系统是这样的,他1973年分配时,我有个同学在复旦编写教材,我就推荐余秋雨去复旦大学编写教材。"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意外得悉,我们的同行、《新民晚报》体育部主任张攻非先生在文革中与余秋雨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便前去采访。张攻非先生说:"我父亲是一个17岁投身湖南农民运动的反蒋革命志士,解放后担任高级干部,却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迫害致死,全家蒙难。我又被分配在一家工厂劳动,心情很坏,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了余秋雨,当时他从农场回来,被分配在写作组系统的一个教材编写组,我知道他与我一样心情苦闷,我们一起喝酒,发泄对时局的不满,我们私下的议论还被人告发过,我们差一点被抓起来。他为逃避被利用,拒绝写大批判文章,后来生了病,干脆离开上海,脱离了政治旋涡。但令人气愤的是,那个当年告发我们的人,后来反而倒过来写文章揭发余秋雨文革中有问题。" 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通过上面的采访,余秋雨在文革中大致经历已经清楚:文革初期已有多人证明他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而文革后期斗争最激烈的那些阶段,像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批邓以及"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时期,余秋雨整个儿都在医院和乡间养病,连犯错误的可能都没有。各位当事人都可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没有斗过、整过、害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虽如此,记者在采访调查中看到,他们对余秋雨在那十年到底写了些什么,都无法说清。余秋雨自已说主要是写了一篇半文章,其中一篇是《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轶文》,至今可以找到;还有《胡适传》的一个开头,没有写下去。 批判者断言余秋雨写了数十篇大批判文章,但他们能指出题目来的也只有《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走出彼得堡》两篇,前者发表于1969年的《红旗》杂志,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后者发表于1975年的《朝霞》杂志,署名"任犊"。记者根据《今日名流》上一篇文章的线索,采访了当时写作组的正式成员胡锡涛先生,胡先生明确告诉记者:"《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我本人执笔,和余秋雨毫无关系。但今年春天为《今日名流》撰文时,无法核对材料,误以为《走出彼得堡》是余秋雨写的,便把他批评一通。最近,从上海知情人多次打来的电话中,我才知道《走出彼得堡》是针对当时上海一个犯了生活错误的著名工人作家而写的,作者并不是余秋雨。由此可见,我和一些老同志即使想为余秋雨说几句公道话,也容易把余秋雨现在的知名度误植到25年以前的他身上。"胡先生现在是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余杰说余秋雨写了"数十篇",刚点出两篇又都不对,那这数十篇是什么篇名,发表在哪里,记者已没有能力访求到,只好耐心请热衷批判余秋雨的人拿出来。 寻找最权威结论 随着批判者给余秋雨头上戴的文革头衔越来越大,而其中两个都自称参加过清查的人的意见又正好相反,我们的采访也不得不深入到当年担当上海文革清查工作的领导核心人物,所幸他们还健在。 在寻访过程中,记者也渐渐明白,上海在文革后期的所谓"写作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组",而是囊括宣传、社科、文教等职能部门的一个松散的行政领导系统,在其间工作的有数百人,包括很多分散在各个高校的教材编写组,因此被称作"写作组系统"。 对这么一个庞大松散机构的清查,上级派出了强大的力量。清查组组长是原《解放军报》负责人王素之,专门从北京调来;副组长是原《解放日报》负责人夏其言。在文革中,王素之受到江青点名批判而受尽迫害,夏其言则受到张春桥的点名批判被长期关押。两人作为清查组的领导是有充分资格的。清查时间长达两年,查出了大量性质严重的事件、人物和文章,不少人受到了处理,清查结果又交司法部门进行严密的侦查审讯,有的人还被判了刑,其间王素之调回北京后,夏其言担任清查小组组长。 经多方打听,日前,记者终于在北京三0七医院的一个病房内找到了王素之将军,他离休前是国防科委宣传部长,现已77岁高龄。问起当前文坛争议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是是非非,王素之将军毫不含糊地说:"余秋雨在文革中根本没有问题,是清白的。当时上海宣传口一位负责人因一件小事对余秋雨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来搞清楚后,这位领导人还向余秋雨道了歉。文革清查结束之后,我一直想调余秋雨到北京的部队来工作,还专门向上级打了请调报告,上级也批准了,但派人去调了很多次,上海不肯放。试想,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我会调一个文革中有问题的人来部队吗?上级组织部门会批准吗?"王将军还气愤地说:"现在还有人拿所谓文革问题指责余秋雨,我看是出于嫉妒,或者借此炒作出名。余秋雨完全没有必要理会这些事,这些人没事找事、无事生非,他们又在重复文革整人的那一套。"在上海建国西路一个僻静的弄堂里,记者见到了今年87岁的夏其言先生。夏老不愧为一个老报人,至今信息畅通,记者不用多解释,他已知道余秋雨的处境。他明确地对记者说:余秋雨没有问题,上海写作组系统的骨干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怎么会扯上余秋雨?清查的总结报告是我写的,到档案馆可以查到。对目前那些人的不实言论,余秋雨可以打官司。或者先警告一下,如果不听,就告他们,先礼后兵嘛! 听到这里,记者真为余秋雨捏把汗。如果这些老人都不在了,而清查档案里又根本没有他的名字,他能洗清自己吗?我们国家的文化出版界和传媒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尊重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不再凭穿凿附会的传言就随口进行带人身诽谤性质的批判? 反思文革,对在文革中追随四人帮及其党羽,舞文弄墨陷害忠良者保持警惕当然必要;但是我们同样不应淡忘,文革之席卷全国,对某一二个人的"批判"一步步酿成难以收拾的浩劫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法律的被全面抛弃,这在今天的文化人中尤其值得反思。 今天新《刑法》已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原则,谁还有权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一个公民作这样的"政治搜身"--你必须证明自己清白,否则你就有罪,你必须忏悔? 为此,记者特地拜访了著名法学专家、长期担任《法学》月刊主编、现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郝铁川教授。郝教授认为,余杰等人就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现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已经涉嫌侵犯了余秋雨的名誉权。 郝教授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侮辱"和"诽谤"是侵犯公民、法人名誉权的两种主要方式。所谓诽谤,是指通过向第三者传播虚假事实而致使他人名誉受损;所谓侮辱,是指将公民、法人存在的缺陷或其他有损于人的社会评价的事实扩散、传播出去,以诋毁他人的名誉,让其蒙受耻辱。"诽谤"和"侮辱"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捏造、传播虚假事实,无事生非;后者是利用确实存在的缺陷诋毁他人的名誉,属于"以事生非"。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余杰等人的文章中所揭露的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劣迹",经法院认定为"虚假事实"的话,那么,文章作者就属于以诽谤的方式侵犯了余秋雨的名誉权。退一步来说,即使文章中所揭露的余秋雨在"文革"中的"劣迹"完全属实,作者的行为也具有侵权的过错。因为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现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何况这一切与余秋雨作为一名散文作家的成就无关。余杰等人抖露这一隐私,并非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且诋毁了余秋雨的名誉。依据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余杰等人的行为属于以"侮辱"的方式侵犯了余秋雨的名誉权。 《新民周刊》金仲伟 《法制日报》杨慧霞《上海法制报》王抗美
|
|||||||||||||||||||
网站简介 | 网站导航 | 广告服务 | 中文阅读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帮助信息
Copyright(C) 2000 SINA.com, Stone Rich S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