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赵安(笔名“赵安之”)的博士论文致谢意外走红了。上面这段文字即出自其中。
网友们除了为文中的催泪故事感动外,也对赵安“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的经历非常好奇。
赵安的困扰也由此而来。致谢文章最初发表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一些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时,用了诸如“考研7次、屡试不第”等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标题,引起了部分读者的不适。有人质疑他是否在宣扬一种“学历至上”的价值观,致谢文章是否反映了某种“学历偏执”的扭曲心态。
“我不希望因为我没把事情讲清楚而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更不希望这篇致谢向社会传递的,是一种焦虑、偏执、撕裂的东西。”赵安说。他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详细讲述了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

赵安,博士,甘肃省镇原县人,中共党员。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求学,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曾担任村支书、第一书记,2016年出版作品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
以下是赵安的自述:
作为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能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心和祝福,令我倍感荣幸,也有些手足无措。
这个公众号是我分享生活心得的,虽然每篇文章都写得很认真,阅读量也大多只有3位数。而现在,这篇博士论文致谢的后台阅读量已经有20万了。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博士,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流量和舆论。打开留言板,大多数人都是善意和鼓励的,但这么大的流量,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人“骂”我,我都觉得我会睡不着觉(笑)。
特别是第一家来采访我的媒体,在题目中用了“考研7次、屡试不第”这样的字眼,让一些读者觉得我的心态挺“扭曲”的,好像除了考研就没有其他人生目标了。
还有网友担心,我考了这么多次,是不是智商水平不及格?这样的人也能混进博士队伍,会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还有人关心我的就业问题:“35岁的大叔才博士毕业,会不会毕业即失业?”
所以我今天接受采访,就是想把我这17年求学的“奇葩”经历讲清楚,回应大家的疑问,也澄清一些网传的不实信息。
首先,我在致谢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在网传的大多数版本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虚伪的谦辞,而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得出的实实在在的结论。
“7次考研”是真,“屡试不第”不实
首先要声明的是,“7次考研”并非“7次不第”。
我在兰州大学读本科,专业是草业科学。虽然是一名理科生,但我成长经历比较复杂坎坷,一直很关心社会问题,考研时就选择了跨考经济学。
和很多刚挥别大学的年轻人一样,那时的我,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再加上报考时目标太高、跨度太大,一头扎进了“最痛苦”的3年时光。
我是从大西北半山腰的窑洞里走出的孩子,对北上广有着天然的渴望。大学毕业,我第一次离开甘肃,南下广州,白天给地产商打工,做一些文案工作,晚上回到住处挑灯夜读,准备考研的事情。
我在致谢里写,那时候我住的是“握手楼”“胶囊屋”。很多朋友不懂,在这里解释一下:所谓“握手楼”,就是当时广州远郊城乡结合部常见的楼,楼间距非常小,相邻两栋楼的人探出窗子就能握住手。楼之间的过道非常潮湿阴暗,老鼠、虫子跑来跑去。然后楼里的隔间又很狭小,才4到5个平米,就像住在“胶囊”里。
而与我们一街之隔,就是广州的顶级社区。富贵繁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我常常从窗户看向对面,觉得这是我一生都无法跨越的距离。
我连续考研3年,最终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的通知书。与此同时,我又考上了老家的基层事业编。我选择了后者。
刚去基层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拧巴。但现在回头看,这3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重新塑造了我的三观,对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及研究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3年的含金量,绝不低于我后来拿到的任何一个学位。
 赵安和山区群众察看饮水困难问题
赵安和山区群众察看饮水困难问题我入职3个月时,恰好赶上甘肃省选派第一批“第一书记”。尽管我当年只有24岁,但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一把手的李四科书记很赏识我,以巨大的魄力选派我去担任这个职务。
我虽然是个土生土长农村娃,但到一个村里去担任一把手,这种艰难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就像沙漏中间的那个小脖子,向上要对接扶贫办、交通办、水务局、电力局,教育局、文广局、能源局、卫健局等等职能部门,所有的政策输入,都要从我这个口经过;向下则要面对父老乡亲们形形色色、众口难调的问题。
李四科书记经常夸我,说我这书记当得好,我问怎么个好法?领导立马来了一句:当了3年都没挨过打(笑)。
这些经历,把我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日后我所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都不曾离开这个母题。
在基层历练半年后,我就参加了人生中第4次考研,还是经济学专业。也许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加深了对学科的认识,也许是因为彻底放平了心态,我这次考出了很好的成绩。
但是刚到年底,我们这个村被列为市委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是全镇原县215个村里的“独苗”。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我出任村书记,在这个重要的窗口期,我没法撂挑子去读研。
第5次考研,我又厉兵秣马地报了名,还现场确认拿到了准考证,最终因为当天工作太忙,遗憾没能去考。
第6次和第7次考研,我做了一个重要转型,零基础开始备考法律专业。
如果单纯以“考上”为目的,那我这个选择显然是不理性的。但我觉得,如果继续一遍遍地复习经济学知识,纯粹是对宝贵青春的浪费。
相比于学历,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而我在当时的工作岗位上,迫切需要用法律知识来武装自己。
在这个阶段,考研早已不是我的人生目的,只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学习和体验的一个副产品。
就这样,第7次,我考上了兰州大学的法律硕士。在此之前,我还在职读完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硕士。恰好我的3年任期已满,我就心无旁骛地赴兰州读书了。
7年备考加上3年硕士在读,一共10年时间。前5年自学经济学,后5年系统学习法律。我在30岁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
我的这段经历,与其说是“7次考研”,不如说是“7年求索”。只是以考试论,7次有些太多,以求索论,7年则又太短。
3次博士答辩,无关“学术内卷”
除了“7次考研”,还有很多人关心我为什么参加了3次博士论文答辩。
有些还在读书的朋友看到这个很担忧,问我“学术有必要内卷到这个程度吗?”但其实这跟学术内卷没什么关系。
我博士一共读了4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期一年”,在博士里基本算正常速度。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涉及农民工权益中的一个“冷知识”——工伤险。
近几年,大量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涌进外卖、快递这些行业中,他们没法在城里交五险一金,回到农村只能交两险。这两险里并不包含工伤险,但他们恰恰又是工伤的高危人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几年,主要就研究这个问题。
虽然现在论文致谢“火了”,但作为一名研究者,我更希望人们来关注我们研究的这些社会问题,关心身边的民生世相。
做这类研究,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一共走访了11个省20多个县,调研了许多行业,除了外卖快递员外,还有矿工、建筑工人、玉石加工工人等。
虽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我第一次博士答辩还是没有通过。第2次再申请,花了更多的时间精打细磨,结果又被毙掉了,这大大打击了我的自信心。
导师对我说,你的观点总是哗哗哗地涌现,但这些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我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磨论文的逻辑链条,终于在第3次答辩时圆满完成。
博士是国家认可的最高学历,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我的这个过程虽然有些狼狈,但返过头去看,其实也很享受,因为扎扎实实地经历了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在思维体系上宛若涅槃重生。
这里需要弱弱提醒一句,我读博士时,每个月只能领到1250元补贴。而立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生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希望国家和社会对那些出自贫困家庭、依然怀揣博士梦想的学生,多一些理解和帮助,不要让他们因为几两碎银而中道辍足。
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
17年求学,我的经历虽然有点特殊,但也算不上什么“传奇”。如果说有什么能跟广大学子、广大年轻人分享的,大概就是:
在当前这样一个就业很艰难的大环境中,你可能不得不先去一些看起来没那么“牛”的平台历练。一些朋友会感到沮丧、失望,但我的经验是,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被命运安排在什么角落里,都应该努力地去发出光和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那这段路就一定不会白走。
就像我在基层工作的那几年,听起来远远不像在名校读书那么风光。但我不仅在艰难繁复的工作中得到了磨砺,还在没有导师指导、没有项目资助的简陋条件下,根据自己在基层的亲身经历完成了《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这本书。
如今,我国已经选派了至少数十万名第一书记。但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很少涉及诸如第一书记、基层干部、村庄治理之类的专业知识。很多年轻人来到村里,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活儿怎么干?
近几年,陆续有很多地方的第一书记来联系我,自称是《祁村奋斗》的读者,与我分享阅读这本书的感悟和收获。
这让我非常感慨:多年前我写下的一点不成熟的东西,竟然也影响了这么多第一书记。
近期,我萌生了再写一本《祁村十年》的冲动。从2012年担任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
我希望以这10年为周期,记录一个村支书和一个村庄的蜕变,通过丰富的案例,和比当年更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写出一本对人们更有借鉴意义的书籍。
相信每一个读者朋友,都有传奇的人生阅历、精彩的人生故事。漫漫征程中,山再高,人为峰,只要我们不停下攀登的脚步,那就会不断刷新人生的高度。
在对的事情上(绝不仅仅是“考研”),持之以恒地投入心血和精力,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不求速效,相信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传说。
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美国大学激情迎新演讲
美国大学激情迎新演讲 十分钟趣味世界历史
十分钟趣味世界历史 60秒动画读懂经济学
60秒动画读懂经济学 意大利美食烹饪入门
意大利美食烹饪入门 2021教育盛典圆满落幕
2021教育盛典圆满落幕 2021国际学校冬季择校展
2021国际学校冬季择校展 2021年高考报道:高考你最牛!
2021年高考报道:高考你最牛! 2019中国教师盛典
2019中国教师盛典 新浪教育#高考公开课#开讲了
新浪教育#高考公开课#开讲了 宅家战疫 直播好课不能停
宅家战疫 直播好课不能停 流行疾病如何改变人类社会
流行疾病如何改变人类社会 2020北京幼升小入学指导全攻略
2020北京幼升小入学指导全攻略 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
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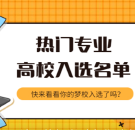 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
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 两会谈教育
两会谈教育 2022年考研直击
2022年考研直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