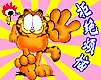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迷失的律师(3)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8 13:30 新浪教育 | |
|
实践智慧与政治博爱 手段与目的 “政治家”是一个赞美之词,我们用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对那些用非凡的智慧和技能领导他(她)们的共同体的人们的尊敬。它也是一个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家发挥才能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今天,至少在某些方面,要比过去复杂得多。任何希望了解其行为的后果的现代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些新的复杂情况。所以,他需要掌握已发明的分析方法等实用知识,从而了解现代政治的环境——从历史意义上来讲,这是与他们所描绘的社会与政治安排一样新奇的方法。但是,拥有这种方法本身并不能造就一个政治家。技术上的复杂,其意义也总是在变化,它充其量只不过是政治家才能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要问达到这一点还需要另外什么条件的话,那么,好的答案是:与过去一样,辨别伟大的政治家的共同品质(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他们是技术上的文盲)。只要有政治社会,就有政治家,并需要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艺术。从希腊时代到当今世界,像勇气和忍让是个人的美德一样,政治家才能的公共美德也一直公认地保持不变。勇气和忍让在今天保留着它们一贯的含义,我们即使在最遥远的古代也能找到令人尊敬的这种美德的榜样。政治家才能也是如此。 政治家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政治家的目标是什么,他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合理的答案可能是,政治家的目标是他或她所属的共同体的利益,政治家特殊的美德在于他们对于这一利益非凡的献身精神和辨明这一利益所在何处的杰出才能。根据这一无可厚非的观点,两个特征把政治家区别开来:首先,热爱公共利益;其次,对公共利益深思熟虑的智慧。第一点如何解释,我将在这一章的后面展开讨论。现在,我将集中讨论第二个特征,政治家杰出的判断力。政治要求那些从事该活动的人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当我们说某个人特别擅长于判断时,意味着什么呢? 从手段与目的的区别开始是有好处的。在一般的政治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问题是与其手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有关的达到某一预先目标的最佳方法的问题。这种问题假定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确定,他们只是对达到这一目的的不同方法的比较成本还不肯定。考虑手段的意义就是确定哪一种方法所需的整体费用最少。 要作出这种选择所要求的判断,人们显然需要某种共同的衡量准则,因为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不同方法的成本就无法比较。当然,人们就这种标准应该是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譬如,不同的方法是用货币成本,社会成本来比较,或者拿它们的实用性(边际的还是一般的)来比较呢?但是,如果不使用一个标准,没有人能够说某一实现目标的方法比其他方法的成本要小。两个人如果首先没能就用什么标准比较不同的方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就不能清楚地讨论手段的问题。这种问题只有在可比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才能大体上确定下来。 因此,每一个政治争论,就其关于手段的争论而言,都有一个基本的计算问题,需要计算的判断力。那么,很清楚,考虑手段最需要的技巧将是快而准地计算成本的能力。这通常很难做,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一样好。这种能力也不是简单地通过掌握一些专业方法(例如现代成本——利润分析法)就能获得的。因为要正确地计算成本,一个人首先要能区分必须计算的成本,因而需要一种感悟能力,专业知识使人容易获得这种能力但却不能保证获得这种能力。因此考虑手段不但需要专业知识也需要一种想象力。但是,基本的一点还没有变,从本质上讲,所有这样的考虑还是一种计算,虽然它不是显然的比较复杂的活动,但是其目的 是什么以及干好它的意义何在却是很清楚的。 然而,如果我们从普通意义上理解手段与目的的区别,很明显许多政治争论至少部分上是与目标相关的——追求什么样目标,如何把这些目标排序,而不仅仅是关于达到我们已取得一致意见的目标的最佳方法。事实上,许多开始似乎完全是有关手段的争论最后都要牵涉到目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它们才能确定。因此,假如追求某一目标需要使用一种实现另一目标同样需要的惟一资源,不能完全实现后一个目标很明显是实现前一个目标的成本。然而,不管它是否有意义,从纯粹的计算的观点来看,因此,是否追求第一个目标就必须取决于(除了其他的以外)我们认为这一特殊成本的大小。如果我们先不能确定这里碰巧发生冲突的目标哪一个对我们更重要,我们便无法作出决定。这提出了一个我们在开始考虑达到这个或那个目标的最佳手段之前可能没有确定的——甚至没有看到的——目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中断手段的讨论,来讲一讲目的问题。或更准确地说,因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成本,当它全部被计算出来时,可能会使我们重新评估原来花在其上的力量,我们必须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根据我们对目的的判断重新审查我们对手段的判断,或者相反。由于政治争论采取了这一更加复杂的形式,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那条清晰的界线消失了。事实上,很少有政治争论只谈论手段。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话,也提出了目的问题,而且大多情况确实是主要关心后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问:在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意味着什么。在有关手段的争论中,可以把良好的判断力认为是有良好的计算能力。但是,当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就目的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情况还是如此吗? 有些人持肯定的说法。例如,许多功利主义者持这种观点。见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道德和立法原则导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23),第29—32页。功利的价值的可比性在玛莎C·纳斯伯姆(Martha C. Nussbaum)的《善的脆弱性: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命运和伦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第89—121页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说,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有一个最高的目标,也就是说,其(总体上或者一般)幸福的最大化。当然,并不总是很清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在那种阶段性目标最有可能增进最高的最大化的幸福方面,经常出现不同的观点。但是,功利主义者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大体上总是一致的。确定非终极目标能够带来总体上的最大化幸福。在他们看来,共同体的最终目标就为评价其他所有目标的价值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认为每一种目标都带来一定的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相同的基本利益。从共同体的纯粹最高目标的有利的方面来看,这些其他的、次要的目标在性质上分辨不出来。因此只存在一种任何一个目标都可以优先于其他目标的理由,即它带来大量的使每一个目标都具有价值和吸引力的相同利益。所以,如果功利主义者是对的话,而且这确实是政治中考虑目的的情况,那么这种考虑一定也是一种计算形式,它所要求的能力与只用于选择手段的能力一样没有区别。 也许,功利主义者经常主张考虑目的的政治争论。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带来最多的一致同意的公共利益。然而,事情总是这样的吗?不让步的功利主义者当然说是。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一答案,尽管任何有关目的的争论都可以从表面上让人觉得只要通过计算就可以解决。因为,如果有一些政治争论最显著的特征不模糊的话,即参与者认为有关的不同方法所要实现的价值是不可比较的,那么,就不能这样描述。 实际上,仅仅从非常含糊的观点来看,任何政治争论中的互相冲突的价值都是可以比较的。这正是功利主义者采取的战略。但是,即使人们总是能够制定一个抽象的标准来比较不同的目标,必须在其中作出选择的政治家可能就会发现这一做法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可能提出反对,“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幸福或财富是什么,或所需要的其他是什么,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把我们区分开的就是对这些含义的分歧——幸福和财富由什么构成——把我们每个人的地位看做是获得这种公共利益的一种努力的观点无助于解决这一争论。” 在他们看来,就会使上述观点在有些时显得如此的没有价值,原因就是这样的事实:对政治家而言,它是从他们所处的最重要的地位的特殊特征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其价值无可置疑地降低了。抽象在政治争论中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有时也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关于目标的争论,其含义与它们的一些具体特征密切相关,把它说成(就其提出者而言)是对实现某种较高层次的目标,如幸福的最佳方法的意见分歧是无什么好处的。根据这些政治家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不能接受的含义上的偏差的话,不同的目标是不能相比较的。从总体上来讲,忠实于不可比的经验似乎比可比性会带来的好处,这一点因事因人而异,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性情和爱好的问题。但是存在着诸如此类的观点,它们很容易渗透到政治争论和其他争论中去。 当然,在我所说的意义上,两种利益不能相比较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不能理性地思考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假如它们带来的欢乐或成就如此不同以致把它们说成是某一更加基本的共同利益的例子,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一种选择被证明比另一种选择要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时机的选择及不同利益之间心情的和谐与不和谐等因素经常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个人的考虑中,这是普遍情况。因此,如果我喜欢看书和看电影——假设这两种活动给我完全不同的快乐——我会决定在看电影之前,先看拍摄这部电影所根据的书,如果这样做有利于增加我对电影的理解的话,或者使我的想象力不受电影中的可看得见的形象的限制的话,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利益可能是不能相比的,但我仍有理由先做一个,再做另一个(一个选择时机的问题)。我也有理由为了丰富多样,做每一个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对我来说,看一部电影的快乐可能被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或之后读有关它的评论所破坏,所以这种特别的读书至少在我的生活中不能与看电影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政治与这些个人判断有类似之处。食物与文化都好,但是,除了某一点外,它们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满足是不能相比较的。一个社会在发展文化之前先保证其成员有足够的食物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不能饿着肚子去享受文化的快乐。与此相似的是,自由与平等都是值得追求的理想,虽然它们的价值不能够用某一相同的原始利益来衡量(不管是幸福还是财富或其他东西)。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拥有这两个理想比只追求一个理想更好。一个对表达自由原则作出基本承诺的社会可能会发现其他价值(像爱国主义和宗教感情)不能与这一原则和谐相处。可以把所有的这些重新说成是对计算分析和判断的修正。然而,即使我们抵制这样做的诱惑,坚持所涉及的价值不能相比较,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由于时机或者心情的原因,可能会有惟一正确的选择。只要这种理由存在,政治家才能就是辨明它们并使人们了解其力量的一种艺术。 然而,如果无论在什么时候计算都不能在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作出选择,为其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基础,那么根据思考的时机与心情来做这一点,将是错误的。这既不是个人选择也不是政治选择。在个人层面上,我有时被迫在对我来说完全不同价值的活动和那些相互之间没有自然因果关系或者不同程度地支持我所坚持的其他价值的活动之间作出选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听演讲和听音乐会之间进行选择,它们都只有一次并且同时举行。另一个更加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杰—保尔·沙特作为公民和儿子在参加反侵略活动与呆在家里保护他的母亲之间作出选择。杰·保尔·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义和人类情感》,伯纳德·弗莱克曼(Bernard Frectman)译(纽约:哲学图书馆,1957),第24—25页。 在政治生活里也发生相同的事情。在政治生活里,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的相似选择。是否建一座将给某一地区带来电力但却破坏鱼类(它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只是与其他相近的种类有遗传学上的区别)的大坝?是否为最近的有争议的战争中的老兵建一个纪念碑,如果要建,它应该写什么或者代表什么?一些犯罪是否应该判处死刑?妇女是否有根据需要堕胎的权利,如果有,有什么限制?这些是美国人近来一直在争论的真正问题。每一个问题上的分歧都不是仅仅靠计算就能解决的。考虑时机也不能解决这些争论中的任何问题。虽然,在每一个争论中持两种不同意见的人指出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重视的其他价值、先例和做法,然而,争论者一般都不能就哪些是最重要的和值得尊敬的观点达成一致的看法。在所有的这些争论中,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相距太远,都不能表达某一单一的根本利益,时机和心情等因素不能为决定哪一个优先提供一个共同基础。 诸如此类的政治选择相当普遍,正如一些事例给我们的提醒一样,它常常带给我们巨大的痛苦。当然,即使假定相互冲突的目标是可比较的,每个人都同意在它们中间选择一种计算方法,但是,这个选择本身可能是痛苦的。这是因为当我们选择一个目标时——一个产生整体上最大化的幸福或财富的目标——我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放弃其他对我们也有价值的目标。如果我们的行动不受资源的限制,我们也会去追求其他目标。这样,资源就会使对可比较的目标中的理性的正当选择变得难以接受。当目标不能相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时机和心情等独立的理由使得一种选择优于另一种选择变得合理。然而,如果政治目标之间不能相比较时,那么也就不存在这种理由,或者其本身是有强烈争议的主题,那么作出的任何决定都一定缺乏理由,这种缺乏的理由又成为相关人日益痛苦的源泉。 这一点在失败者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们作出的选择在现实中已经最好地满足了他们的最高价值的思想,却不能使他们得到安慰。他们不仅失败了,而且,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失败是独裁的和不合理的。也没有把胜利者排除在这种不幸之外。马克斯·韦伯曾经观察到,每个社会的富人和强者不仅需要保护他们的特权,而且认为他们是通过正当途径得到了财富与特权。他说,要相信这点,就要说服那些比较倒霉的人,使其相信他们的失败也是应该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学”,载《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H.戈斯(H. Gerth)和C.瑞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第271页。同样,任何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不仅要享受胜利的成果,还要失败者承认他们的失败是合理的。然而,没有理由的选择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它使得胜利者对自己没有得到的好机会感到焦虑,正如使失败者认为自己的倒霉是不合理的一样。 当然,如果这种决定无足轻重(像我在演讲和音乐会之间作出的选择),要求作出缺乏理由的判断就不可能会令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认为,作出决定的最好方式是借助某些随心所欲的程序,如抽签。但是,当政治选择涉及到重大问题时,没有根据的决定常常带来许多特殊的焦虑。当这一选择关系到一个共同体的身份——关系到其成员认为对他们的共同生活而言是最基本的承诺和目标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是一个共同体作出的最重要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这个目标而不是别的目标等于是一个共同体表明其自己的价值的宣言。因此,政治选择越接近于自我界定的问题,就越不可能有作出这一选择的一致同意的标准,因为这种问题的争论经常超出了这些标准本身的内容和范围。因此,如果一种选择看起来更像一个共同体的自我宣言,那么它就可能比较重要,但同时任何作出这一选择的决定可能更加缺乏根据。 这里我对政治家才能的解释明显地陷入了僵局。只要能够用计算的方法来回答政治问题,或者根据一致意见的时机和心情等因素来解决政治问题,要求什么类型的思考程序、深思熟虑的含义是什么就变得很清楚了。然而,就在这些情形下,对相关的共同体来说,所提出的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可能最迫切地需要政治家才能,作出缺乏根据的判断似乎排除了我们主张一些人在作出选择时比其他人具有更好的判断力的所有根据。在这类重要的争论中,它似乎剥夺了我们确定政治家的杰出判断力的所有基础。因此,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政治家艺术的本质就变得含糊不清。 在这点上的争论每前进一步都变得相当困难。要么,似乎有解决政治争论的共同基础,要么没有——因为当相互冲突的价值不能相比较时,选择时机就无关紧要,任何与问题有关的心情因素与价值本身一样也可能引起争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抽签是与其他方法一样好的选择方法,并且成本也要低得多。无疑,抽签本身并非深思熟虑的一种形式,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根本不需做任何判断。有人也许会争辩,政治家不同于他人之处正是在于,在进一步的深思熟虑不起作用而需要采取更简捷有效的方法时,靠他的才智来作出判断。亚里士多德说,知道对不可能的事进行深思熟虑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智慧的象征。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基伦理学》,1111b20—30。因此,能够看到对只有无根据的答案的问题进行深思熟虑是没有意义的,并建议用一种简便但随意的方法作出决定也可以看做是政治家才能的一个标志。 然而,这一结论把我们普遍的政治家才能的概念搞颠倒了。因为没有肯定大多数人相信的观点——政治家是靠其对最棘手的政治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杰出才能来加以区别的——而是解释他知道某些分歧不能靠深思熟虑的方法解决的原因,因而就放弃这种努力,而其他的人则愚蠢地坚持对这些分歧进行深思熟虑,然后才能解决问题。这一观点不但与普遍接受的政治家才能的含义相冲突,也导致令人不安的结论,即解决那些与一个共同体的基本承诺和理想有关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某种诸如抽签之类的随意程序。我们本能地觉得这是错的,并觉得即使我们所有的决定缺乏我所讲的意义上的根据,对这些选择进行深思熟虑也是重要的。然而,事实上,此类情形下的深思熟虑有没有意义呢?深思熟虑意味什么呢?下面的研究将把我们带到这些问题上来,为了理解政治家才能的艺术,我们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为自己创业》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