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丰收”合影,在中国科学院大学7月3日举行的2022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被国科大党委书记、校长李树深院士“点名”。
照片里 ,三名学生簇拥着国科大现代农学院专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勇,背后是一片即将成熟的金黄麦田。照片右下方写着:2022年6月,河北高邑。
在国科大,今年有6493名博士生、6075名硕士生以及371名本科生获得学位。部分人因科研任务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他们把最后的毕业回忆留在了各自的科研基地。这三名学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张合影同时定格了粮食丰收的景象和学业丰收的幸福。”李树深在毕业典礼现场说,从国家级种质资源平台,到“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从培育良种到保护耕地、开发边际土地,学生们真正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国科大2022届遗传与发育专业毕业生和导师在河北高邑的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国科大2022届遗传与发育专业毕业生和导师在河北高邑的毕业照。受访者供图15万株小麦收割的“毕业任务”
站在照片最左边的是国科大2022届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杨翼骏。就在不久前,他和师门同学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们凌晨5点出发,拔掉了4.2万多单株小麦。
对于2022年应届博士毕业生郭广昊,这片麦田有着特殊的记忆。从硕士到博士,长达7年的时间,他是在这里度过的。今年毕业,因疫情防控加上恰逢麦收季节,他和师弟们选择了留在这里,任务是收完15万株种在基地的小麦实验材料。
拔麦,是开展田间试验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秋季,播种会根据研究需求去设计不同实验材料的种植规模、种植方式。到了收获阶段,大部分遗传研究材料要以单株为单位收获,并对每一个单株进行性状调查,分株采集叶片样品提取DNA,展开分子检测,进而定位所研究性状的目标基因。
“在育种上,选择是相互且残酷的,你在选育材料,材料也在选择你。” 杨翼骏解释,如果要研究小麦中的抗病基因,需要进行人工接种鉴定,“不能单纯靠天吃饭,如果气候和环境条件不适宜,鉴定的材料不发病,那么一年的时间就浪费了。”
为了找出小麦抗白粉病的基因,郭广昊在这片小麦田里“死磕”了近5年。通常,小麦植株一旦染上了白粉病,叶片会出现白粉状的霉斑,使小麦叶片失水枯死,严重影响光合作用,穗少粒小,产量下降。农民要控制白粉病,只能依赖打农药的方式,不但费时、费力、费钱,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
3705个遗传分离群体单株结出来的种子,是郭广昊的研究切入点。他的任务是找到能抗击白粉病的基因。但这显然并非易事。
从微观层面来看,小麦有十万多个基因,需要逐步精细定位,一步步挨近目标基因,待找到目标基因后完成克隆。当时国际上对小麦该类抗病蛋白的研究还较少,能利用的资源有限,能提供的学术参考资料也极少,这是一个还未被探索的科学“无人区”。
那一阵走在麦田里,郭广昊有一些恍惚,总感觉麦田就像是一片荒漠,要在大漠里找到一粒沙子,“难于上青天”。
他只能不断地试错、不断地缩小范围,“一点点地接近真理,等到发现它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对它展开功能验证。”那时,他心里记着导师的一句话,“做科研千万不能浅尝辄止”。
基于前几届师门不断累积的资料,郭广昊和实验室的伙伴们找到了破解之法:他们利用收获的几千棵小麦的DNA样品,通过创新的生物信息学方法,成功克隆到抗白粉病基因。
随后,他通过转基因的技术将该基因转移到感白粉病的小麦中,在温室和田间展开表型鉴定调查,反复验证,成功地克隆了小麦抗白粉病基因Pm5e。研究成果在专业学术期刊《New Phytologist》上发表。
在聊天群里,导师给他发了一句话:恭喜小伙子,苦日子熬到头了。
麦穗里结出“果实”
在不少人看来,做农业科研是极苦的。
到了麦收季节,老师和学生们凌晨5点要起床下地,待太阳出来后,有时室外作业温度高约38°;科研基地位于河北高邑,方圆几公里见不到高楼大厦,大家想打打牙祭,得骑上三轮车去集市买。
但在实验基地里,老师给学生的硬性要求是,每个人、每天必须要吃上一颗鸡蛋、喝上一盒奶,才能下地干活。
没人因吃不了苦而离开。
这群年轻的学生聚在一起“苦中作乐”。他们总结了拔麦子的四招“武功秘籍”:如果你爱健身,就采用一招屈膝式的“招数”,提臀、用背部发力,能锻炼背部力量;如果个头较小,可以采用站立式,拔麦子时气沉丹田,集中发力,但要防止弄断小麦的根部,伤害了材料的完整性……
曾经有一位外省的农业教授来调研,看看50多亩小麦试验基地说,“你们的工作量很大”。刘志勇陪同着说,“一届届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在传承了。”
在这片小麦田里,传承着什么样的精神,从毕业学生的成长故事里或许可以找到痕迹。
1998年出生的河南信阳小伙符宏奎今年刚考上国科大研究生,来基地3个多月后,习惯了带着绳子、纱网袋出发,凌晨四五点在田里干活的日子。
在一次观察中,符宏奎发现了一颗有特殊表型的单株,一时好奇心大起。师兄告诉他,做判断之前,要先排除是否是人为因素的误差,比如是否有去年的种子混在其中,种植的方式有问题等,再通过检测等方式进一步去验证。在基地待了3个月后,符宏奎慢慢领悟:他想“生长”为一个思考全面的科研人。
自诩从小爱偷懒、耍滑头的杨翼骏改变了不少。刚在田间做试验时,师兄张怀志带着他去给小麦系牌子——为了试验分类,需要把标签牌捆绑到对应的单株麦穗上,有时得借助胶带固定。师兄反复地叮嘱:胶带和塑料牌会破坏农田环境,等解开绳子后,一定要把难以降解的材料从麦田里带出去。
另一个被传承下来的习惯是,每逢收获季节,无论是哪位成员种植的试验材料,一个课题组的人都会抱成团,一起扛着工具去地里割麦子。要是碰上雷阵雨,大雨哗哗地下着,一群研究生们拖着20多斤纱袋的小麦,紧跟在收割机后狂奔,几个人合力,一把将麦子扔上了车。
看着这群学生,刘志勇想起了1993年自己读研究生的那段时光。他师从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学习小麦遗传育种。那时候每天晚上,孙教授忙完了事情,就给研究生们“开小灶”学英语。孙教授常说,要学习最先进的技术,要不怕困难,要扎扎实实地把小麦育种工作做好。孙教授还告诉同学们,当年,他的老师蔡旭——中国科学院院士、小麦栽培及遗传育种学家,也是如此教导他们的。
6月,是小麦收获的季节。麦穗结出了果实。学生也从这片肥沃的麦田里结出硕果,学有所成。
“希望你们能够志向远大,脚踏实地,在生产和育种实践之中发现科学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攻坚克难,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解决科学问题,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刘志勇对两位毕业生寄予希望,鼓励他们带上研究成果,无论走到何处,都要把小麦的好基因留在这一方水土。
 国科大2022届遗传与发育专业毕业生和导师在河北高邑去往麦田的路上。受访者供图
国科大2022届遗传与发育专业毕业生和导师在河北高邑去往麦田的路上。受访者供图在国科大毕业典礼上,李树深院士寄语毕业生们:希望做一粒种子,向下生根、向上生长;做一颗星星,努力发光、用力闪耀;做一滴水,清澈纯粹、坦荡坦然。
在郭广昊的回忆里,麦田里的科研生活是坦荡自由的:他曾看着小麦抽穗开花、变黄结穗;和研究所老师、同学们组成两队打篮球比赛;还有在傍晚,他们搬出唱歌机,把屏幕打在露天一堵白墙上,围在一起唱歌,有人爱当下最流行的新裤子音乐,有人爱唱周杰伦的歌,还有人总会唱上一首《鸿雁》……
毕业后,从小在山东农村长大的郭广昊选择继续从事小麦研究,把它当作一辈子的事业。他说:“农业科研就像是一场修行,一半是初心,一半是克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洁




 2022全国高考报道
2022全国高考报道 #高考公开课# 6月最新课表来袭
#高考公开课# 6月最新课表来袭 最热!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
最热!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 2022年双一流大学高考招生章程
2022年双一流大学高考招生章程 美国大学激情迎新演讲
美国大学激情迎新演讲 十分钟趣味世界历史
十分钟趣味世界历史 60秒动画读懂经济学
60秒动画读懂经济学 意大利美食烹饪入门
意大利美食烹饪入门 2021教育盛典圆满落幕
2021教育盛典圆满落幕 2021国际学校冬季择校展
2021国际学校冬季择校展 2021年高考报道:高考你最牛!
2021年高考报道:高考你最牛! 2019中国教师盛典
2019中国教师盛典 新浪教育#高考公开课#开讲了
新浪教育#高考公开课#开讲了 宅家战疫 直播好课不能停
宅家战疫 直播好课不能停 流行疾病如何改变人类社会
流行疾病如何改变人类社会 2020北京幼升小入学指导全攻略
2020北京幼升小入学指导全攻略 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
2022职教高考专题报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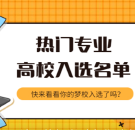 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
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 两会谈教育
两会谈教育 2022年考研直击
2022年考研直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