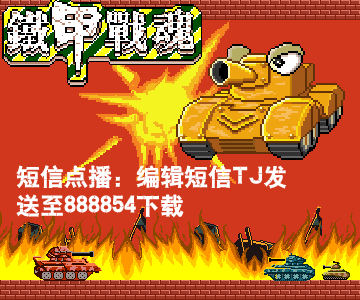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
4月1日中午,北京市蓝旗营小区某居民楼一个“学生公寓”里,本科毕业后从福建来到北京、尚未找到工作的小任正在电脑上玩游戏,他的床头贴着“努力”、“奋斗”4个字。
这个宿舍的7个人,要么是从外地来北京考研,要么是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找工作。整整一天,只要有人在,这里总是充满笑声。
但并不是所有流动知青的生活都这样快活。“流动知青在整个知识青年群体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些年轻人缺少经验、缺少社会关系,往往处于工作、生活的极大动荡中。社会位置漂浮不定,对很多流动知青来说是常态。”周拥平说。
孙晓芸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月薪是200元。她干得很苦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省钱,她吃、住都在学校,“我想存钱,贴补家里”。为了多赚钱,孙晓芸曾去抄信封,抄一个信封赚3分钱,她最多时一个晚上抄了400多个信封。
工作了两年多,孙晓芸总觉得失落,于是参加了成人高考,在北京大学读夜大,学习财会。这次读书,她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学个能谋生的专业。3年后,她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找到第二份工作———做社会调查,月薪400元。为了省钱,她在北京大学旁边跟另一个女孩儿合租了一间平房,每人每月30元,房子没有暖气。“吃饭、洗澡什么的还是在北大,便宜。”
之后,孙晓芸又换了几份工作,有几年就住在办公室,连租房的钱都省了。“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苦,现在回过头来看,挺心疼自己的。”她从不吃早饭,午饭就吃1.5元一个的煎饼,整整吃了一年。
几乎每个流动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陈颢庐至今还记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场吃盒饭时碰到的那些别有意味的笑脸。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还是到劳动力市场去试一下。”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没多久,陈颢庐的钱快花光了,因为他是自作主张来北京,家人拒绝提供援助。连吃了3个月方便面,他开始掉头发。为了补充营养,他买来韭菜,用开水反复烫熟,撒些盐,强迫自己吃下去。
目前的陈颢庐已经在筹办自己的文化公司。说起那段日子,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记得当时绝望之下,他曾给姐姐寄去一幅画:一个小孩,端着碗站在路边,旁边写着一行字———大爷,行行好,赏点米吧!姐姐收到信后哭了,给他寄了2000元钱,他得以活下去。“那时候,我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消失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首先得活下去。”
几经周折,陈颢庐在一家酒店找到工作———洗碗,每月300元,这些钱他大多用来订报纸,了解各种信息。老板有一次表扬他:“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订报纸的洗碗工。”
工作两年,攒了点儿钱,陈颢庐终于作为旁听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过,已经毕业的他,又有了新的苦闷。“不想做但不能不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陈颢庐开始怀念自己丢掉的很多东西。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