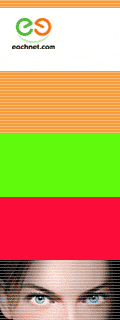|
作者:余云华
1978年春天,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我提着一口旧木箱,找到了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的迎新车。那一刻,人生若梦的感慨强烈撞击心头。
此前数月,秋天的下午,我正在聚精会神背《药性赋》:“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犀 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兴高彩烈的堂兄一步跨进大队合作医疗室,见我手头拿的药书,满脸惊异:“你还不晓得呀?现在时兴考试啦!好多人都在忙着复习哩。”我已从隔壁小学校的广播里隐隐约约知道这事儿,但压根不相信:推荐入学这么多年了,头儿们的屁股后面,子侄老表、三亲六戚跟了长长的一排,非亲非戚又不掏大价钱,休想入列。见我心如死水,堂兄很着急,第二天便找来一篇《人民日报》,免不了又苦苦劝说一番。
堂兄的工作没有白费,中学时候的雄心穿过层层冻土,“那就试一下吧!”
1977年的12月,我挤进了考场,心想:读了十多年书,终于有机会参加考试,该心满意足了。
考试的第二天便一头钻进药房,岂料没有多久,通知进城参加体检,这可犯难了:考试在公社中心小学,费不了多大事,花不了多少钱。而进城一趟,单是车费,也需花一两块钱啦——当年,大劳动力一天10个工分,值一两毛钱。更重要的是,高考会当真么?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再去浪费,值么?我犹豫不决。大队小学的一位当年和我一起高考老师平日与我谈得来,他说:“进城住我亲戚家,不花钱。管他是真是假,不就两三块钱吗?”卖了几十个鸡蛋,便到曾经读过书的县中体检。医生们都用另样眼光看待这群30岁上下的“老三届”,不是大问题一路绿灯。世风真的变了吗?
1978年初春,小学开学了,那位小学老师接到了重庆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县里派下来的工作队长马上通知我接替这位老师的工作。我真的有些高兴了:没有找任何人说情送礼,社会确实在变。我正准备当一名工分教师,三天过后的中午,有人在村旁的水沟边,高声呼喊:“余云华,快到乡邮递员那里去拿录取通知书!”这一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匆匆跑去,迫不及待的打开,确定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才想起:填志愿时,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又逢场作戏,照抄身旁的一位教书的老同学的志愿。不错,第一志愿录了我。
我如梦初醒:中国真的变了!
人的一生,没有比“金榜题名”更高兴的事了。我家住川东农村一个叫杨家祠堂的地方,不用说是杨姓天下。父亲抱定一个信念:为了不受欺侮,显耀门庭,砸锅卖铁地供我读书。他挑担挣钱,爬山涉水不穿草鞋,家中盐罐时常刮了又刮。就这样还得凭助学金的支持,才从小学念到高中,后来不巧被“文革”赶回农村。在杨家祠堂脚下的农田里,我是解放后培养的唯一的高中生。可我的“字墨”得深深掩埋,举荐决定命运,单家外姓,且不送礼,那就心安理得的修地球吧!哪知喜从天降,命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家徒四壁喜若狂!
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国家洗新革面兴利除弊的关键时期,变化太快,一天绕过20年。我这个土得掉滓又与世隔绝的川东农夫跟不上趟,尤其是考大学的数月间,告别恶梦,一个好梦接着一个美梦:1977年秋天,我在大山深处的农舍里,给一户人家做陪奁木器。父亲翻山越岭找到我说大队让我回去。我吓了一跳:一天收入一块二,上交七毛,一分不少哇,让我回去干什么?又要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么?唉,又要挨整了!我心急如焚赶回大队,县里来的工作队长笑嘻嘻地说:“大队合作医疗要搞起来,为贫下中农做点实事。你是老高中生,来吧!”我有些发懵了,第二天走马上任,心里疑团难解:九年木工生涯结束了!
就这样,半年左右,我从一个公社社员、农闲时背着木工背篼钻进大山沿门讨活的木匠,一夜之间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跃升到另一个新台阶,成为大队小学的工分教师,还没有走到土黑板前又打住,平地一声春雷,摇身一变成为“文革”后首批大学生。
所以,我的真实身份是农民,是贫农,是老贫农。当我告别三个孩子,走下迎新汽车,走近新生报名处时,同学们都睁大了眼睛,他们开始还以为我是送孩子来读书的农民哩!四年的大学生活,一些同学也许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一提到“贫农”,他们都心照不宣。
一直到今天,中国农民的禀性还跟我和平共处:干实事,守本分,无奢求,不烧香,也不叩头。因此几十年磕磕绊绊,在生命的秋天才躲进平静的大学校园,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事儿:民间文化。
余云华简介:男,1947年10月生,当过农民、木匠、中师教师,现为西南师范大学民间文化学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中国隐语行话研究会、四川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四川民俗学会、重庆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发表学术论文和著作200余万字。
新浪天堂隆重发布,百万玩家迎接公开测试
| 
![]()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