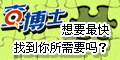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尊 严 DIGNITY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11/13 13:58 新浪教育 | |
|
参观位于华盛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前,我还是相当犹豫的。上小学时,被少先队辅导员领去参观过万人坑,我被累累白骨吓得当场吐了,在随后好长时间里吃不下睡不着,晚上连眼睛也不敢闭上。所以,第二次游华府时,才鼓起勇气去排队。 进了门,就直接被带到了电梯口,电梯旁,放了许多制作成像护照一样的小册子,每个册子上都有照片,记载了他或她的简要生平和在大屠杀中的真实经历。从我拿到的名册上 “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bear witness (为了死去的更为了活着的我们承受一次见证)”,这是印在名册封面上的一句话。虽然馆里没有像我预先想像的那样赤裸裸地陈列着累累白骨,但也布置得阴暗沉重,置身其中,仿佛是在纳粹集中营里一般。手里拿着这个小册子走完展厅全程,我真的像亲身经历了一遍Jovanka所遭受过的屈辱和苦难,好像自己也穿了那件囚衣,正在人性的暗淡中一步步走向毒气室,我身上的膏脂也将被做成肥皂,我头上的乌发也会被剃下用以证明我非雅利安的劣等血统,而我能留给女儿的也许只是脚上的一双鞋子,如果她还有勇气去刨那堆鞋山。 展程的最后,还有一个影像厅,循环放映着对几个幸存者的访谈。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却都衣着光鲜,精神矍铄,除了眼中偶尔的泪光,叫人一下看不出苦难的痕迹。连他们讲述苦难的语气,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平缓和隐忍,而完全不是我习惯了的那种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令我多少有些诧异,但心灵的震撼却似乎因此而加倍。特别是,他们的回忆里常常提到的故事,是诸如母亲如何留下一双皮靴叫女儿捱过了冰天雪地里的跋涉,就像是黑白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那惟一的一抹红,叫人过目难忘,挥之不去。而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一个妇女淡淡讲述的故事。她说,当盟军来到她所在的集中营时,她已经被摧残得羸弱不堪,和其他人一起被关在一间地下室或是类似的黑屋子里。当屋子的门被打开,与久违了的阳光一道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只向她伸过来的手,“Madam(英语里对妇女的尊称)”那人这样叫着她,她说,就在听到这个称呼的那一刻,她恢复了被剥夺已久的做人的尊严。听到这里,我好像也有了种被解放了的感觉。紧接着,她又幸福中略带羞涩地补充了一句:“那个人后来成了我的丈夫。”当时,我就差跳起来大声喝彩了,好像一部令人窒息的灾难片看到最后,终于等来了一个明媚的结尾。 我始终没搞清这个纪念馆是怎么设计的,一进门就被电梯直接送进了幽暗的展厅,等参观完就不知不觉地又走回到了进门时的大厅。那里有个洁净的缅思厅,当我终于走出黑暗,在那里停下脚步时,我情不自禁地点亮了一根蜡烛,为Jovanka,也为我自己。 就这样,除了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大屠杀纪念馆也赢得了我的深深敬意。 海燕: 听过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兴奋呢?对于被人性的黑暗抛入灾难的人们,能拯救他们的最终还是人性的光明。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盟军士兵的彬彬有礼以及他的爱情,带给这个世界的,岂止只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重获的尊严与幸福,它至少让我们有理由对人性充满信心。不是吗? 而这样的一个纪念馆,更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尊严。咱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始终没有机会去参观过,不知那里展现出的是否也是尊严大于屈辱。近来好像听说,纪念馆外的路上又印上了许多当年幸存者的脚印,在我看来,这要比用受难者的累累白骨展示屠夫的凶残更具创意,至少它在以生者的不屈不挠向世界宣示尊严,还有希望。 关于尊严,海燕,在咱们受过的教育里,还是有的,至少比一穷二白的性教育要好些。回想起来,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从电影、书籍里看到的革命烈士上刑场前的大义凛然了。比如,女共产党员江姐换了身衣服理了理头发的从容,抗日英雄吉鸿昌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豪迈,到如今我都记忆犹新。特别是吉鸿昌的副官临行喝罢一碗酒长笑而去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用今天时髦的话说,简直就是“酷毙”了,以至于那个配角演员几乎成了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对他,我虽然没有条件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如影相随,凡有他出场的电影我还是每部必看的,好在不多,票价也不高,还看得起。 至于一个非革命者的尊严该如何,我却是没什么印象的。海燕,你有吗?我是说,像你我这样不闻一名的普通人,该如何活得有尊严,有谁教过我们吗? 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不经意地在电视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身材瘦小的黑人妇女在接受授勋,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漫不经心地看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听一个黑人同学评论说,那根本上是“a victory of dignity(尊严的胜利)”,我才第一次了解这个黑人老太太在美国历史上以及人们心目中的显赫:她被认为是“a persistent symbol of human dignity in the face of brutal authority(一个面对强权时人类尊严的持久象征)”!她的故事是这样的:1955年12月1日,在当时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阿拉巴马州(Alabama)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这个叫Rosa Parks 42岁的黑人妇女在乘坐公共汽车时,因为疲累而坐到了黑人免坐的白人专座上,并拒绝为一个白人男子让座,当白人司机警告她会因此被逮捕时,她只是平静地回答:“You may go on and do so(悉听尊便)。”她果然被送上了法庭,而由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借机发动和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则由此星火燎原。后来我又看到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戴着眼镜穿戴得体的Rosa Parks坐在公共汽车上,头望向窗外,依然散发着一种宁静的力量,而在她的后排,则坐着一个同样安详的白人男子。照片是摄于1956年12月21日,就在那一天,一年前导致Rosa被捕的种族隔离在蒙哥马利市的公交系统被全部取缔!海燕,我得承认,在此之前,我也许偶尔被普通人的尊严打动过,但真没怎么在意过尊严之于非革命者的意味,以及蚁民尊严的力量。 海燕,你是否同意,在我们的成长中确实是缺了这一课的?就在昨天,我到一个芬兰朋友家看她给几个小朋友上艺术辅导课。其中一个叫Robin的四岁男孩儿显然有些吃力,嘴里不住地嘟囔着“I don’t like it(我不喜欢这张)”,画一张扔一张,直到最后难过地趴在了桌子上。比他都大了两三岁的几个女孩子则都不约而同地对他说,没关系,Robin,我觉得你画得挺好的,一个叫Andian的女孩儿说完“I like it(我喜欢它)”之后,似乎还觉得不够分量,又加重语气地补充到:“I like it a lot actually.(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它。)”我在一边看着,不由得又想起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在跟Andian差不多的年纪上做过的一件事。 那时,我大概在上小学一二年级,作为班长,我每天早自习时要带着全班同学复习字词,就是老师预备了一些大字卡片,我站在讲台前把它们一一亮出来,全班同学就跟着一起读,我也有权叫起任何一个同学单独读。班里有个学习很差的男生,因为面部长得不很饱满,得了个外号叫“大老瘪”。有一回,正好复习到“瘪”字,大家读后都向他看去,他涨红了脸低下了头去。等又轮到举起瘪字时,不知是出于对他消极怠工的憎恶,还是纯粹的恶作剧,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叫了起来,全班哄堂大笑,他的脸涨得更红了,倔强地将头扭向窗外,拒不做答,但同学们的心领神会叫我觉得受到了拥戴,快意盎然。老师不在场,也没人打小报告,“大老瘪”更不可能自己去告状,这件事就像很多的事一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所以,海燕,你可以想像,在看到那几个外国小朋友懂事的样子,我是怎样地羞愧!而且,一想到那一次因我的无知而造成的羞辱可能会成为那个男生一生中的阴影,我真的是追悔莫及呀。如果当时能被老师家长发现,狠狠地批评我一通,哪怕是叫我当众道歉,我都会早一点了解人生来都是有尊严的,即便他是一个考试常常不及格的差生。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尊严的正面教育缺席了,而相反,对于尊严的剥夺,我们倒见识了不少。记得从我还没入学的时候起,就一直有机会参加公审大会,它们大多是在街上举行的,高音喇叭广播得几条街都听得清楚,而且它们还是流动的,公审车开到哪儿哪儿就像过节一样热闹。被打击的犯罪分子,我见过的都是五花大绑站在敞篷卡车上被押着向人民低头。那时候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人民,爱哪儿热闹往哪儿钻,一次就钻到了审判前沿,仰头就看到了那几个“罪恶多端的无耻败类”,一个家伙似乎还冲我挤了挤眼,可旁边一个就真的是直勾勾恶狠狠地盯住我,像是一旦挣脱了捆绑他就要把我一口吞了,吓得我立即转身往家跑,听邻居大人说,那里面还有对面街上的谁谁家的儿子,我听了,真怕等他再放出来的时候能认出我来。类似的公审大会,直到我上高中了还在参加,不过那时都是在学校礼堂里,都是些据说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反面教材,但是只争朝夕的我们大多还是忙着在底下偷看“正面教材”。 海燕,这样的事情在你们的县城里也有吗?可不管你见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你都不会否认,我们这一代就是在这样的混沌里长大成人的,以至于到了21世纪仍不得不为它尴尬着。我经历过的一次尴尬是这样发生的:在海外的课堂里,当一个惯于哗众取宠的教授用匪夷所思的口气讲述中国的死刑犯家属曾被要求支付子弹费时,我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们果然一片哗然,而这回,涨红了脸无言以对的是我——课堂上惟一的中国人。当然,尴尬并且应当羞愧的不该只是我一个人。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四川的一个九岁小学生向伟只因一道数学题做不来,老师讲三遍后仍摸头说不知道,恨铁不成钢的老师居然就一脚踢向其下身,踢得孩子鲜血直流,不得不接受生殖器缝合手术!海燕,我儿时那次对尊严的冒犯,毕竟是因为还小还蒙昧,加上那时候的教育还有缺陷,可是,二十多年过去后,仍旧视尊严如无物的却是一个以启蒙、教育下一代为职业的老师,这可叫人说什么好呢?! 当然,时代到底还是在进步,同样是从互联网上得知,现在在咱国内,不仅定罪前的“犯罪分子”都改称了犯罪嫌疑人,连处决也开始采用注射死刑了,为国家机器节约了成本的同时,十恶不赦的罪犯也能求一个好死了。可是,海燕,我还得说,虽然我举双手赞成这个人道主义的进步,可有时也难免有些不平衡,似乎戴罪之人反倒比咱们良民更快地找回了尊严。这有点像在我们常搞的卫生大扫除过后,明显变干净了的一定是脏乱差的卫生死角,而窗台桌面上的灰可能反倒被忽略了,而我们自己呢,可能扫除一过,要吐的痰还会照旧随地吐、要扔的冰棒纸还会当街照扔不误。 我做记者时,曾经采访过残疾人运动会,那时候我们从“残废人”改口称“残疾人”还没完全习惯,所以采访时我特别小心,生怕一不留神伤到谁。可即便是小心翼翼的“残疾人”称呼还是遇到了抵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台湾选手和蔼地告诉我:“在台湾我们叫残障,比较好。”是啊,当只剩下一截的躯体还在泳池里扬波,看不见跑道的盲人仍在奋力冲刺,我们凭什么以我们四肢健全的骄傲去居高临下地冠之以“疾”呢?海燕,可以说,那是我第一次特别强烈地意识到,一字之差于尊严的意义。原来,人对尊严的意识竟是这么地无微不至,敏感得像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它一旦麻木失灵,整个人不就真的废了? 而我对那些社会进步之所以不平衡,就是因为常常在这些细微处,我们能体会到的尊严未必赶得上体面而亡的死囚。举个例子说,我不知道现在学校里是不是还在沿袭考试成绩的张榜制度,但在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整整15年30个学期里,我们的考试成绩都是实名公布的。海燕,不知你想到过没有,对于那些排在榜尾、或者名字后面还拖着个被红墨水特别标出的不及格成绩的同学,只要他/她还尊严尚存,这些布告岂不就跟公审宣判一样?换了我,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捱过这周而复始的刺激。好在,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张榜制度的激励,我一直成绩不错,即便偶尔会为小小的发挥失常而难为情,但大体算对得起观众。但是,有那么一次,平生第一次,记得是在上高中文科班时,我的数学考试不及格需要补考,我无法接受失败就硬是躲着没去,驼鸟一样地幻想着这个没脸见人的成绩能和旧学期一样不知不觉地流走。结果可想而知,新学期返校第一天,就看到布告栏里赫然张贴着一张处罚通知,而我的名字也结结实实地列在了上面,那羞辱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了,因为,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一头撞死在上面的心都有。后来到了海外才知道,至少在大学里,任何学生的成绩如果不经过本人授权,是任何人无权得知的。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我上过的班上,似乎人人都心安理得,特别是那些本土学生,看他们考试过后不上心的样子,好像个个都得了A。海燕,因为在海外的课堂里,我终于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当“差生”的滋味,你不知道,我是如何从心底里感激那个不张榜的制度! 叫我这么一讲,海燕,你大概也会联想起一些类似的经历,也许你会有不同的体会,但我想,你至少会同意,即便是对于如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重申一下尊严意识总是不为过的。至少,如果飞飞哪天也因无知而挑衅他人尊严的时候,你能意识到该是指引她认识人的尊严以及她自己的尊严的时候了,毕竟,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学会尊重别人的礼节性问题。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个以绝对优秀的学业表现折服英伦的中国小留学生的故事,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她敢在日不落帝国豪情宣称:“生而贫穷不是耻辱”,真的叫我舒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又说这是炒作,争论得沸沸扬扬,还是叫人真假莫辨。不管怎样,我是这么想,能把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传上一阵,至少算是件好事。你说呢? 人文格言 Dignity consists not in possessing honors, but in the consciousness that we deserve them. 尊严不取决于拥有多少光荣,而取决于我们意识到这些光荣是我们应得的。 ——Aristotle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我们配做父母吗? > 正文 | |
|
| 新 闻 查 询 | |
|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 |
|
| |||||||||||||||||||||||||||||||||||||||||||||||||||||||||||||||||||
企 业 服 务 | |||||
秋意浓浓美妙重重!(京) 心的冬季旅游(豫) 牛皮癣鱼鳞病重大突破 谁说糖尿病无法治愈! | |||||
| 分类信息刊登热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