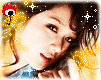| 窗棂里的爱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4/13 12:48 大中专文苑 | |
|
那年冬天,顺景被送进济安福利院。很冷的晚上,坐了五个多小时车的她被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领着,去楼上睡觉。灯光昏暗的楼道里,有陌生和潮湿的气味,水泥地板坚硬而冰冷。顺景牵着女孩的手,在黑暗里迈着每一步。厚重的碎花棉袄在惶恐寂寞的空气里摩擦出小心的声音。 “我叫恩夕,你呢?”女孩低低地问道。 “顺景。” “很好听的名字。不过,以后就用不着了。” “为什么?” “来这里的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新名字。为了告别过去。” “哦。”顺景低下头去,没有再说话。 女孩领她到一个房间,离楼梯口整整42步。房间的门上有漆皮剥落的痕迹,摸上去仓促而温情,有一点儿碎裂的疼痛。 “顺景,你过来,我们一张床。”女孩铺好了床,轻声喊着她的名字。 黑暗中她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问:“还有别人吗?屋子里。” “嗯。是恩桐和恩词,已经睡了。” 顺景脱去棉衣,在女孩身边躺下。屋子里有点儿冷,刚铺开的被褥还没暖起来。顺景躺在那里,轻轻吸着冰凉的空气。她苍白的手指蜷缩在一起,像一群寒冷无依的孩子。 顺景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看顺景的手,便摇头走开了。春天的时候,顺景上山采野花,从山坡上滚下来,折了腿,到入秋才能下地走路。相依为命的外婆常常哭肿了眼睛,后来犯了老病,不停地咳嗽。外婆终于没能熬过冬天,那是下第一场雪的时候,外婆枯瘦的手一直摸着她的头发和眼睛,直到离开。 1993年12月,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顾恩铭。 我不知道顾院长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给我,也许,只是为了让我很好地铭记这份恩情。恩夕说,是为了忘记过去。我不需要忘却,因为记忆并没有带给我深刻的伤痛。从一个黑暗里进入到另一个黑暗,不该有任何纪念。 而我的纪念,只是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 与其说这里是孤儿的天堂还不如说是残病儿童的遣散地,因为很多人把自己的孩子悄悄送到这里,是因为他们不健全,先天或后天的。当然,大部分孩子的确是孤苦无依。如果他们够漂亮,够聪明,还够幸运的话,会很快离开这里。恩夕对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14岁之前被领养。我暗地里为她祷告,因为她现在已经14岁了,机会很渺茫。没有人愿意收养记忆很多的孩子。记忆在某些时候,不是色彩斑斓的梦,是沉甸甸的包袱,恩夕领我走遍了福利院每个角落,她说我必须熟悉自己的家。到四楼的时候,我们碰到顾院长,他叫恩夕跟他去会客室一下,于是我站在那里等着。好像是傍晚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一楼上课,所以楼道里很安静,没有一点儿声音。我沿着窗户慢慢走过去,摸到了窗棂上落着的土,细细绵绵的,很舒服。是岁月很久很久感情的沉淀。 我走着,想起小的时候上山去摘红彤彤的山花。漫山遍野的红,从天空里一直烧到山脚下,再没有别的颜色。突然一只手拉住了我,用很大的劲儿一把把我拉过去。“没看见那只暖壶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对着我喊,他嘴里的热气冒出来,扑到我脸上。 “没有。我只听到一只暖壶在对我说话。” 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了,笑得很大声。“你是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顾恩铭”。 “恩铭?我是恩言。你可以叫我恩言哥。” “为什么要叫你哥?” “嗯………因为这里比我小的孩子都这样叫。” 我低下头去没有说话,表示默认了。我喜欢这样的叫法,很有亲情的味道,像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一样。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等恩夕姐。” “她今天有点儿事。你还是别等了,自己先回去吧。” 我听见他转身离去,硬皮鞋的声音渐渐走远。那个声音忽然又走回来,站在我面前,“怎么还不走呢?马上要开饭了。” “我……” 空气很寂静,窗外起了一点风,有沙沙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冬天是没有落叶的。 “我看不到路。” 寂静。这是我预料到的。 “哦,没事。我领着你走好了。”他说着伸过手来拉着我,他的手比恩夕的还要大,很暖和,手掌里有细细的纹路。我在想,他为什么没像很多人那样,知道我看不见,然后大声惊叫。 他牵着我的手,慢慢走着。在我的黑暗世界里,第一次感觉到有别人走了进来,我能觉察到他细微的动作和呼吸。因为走得慢,从四楼到一楼,走了好久。 晚上恩夕到很晚才回来,她一进屋子就抱住我,说要离开这里了。我很为她高兴,她的愿望终于在14岁之前实现了。听说那家人很有钱,只想要个女儿。他们看了所有女孩子的档案,最后选了恩夕。 “再过3天,我就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你不喜欢这里吗?恩夕姐。” “我在这里住了5年,已经足够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包括记忆吗?” “我早就丢掉了过去,所以什么都不在 乎。” 她伸出手来抱住我,有些颤抖。我伏过去紧紧搂住她的脖子,两个人拥抱在一起。那一晚很冷,我们睡在一个被窝里。 3天过去了,被那家有钱人接走的不是恩夕,而是恩词。所有的人都懵了,恩夕哭着跑回去。我看不到这里的任何事物,包括嫉恨和争夺。很久以后恩词写信回来,说要跟着家人出国去了。她和恩夕说对不起,因为她比恩夕还要大,没有时间再等另一个机会了。况且,她的学习成绩要比恩夕好很多,人家选择她也是应该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地方也在很残酷地竞争。 恩夕已经上中学了,她每天都去很远的学校上学。福利院的条件不是很好,没有自己的车,也没有足够的自行车,所以大一点儿的男孩子通常都骑车带一个女孩子去学校。恩夕很幸运,她由恩言哥带着。而我,却在一楼的课室里学习我的盲文。在那个凸凹不平的世界里努力找寻和外界联络的方式。 中学放假以后,已经快到除夕了。院长整天在外面跑捐助要给我们做新衣,阿姨们也常常借故回家。大一点儿的孩子没有人管,就跑到福利院后面的山坡上打雪仗。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雪了,可我不能和其他人一起,去看看雪的颜色。在我的记忆里,只剩漫山遍野的红,再没有其他色彩。时间久了,我就会以为,黑暗以外的世界,是红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四楼,去摸那些窗棂里的尘土。我知道,那是春天刮风的时候积下来的,整整一季的风最后都停留在这里,不再远走。摸着它们的时候,我会轻易地想起以前。 “恩铭,你不快乐吗?” 我回过头去,感觉到一点儿温暖。“是恩言哥吗?” “你常常一个人站在这里,为什么?” “我喜欢这里的土。是不是很好笑?”我微微笑着,继续捏着那一小撮窗棂土。 “我刚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寂寞和害怕,于是也常常一个人跑到这里。打开窗户把身子侧出去。” “那样,是不是就不会害怕了?” “呵呵,是更害怕了。于是就觉得窗户里的生活很好。” “恩铭,想看雪吗?” 我的手指一松,那些细细的土就成群结队地溜了下去。它们想回到窗缝里。 “走,我带你去后山坡。”他的手伸过来,紧紧抓着我。我跟着他,在四楼的楼道里跑起来,听见我的棉鞋和他硬皮鞋的声音“咯咯”跟在身后。我看见眼前一条红红的道路,还有红红的身影在我身边飞奔。 我们下了楼,一直在跑。直到脚底下松软的雪开始漫到小腿上。恩言哥气喘吁吁地说:“恩铭,我们到了。”我的手还放在他那里,微微出着汗。 “恩铭,把那只手给我。” 我伸出手去,接到了一捧雪,满满的一手掌,冰凉得近乎幸福。 “看到了吗?雪。” “嗯,是最幸福的颜色。” “那是什么样的颜色?” “我所记得的惟一的色彩。不过……我不告诉你。”我笑起来,把那捧雪撒向他。看到面前飘落了一瓣瓣血红的花瓣。那只他握着的手还在冒着热气,而身体另一侧那只孤单的手,却冷得没了感觉。 我们在雪地里追逐起来,把黑暗和记忆抛得远远的。恩言哥问我,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我摇着头说不知道。他笑起来,说天已经黑透了。恩言哥你不害怕吗?不。我想和你一起待在黑暗里,那你就不会寂寞了。恩言哥,长大了就不会害怕了吗?是。长大了就不会怕了。那个时候,我是那样地渴望成长,仿佛成长不是一种过程,而是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那里,不会有黑暗、恐惧和孤单。 那天夜里,我的肚子疼起来,发现床单上湿了一大片。我害怕得大哭,恩夕醒来,她和我说,恩铭你长大了,这张染红的床单是为了告别过去。为了告别过去。我想起成长的承诺。那天夜里,我没有再睡着,成长的恐惧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赶跑的。 院长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除夕那天,我们每个孩子都穿上了新衣,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雪地里放鞭炮,用这种骤然间的燃烧和破碎来庆祝自己的成长。劈劈啪啪的声音里,我走过了自己的12岁,黑暗和温暖并存的12岁。 1996年8月。 已经习惯了黑暗。所幸,还可以用耳朵来听这个世界。 人们都说瞎子的听觉和嗅觉很好。因为当你失去了一种生存的方式,必须把剩余的能力发挥到最大。我学习盲文,练习风琴,在恩夕和恩言恩平哥的帮助下已经学到了初中二年级的课程。他们惊异于我的聪明和适应能力。我不是天生盲的。12岁那年从山坡上滚下来后,我失明了。医生说我的眼睛没有太大损伤,失明的原因很可能是过度的恐惧。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样。3年前恩言哥牵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了。我怀疑医生在骗我,或者,是骗我可怜的外婆。3年里我没有看过医生,我竟然像个动物一样坚强。也许,是因为身边有太多脆弱的生命在不断激励着我。 恩言哥在等着高考通知。于是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陪我。每天下午他给我讲完课后,我就会弹风琴给他听。在一楼尽头那间满是玻璃窗的音乐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窗户开着,盛夏的花香和微风悄悄溜进来,在我们面前牵扯。恩言哥说:“恩铭,你的手指真好看,像是天生用来弹琴的一样。”我的手指停在那里,突然不会动了。脚踩在那两块很年久的木板上,微微颤抖。一阵风走进来,我前额的头发就落下来,遮在眼睛上。 “恩言哥,那是天生用来为你弹风琴的。”我说了这样的话,在寂静黑暗的时候。 没有动静。空气里只有很淡的丁香味,恩言哥说过那是紫色的。紫色在我的意识里只是个概念,我无法感觉。我只有红色,我失明之前看到的最后一种颜色。 他走过来,站在我的身后,很近。我感觉到他的体温。那个瞬间仿佛永恒一样,永远定格在那只破旧的木风琴旁边。有风吹着,很慢很慢。 恩言哥考上了南方的军医大学。他走的那天下着小雨,院长带着恩平哥恩夕和恩年去车站送他。他说:“恩铭,你待在家里,我不想看见你离别的样子。”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一个人走到四楼,听离别的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清楚而疼痛。手顺着窗棂摸过去,找寻岁月年久的感情沉淀。它们还躺在那里,有些潮湿,没有曾经的细腻和缠绵。我突然流起泪来,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恩夕回来已经很晚了。她上床不久,我听见低低的啜泣声。我爬过去,用手指轻轻摸着她的脸颊,冰凉的泪水顺着我的手指滑下来。天生为恩言哥弹风琴的手指。恩夕渐渐哭得大声,身子跟着抽搐起来。我伸手抱着她,像3年前那个冬天的晚上一样。从对方身上获取一点温暖和安慰。 我第一次知道,恩夕很喜欢恩言哥。 第二年新年的时候,有家医院来为我们做免费诊察。我被恩夕带着去见医生,女医生说她可以治好我的眼睛,叫我相信她。我已经习惯了在黑暗的世界里独自生存,听到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恩夕大声地问我,恩铭你不高兴吗?你就要重见光明了。 恩夕拉我出来,你不信任医生吗?我说没有。那你……,恩铭你知道吗,大家都想让你好起来,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和我们一样去学校读书了,像恩言哥那样考上大学离开这里。恩言哥。我的心一紧。我知道自己在乎什么。 1998年2月。我成功地做了手术。3月份,去学校插班读初中三年级。 恩言哥一直没有回来,每个假期他都会寄钱给我们。恩夕说他想让我们过得好一些。恩夕一直不断地给他写信。她的梦想是考到和他一样的学校,并为此付出了超乎一般的努力。每个深夜她都会点着蜡烛在那里看书。我看着伏在小书桌上的单薄身影,心里就会有点儿不可名状的疼痛。我知道,瘦小羸弱的她有一颗很爱很爱恩言哥的心。 6月,气温高得让人害怕,院里的树叶花草都打着蔫儿,抬不起头来。我和恩夕每天下午几乎没有午休就顶着大太阳骑车去学校。有一天在路上她忽然流起鼻血来,大滴大滴鲜红的血把白衬衫染湿了一大片。我擦着血和她说,恩夕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恩铭,你知道吗,我今年必须考上,没有退路。我要去找恩言哥,她苍白的脸上绽出一个脆弱的笑。 我竟然在妒忌恩夕的长大,恩夕的高考,恩夕的毅力,和她那颗爱恩言哥的心。没有理由。我承认自己也在同样深爱着和自己一起长大的恩言哥。恩夕脸色越来越苍白,开始出现呕吐和咳嗽。我担心起来,害怕她会出事。在我的生命中,已经不能再承受过多的离别。 一天晚上,恩夕晕倒了。她端着的水盆掉落下来,很清澈的水在走廊静静地流淌,红色的塑料脸盆在旁边打着转。我们听到声音跑出去,看见瘦弱的恩夕躺在那里,长长的头发被水打湿,很小的水珠顺着脸颊流下来。我想起了恩言哥走的那夜,她冰凉的泪顺着我的手指滑下来。那时,我们都在为一个要远离我们的人而各自伤心。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有上帝的存在,或者,他总是遗忘我们这些缺少关爱的孩子。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福利院里,总是有太多的孤苦和分别。恩夕醒过来的时候,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我没事的,就是有点儿累了。我别过脸去,眼泪肆无忌惮地爬满脸庞。 没想到,我第一次知道“白血病”这个遥远的词竟是以这样的方式。 恩夕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我开始怀疑是我的嫉妒害了她。我曾卑劣地想过,要是恩夕考不上大学,那她就不能去南方找恩言哥了。我为我的邪恶心痛不已,是我害了恩夕。为什么要让我身边的人都一个个离我远去,父母,外婆,还有恩夕。 院长决定告诉她。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支配自己仅存的一点儿时光,恩夕已经长大了。只是在不久前,我还在为恩夕的长大而耿耿于怀。恩夕的平静让我吃惊,原来瘦弱的外表下面有着坚强执著的心。那是一颗爱恩言哥的心。 恩夕没有参加高考,她每天都在一楼的教室里为小一些的孩子上课,没有伤心,没有绝望。她说,剩下的日子要和弟弟妹妹们在一起。她和我说话的时候,窗外的阳光打进来,照在她细致苍白的脸上,像一朵想要在冬日里开放的小花,凄清而干净。 1998年冬天。 很久没有下雪了,空气很干燥。一个没有雪的北方的城市,冷得厉害。恩夕和我说,要是恩言哥回来了,一定会冻坏的,他大概已经忘了这里的冬天有多冷了。我笑着说不会的,恩言哥不会忘记的。可出去的时候我在想,恩言哥还记得这里和我吗? 终于下了一场大雪,福利院的整幢楼都被白白厚厚的雪盖着,孩子们都跑到外面打雪仗堆雪人。下午雪停了,我去医院给恩夕拿药。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小小的雪花又开始飘起来。我一个人走在雪地里,听自己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走着走着,我发现响声不止是我一个人踩出来的。回过头去,看见不远处有个人跟着我。那个人长得高高大大的,走得很快。我有点儿害怕,就跑起来,听见后面的咯吱声也跟上来。他终于冲我喊,小姑娘你停下来,我不是坏人。我站在那里,不会动了,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他走到我背后,呼呼喘着气,小姑娘,我……。你是恩言哥吗?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没有回头。恩铭?你是恩铭?他一把拉我过去,像多年前那个傍晚一样,我冻得通红的手安静地躺在他的大手里。 我上楼去告诉恩夕。她跑到镜子前,忽然哭了起来。怎么办,恩铭……我这么丑,她拍打着苍白的脸,泪流不止。我走过去拉着她的手,恩言哥不会觉得你丑的,真的,因为他爱你。我不知道除了这样说,还可以怎样。 快到除夕了,福利院又热闹起来。孩子们跑来跑去,大声尖叫。我整天躲在四楼的小图书室里不见天日。恩夕常常去找恩言哥,他们在一起说很多的话。恩言哥还不知道恩夕的病,她只说是受了凉,爱咳嗽。看见她幸福地微笑着,我觉得她可以活得更久一些。爱情在有的时候,会产生奇迹。 有一天我帮恩夕整理床铺,看见枕头下压着一条手绢,粉色的格子手绢上有一簇簇暗红的血,像是盛开在黑夜里的花朵。手绢掉在地上,我不想哭,我不是个脆弱的人。而此刻,泪水竟是那样的倔强。我跑上四楼,看窗外的雪铺满了整个世界,天空和大地白得令人心痛。我摸着已不平整的窗棂,想第一次见恩夕的时候,她牵着我的手,低低地说,我叫恩夕,你呢? “恩铭,你怎么了?” 我回过头去,细细的窗棂土从指间滑落。 “为什么总躲着我,恩铭。” 我站在那儿,不说话。 他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两只有力的臂膊紧紧将我拥着。我又流下泪来。 “恩言哥,恩夕姐她……就快死了”我竟然说了出来,“已经……开始咳血了。”我泣不成声。 “我知道,我知道。”恩言哥哽咽着。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恩夕姐她喜欢你。”我挣脱开他,大声喊着。他抱住我,“恩铭,那不是我们的错。” 不是我们的错,可恩夕她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恩夕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已经晕倒好几次。恩言哥每天都陪着她,一起听范晓萱的《踏雪寻梅》。恩言哥说,等你好起来,我们一起去山上看雪。 除夕那天,恩夕穿上去年做的新衣,很仔细地梳了头发,涂上口红。她问我,恩言哥会喜欢吗?我说,会的,一定会的。 晚上吃过饭,大家都去外面放鞭炮。小孩子拿着焰火条在追逐打闹,大一些的孩子放很响的雷炮。恩夕说她很冷,恩言哥就抱住她。两个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天空里的五彩焰火。很美丽的火光,飞上去,又掉下来。我站在四楼的窗户口,想起以前的除夕夜。 鞭炮声越来越大,天空被热闹的火光照得很亮。远处的钟声响起来,1999年到了。我低下头去,看见恩夕躺在恩言哥怀里,一动不动。 2001年7月,我参加了高考。 9月,我提着行李箱走在拥挤的南方某城火车站。背后有人走过来。 “没有看见那只暖壶吗?” “没有。我只听见一只暖壶在和我说话。” 他一把把我拉过去,说:“我这只暖壶可是烫人的。”我们笑起来,紧紧拥在一起。 贾小利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大中专文苑》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