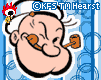| 8/初涉政界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6/09 09:3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到1972年,约翰·克里已经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但却始终是个没有根基,确切地说,没有家乡的漂泊者。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两块大陆辗转度过的。在他不到七岁的时候,他家就搬离了马萨诸塞,直到从越南战场返回,克里才又回到马萨诸塞。对于一个拥有政治雄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政治根基真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相信他在反战运动中的表现足可以让他在众议院赢得一席之地。他准备离开游行街道进入反战伙伴们所蔑视的“体制”内工作。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参加波士顿西部郊县弗雷明翰的公开州众议院席位选举,“交上几年会费”。 但是克里的政治雄心是全国性的,对政治充满了天真的遐想。他奔波于各个众议院选区宣传自己。在1972年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反战领袖就在马萨诸塞三个选区中宣传了自己。这种各区拉选票也为自己招来了投机分子的恶称,克里也承认那段时间是自己在故乡的一个“负担”。
1972年初克里仍然住在沃尔瑟姆,两年前他就在这里挑战过老谋深算的民主党鹰派人物菲利普·菲尔宾,沃尔瑟姆也位于第三选区。然而克里当时的计划被反战耶稣会牧师罗伯特·F.德里南的出现打乱了,他最终赢得了议院席位。就在德里南于当年春季开始自己的竞选活动时,克里接受了《洛厄尔太阳报》的采访。该报是洛厄尔市所在的第五选区的主要报纸,他对两个记者说他打算挑战F.布拉德福·莫尔斯——一个支持尼克松越战政策的共和党,一直是国会议员。然而,那年克里折戟沉沙,在1970年的选举中,他早早便失败退出了。 但是在下一个众议员改选期,克里重新振作起来。他离开沃尔瑟姆搬到了25英里外的伍斯特。1972年2月7日,朱莉娅为位于欢乐大街690号的一处价值为29 500美元的房子交了6000元定金,这样房产就在她自己的名下。她的丈夫此时正在挑战哈罗德·D.多诺霍——一个坚定的民主党议员,他也对竞选踌躇满志,甚至从《伍斯特电讯公报》(Worcester Telegram & Gazette)雇了一个记者为他的竞选开始宣传。 克里夫妇没有搬进新居。相反,克里在获知第五区的议员莫尔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总次长(undersecretary general)后又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五选区。3月末,这对夫妇收拾行装来到位于麦瑞马克山谷(Merrimack Valley)的洛厄尔市租了一处公寓。莫尔斯即将赴华盛顿任职,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人曾把持的一个席位要重新公开选举产生。 克里寻求议院席位的政治雄心也有一种肯尼迪情结。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战斗英雄肯尼迪为了在政治领域一展宏图,也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马萨诸塞第八选区做了竞选开始演说。“这里我们有一位候选人,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肯尼迪的一个助理帕特西·墨尔肯回忆了他们在位于波士顿灯塔山的老贝尔维尤饭店(Old Bellevue Hotel)竞选战略会议上的谈话。墨尔肯提到了肯尼迪的外祖父——波士顿前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人们都亲昵地叫他亲爱的菲茨),建议道:“把这里当做住址怎么样?” “于是我们在饭店租了一间两室的套房,那就是候选人手册上所写的地址。”菲茨说。 26年以后,克里的政治追求过程甚至更加困窘。在注意到克里是“政治移民”后,《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在标题为《多人角逐议院席位》的社论文章中尖刻地讽刺道:“如果克里仍然居无定所,他将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总助理,还需要一个全职地产经纪人。”克里的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10年,但是除此以外,克里在第五选区没有任何关系网——结果证明,毫无根基的外来政客根本无法抵御即将来临的猛烈攻击。 对于有关他是个外来客的问题,克里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在第五选区学会走路的。”没错,当克里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的父母和孩子在洛厄尔市西边的格罗顿镇度过了一年的田园生活。他的父亲理查德在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任教,那是一个寄宿学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著名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从外交官职位上卸任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了这个小镇,此时约翰刚刚进入耶鲁。格罗顿与洛厄尔近在咫尺,只有15英里的路程;但在这里度过幼年时光的克里却无法被洛厄尔接纳。 洛厄尔的显赫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在历史书中还能窥见其往日荣光。数年以后,高科技公司和乡村国家公园又使这个城市重新繁荣起来。1972年,洛厄尔像过去一样又陷入了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旋涡。工业不景气极大地打击了洛厄尔的经济,而70年代初就开始的经济低迷导致该城失业率达到12%。几座纺织工厂还在苟延残喘,还可窥见当年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盛况。正是纺织业振兴了洛厄尔,它是美国第一个计划经济城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奇迹。 从附近城镇和乡村招募的北方女工是最早的劳动力,现在她们早已与众多外来移民融为一体了。爱尔兰人最先移民到此地,帮助开掘了动力水路;随后是法裔加拿大人、希腊人、波兰人、立陶宛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等等。 劳伦斯是位于第五选区的另一个衰败的纺织业城市,也是一个颇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市的工人也是各地移民。1912年,该城因为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在美国劳工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2万多纺织工人走出工厂,抗议减薪。参加了“面包与玫瑰”的罢工者竟然讲着多达24种语言,甚至到了1972年,其中的很多种语言仍然可以听到。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当时失业率达到了9%。在这两个人口复杂的城市,政治通常受到残酷的种族生存第一论影响。在这两个政治上民主党控制、社会风气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中,谋取政治职位颇为困难。此外,洛厄尔还因为它独特的血腥政治文化而闻名。 1972年初,贵族约翰·福布斯·克里来到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他是一个民主党员、天主教徒,但对于城中的居民以及保守的郊区居民来说,他是个外来的政客,是个与洛厄尔格格不入的人。他的高贵血统在这里毫无价值。 “我理解那些对我不满的人,”克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国会竞选时说,“我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这个选区,大声宣布‘我来了!’这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接受的粗鲁举动……如果我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政治,恐怕就不会那样做了。” 但是在第五区,另外一些地方却对像克里这样的候选人给予了足够关注,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洛厄尔和劳伦斯市约有一半民主党预选选民——周围的保守城镇中占了30%——剩下的五分之一的选民都居住在这一选区南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在那里,反战情绪很强烈,平民们大多是革命祖先的后代。在这样的中等住宅区,如康科德城和来克星顿,克里是个充满活力、让人激动、有摇滚歌星般轰动效应的新人。而城镇中的政客却被平民们看做糟糕的倒退者,甚至更糟。 莫尔斯的调职升迁激发了许多人的政治雄心——所有人都开始关注着两个纺织城市。除了克里之外,加入到这场众议院席位争夺战中的还有洛厄尔地区的七个民主党人,以及劳伦斯地区的两个民主党人。在共和党一边,保罗·W.克罗宁,前众议员以及莫尔斯在安多弗(Andover)的前助理,也要竞选这一席位,他还有三个同党竞争对手。此外,罗杰·P.德金——洛厄尔的保守民主党人,也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直接参加11月的终选,使得竞选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克里的竞选费用数目巨大,主要来自于选区外富有人士的赞助。此外,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军人作为克里狂热的支持者也在四处筹募资金,志愿发起预选前的民意测验。克里的志愿者们超出了传统竞选宣传的界限,甚至为民众提供免费教育以建立起民众对克里的好感。这些年轻志愿者给老年人散发传单,向他们介绍政府的各项服务和福利;给中年人准备了一份购物指南,详细比较了这一选区各大超市的价格;甚至还设立了一部“租赁者热线”以处理对房东的投诉。 电影人奥托·普雷明格、作家乔治·普林顿、著名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一个劳伦斯本地人),以及其他社会名流都是克里激进一派的支持者。普林顿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纽约人,他亲自来到劳伦斯城区内著名的黎巴嫩人饭店毕肖普(Bishop)为克里的竞选筹募资金。 9月19日的预选逐渐临近了,克里看起来似乎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他所花费的竞选资金高达279 746美元,第五区的竞选将是当年整个国家国会初选花费最多的选区。就在克里踌躇满志时,灾难临近了。就在预选前一天下午两点,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发现有人闯入了一座多层办公楼的地下室,该办公楼正是克里以及另一个民主党竞选人——劳伦斯的众议员安东尼·R.迪弗鲁西亚(DiFruscia)——的总部。 当后援警察赶来时,他们看到克里的弟弟卡梅伦和竞选助理托马斯·J.瓦莱里这两个22岁的小伙子正在大楼电话系统干线附近。警方以破门而入和企图盗窃为由逮捕了这两个人,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了。 第二天,《洛厄尔太阳报》登出了少见的双行大标题新闻:“克里弟弟因洛厄尔‘水门事件’被捕。”迪弗鲁西亚也被揭露出来曾在三个月前非法进入华盛顿民主党总部,这给马上来临的预选又增加了不少话题。 克里阵营宣称,这两个年轻人是被人故意陷害的,说他们几分钟前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该电话威胁要在最后投票的前一天剪断总共36部电话线,两个年轻人前去察看,恰好被警方发现。时至今日,每当克里谈到这件事时都激动异常,他坚信那是一个阻止他竞选优势的阴谋,尽管他不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他也觉得媒体对迪弗鲁西亚的报道简直荒谬异常。“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竞选中。”克里说。 克里认为,洛厄尔闯入事件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太阳报》的排字工人说,在凌晨1点的时候,那头条位置就预先留出来了,头版位置也留出来了。”克里说,“你们知道,这对报纸来说太不正常了。最重要的是,事发第二天早晨这份报纸就出现在街头了。” 《太阳报》是份晚报,它的最早付印期限是在被捕事发8~9小时以后,它有足够的时间编辑这条轰动新闻。劳伦斯的《老鹰论坛报》(EagleTribune)也是一份晚报,也在当天报道了被捕事件。它用稍小的篇幅报道了该事件,题目是《水门事件阴影?》 今天,克里的弟弟拒绝详细描述当时被捕和被指控的经过,该事件一年后才平息下来。“我们所做的事很冲动、鲁莽,给约翰带来了麻烦。”卡梅伦·克里说,他现在是波士顿明兹·勒文·科恩·费里斯·格拉弗斯基和波比奥(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就是我对该事件想说的话。” 瓦莱里曾经是在越南服役的海军陆战队战士,后来是波士顿的国会众议员,他对于此事更加直接和坦率。“我一脚踢开了地下室的门,”他回忆道,“随后,警察就包围了这个地方。”他当时最担心的不是选民们会对此事有什么议论,而是他的父亲会因此责骂他。“我的父亲是一位法官。我担心他会不认我。”瓦莱里回忆道。 迪弗鲁西亚与此事毫无关系,瓦莱里说,有人威胁要破坏电话线,我们担心克里会首当其冲,但是现在回想,他说:“我们也许对某些人的玩笑反应过度了。” 这次被捕对于预选并没有太大影响。第二天,克里赢得了22个城镇中的18个城镇。在10个候选人角逐的选举中,他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的得票率惊人地高,如卡莱尔(82%)、康科德城(78%)和来克星顿(72%),以3∶1的优势战胜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不过他在工人主导的城市中得票形势却不太乐观,在洛厄尔名列第四,劳伦斯名列第二。总之,克里赢得了20 771张选票,是总票数的28%。名列第二的是洛厄尔的众议员,赢得了15 130张选票,占总票数21%。迪弗鲁西亚以12 222张选票和16%的得票率位列第三。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克罗宁轻松取胜。不过两党相比,克里似乎更占优势。他在七星期后的大选终选中似乎会以绝对性的优势胜出。《波士顿环球报》在预选两星期后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克里的支持率为51%,克罗宁则是24%,德金仅为7%。 可是胜利不会这么简单。在克里与最终胜利之间插进来了克莱门特·C.科斯特洛——行为古怪、捍卫正统的《太阳报》主编。 克莱门特·C.科斯特洛是洛厄尔的异类。作为当地知名报人,他一直保持清廉,避开洛厄尔上层社会的严密社会关系网。他是一个崇尚法国文化的绅士,驼背的上身总是套着得体的丝绸衬衫,带着法式的卷袖。即使在《太阳报》每天接待形形色色人物的新闻室中,他也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他酷爱戴着贝雷帽,长发潇洒地从帽子下面垂到肩头。他当时53岁,住在穿过洛厄尔上层住宅区贝尔维迪尔的安多弗大街上,他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科斯特洛继承的豪宅中摆设着精致的上等家具和昂贵的古董,然而他对这所房子根本就不精心管理,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庄重住宅看起来像座鬼屋。不加修剪的草坪已经长了几英尺高,房顶的裂缝也放任不管。曾经有一个在楼上卧室过夜的客人半夜被反反复复的巨响惊醒,他起身打开门后发现成群的鸽子在大厅里飞进飞出。 每天,在报纸城市版编辑好付印后,科斯特洛就来到位于城区卡尼广场附近《太阳报》车间的狐尾休息室(Foxtail Lounge)。他呷着香槟,抽着法国Galoise香烟,从头到尾仔细圈阅报纸上的每一个字。 他的形象与哥哥形成巨大反差,约翰·H.科斯特洛是一个严厉的人,是洛厄尔上流社会的支柱人物。他们一起继承了家族于1878年创办的《洛厄尔太阳报》。约翰是出版者,负责报社商业运作。克莱米——他经常被人这样称呼——负责新闻业务,这家中型日报总是能抢到有轰动性的新闻。科斯特洛兄弟在新闻业务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们的《太阳报》早在调查记者流行之前就有一个全职调查记者,有自己的华盛顿特派通讯员,还在波士顿的州议院和剑桥郡的法院有众多记者。 不过该报的社论版完全体现了克莱门特·科斯特洛一个人的风格,这个极端保守分子犀利地攻击政府的弊端,不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对政府惟命是从的政客。他不受习惯的约束,在70年代末期,他甚至强烈建议美国吞并加拿大、入侵墨西哥以解决石油危机。 《太阳报》一直持有反克里的态度,但在预选期有所收敛。这段时间,科斯特洛组织他的大部分社论火力攻击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们,这个三人小组被怀疑卖官鬻爵,任用亲信,还虚报建设东剑桥新法院大楼的建筑预算。 科斯特洛在大选前大肆宣传一个年轻的、连任两届的洛厄尔市议员,叫做保罗·E.松加斯(Paul E.Tsongas),他当时正在委员会竞选中遥遥领先。松加斯在预选中的胜利就等于洛厄尔的胜利,这让科斯特洛有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大选中来。 就在预选前一天,《太阳报》写文章支持罗伯特·R.肯尼迪——洛厄尔的评议员委员会成员(与产生总统的马萨诸塞家族没有关系)。该头版社论的大字标题就是《洛厄尔“水门事件”》,对克里弟弟被捕一事大肆渲染。 科斯特洛本来写的社论是支持希伊的,但就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他改了名字,加入了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就在这篇社论发表前一天晚上,肯尼迪拜访了科斯特洛,向科斯特洛出示了一个虚假的对自己有利的民意测验结果,以此劝说他改变立场。肯尼迪在预选中仅名列第五。 最后大选的前期阶段很平淡,但克里努力平息人们对他这个外来人的愤怒,尤其是在洛厄尔,那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气息。克里请了一些大人物来这些纺织城镇参加他的筹款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 克里从来不是个对人过分表示亲密友好的人,但一天晚上,他来到位于洛厄尔贫穷的阿克里区的一个小酒吧迈克·莫洛埃(Mike Molloy),请里面所有的人喝饮料,还玩儿了台球。只有几个常来的客人拒绝了这免费的饮料,但其他人都对克里勇于在希伊曾经拥有的酒吧里露面表示了欣赏,希伊是他预选时击败的劲敌。 由于克里的反战立场,他既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又遭受一部分人的憎恶。不过他的大多数竞选广告都力图展现他和普通市民聊天以及讨论经济问题等亲民的一面,试图把这个候选人人性化。“他不是一个政客,他倾听民众的心声。”一份竞选宣传册上这样写道。克里的政纲主要是要求政府解决一系列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失业工人实行处方药折扣。他还提出清理麦瑞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污染问题,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赞同对劳伦斯和洛厄尔实行出租控制。 在这样一个反对流产根深蒂固的地区,克里说他个人也反对流产,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应该干涉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被要求明确表态后,克里在竞选后期说他宁愿把流产这个问题留给国家去决定。几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它划时代的Roe v.Wade判决中宣布废除有关流产违法的法令。 朱莉娅尽管天生羞涩,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却尽职尽责地扮演她的角色。她会随丈夫登上三层的公寓房屋倾听租户的抱怨;面对潜在的选民,或是在劳伦斯和麦修恩(Methuen)一些住宅区的重大场合上,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选民说话。她的童年在罗马度过,那时他的爸爸在意大利任外交官和新闻出版人。她独特的上层贵族口音在居民中间赢得了“女教授”的称号。 从一开始,克里的竞选似乎就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文化背景。在狭隘、孤立的洛厄尔,像克里这样的移民一成不变地被冠以“闯入者”的称号。即使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当地人也仍然不能接受他们。更何况,克里从许多外面的议员那里获取了支持,如俄克拉荷马、密歇根以及纽约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克罗宁的广告宣传就嘲笑了克里的大肆投资和外界赞助人。“好莱坞的奥托·普雷明格和洛厄尔的路易斯·拜伦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一份大报纸上的广告说,“那就是今年他们都参与了大选。奥托·普雷明格为约翰·福布斯·克里捐助了1000美元。路易斯·拜伦给保尔·克罗宁赞助了15美元。” 德金更加富有侵略性。在没有得到允许重印克里1971年的著作《新战士》的封面后,他在报纸上用通栏广告打出“审查”两个大字。该书的封面是一个越战老兵,旁边的美国国旗不是高高飘扬,而是大头朝下垂了下来——悲观沮丧的象征。 科斯特洛抓住这个话题大肆渲染开来,在一系列社论中全面反对克里。除了主编社论攻击以外,科斯特洛还在新闻版面配以有关克里跨区竞选、从区外筹集资金以及反战活动等新闻。 随着1972年大选接近尾声,科斯特洛更加紧了对克里的攻击。现在看来,这些社论已经是价值很高的古董了,它们不仅仅是主编对地区偏见的反映,还表现出了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矛盾。 10月18日,选票最后揭晓前三个星期,科斯特洛第一次全面对克里的著作《新战士》开火了,旁边刊登着封面照片,他是这样说的: “三四个留着胡子的嬉皮青年扛着美国国旗,这让人不禁对比美联社乔·罗森塔尔那张永恒的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在占领日本硫磺岛后使美国国旗高高飘起。 而两张照片的巨大差异就是,在约翰·克里这本书封面所采用的照片中,美国国旗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被大头朝下地提着。这种态度就是年轻人对越南以及一切可能反对的国家事情的态度……这些人践踏国旗,焚烧国旗,倒拖着国旗,用国旗擦鼻子,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展示他们对国旗所代表的事物的蔑视。” 上面这番攻击只是科斯特洛的热身。在克罗宁于10月29日获得总统支持后——也就是大选的前10天——科斯特洛又在他的社论版面发起了持续四天的猛烈攻击。第一波攻击的题目是《新战士克里》,出现在30日的报纸上。 “他放弃了在越南赢得的好名声,转而捍卫激进的和平煽动者。事实上,他不仅捍卫他们,还领导他们……克里用他对美国在越南的角色不成熟的判断赢得了激进左翼反战英雄的全国荣誉,可事实上,这不会带来人们对克里先生的丝毫信任和尊敬。” 万圣节的报道则是《克里的旅行》: “很久以来,克里先生就渴望成为众议员,尽管他把自己定位为作家和演讲家,他一直都没有在商业和实业领域拥有一份工作。他的眼睛一直就盯着国会的座席。对他来说,做哪个选区的议员并不重要;哪个选区能使他最有可能成为议员,他就来到哪里……可以是第三选区、第四选区、第五选区——你随便挑吧…… 克里先生对第五选区所能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众议员席位——格外关心,远远超出他对能给予第五选区什么的关心。他需要一个全国的声望和政治权力,这样就可以推行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宣扬的激进观点,而第五选区的发展和选民的利益则被放在了第二位。” 11月1日的报道是《克里的钱》。 “资助克里竞选第五区国会席位的最多金钱来自……纽约。数目第二多的钱来自……波士顿……很显然克里先生的意图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淹死克罗宁,从而夺得席位。 克里先生的忠诚和责任是不是要在服务第五选区民众前先要效忠于纽约派克大街、第五大街、斯卡斯代尔、韦斯切斯特街区的富人呢?这一席位是不是要被纽约的百万富翁们物有所值地反复利用呢?……” 科斯特洛在11月2日,大选前五天发出了最后一次攻击——《克里的华盛顿》。 “有人能想像一下尼克松政府会怎样接待克里吗?我敢说,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个部门都会冷冷地拒绝他。
事实上,克里今天已经是尼克松政府极端厌恶的眼中钉,因为克里先生总是对政府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如果约翰·克里的名字是华盛顿总统脚下的烂泥,我们可不希望看到这团烂泥糊在第五选区选民的脸上。” 这番尖刻的、体无完肤的批评被比做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出版人威廉·洛布鼎盛时期的极端保守日报《联合领导人》(Union Leader)的一贯尖刻风格。“也许只比那个(Union Leader)差一点。”肯德尔·M.华莱士说,他在1972年是《太阳报》城市版的编辑,现在是该报出版人。“如果没有那种激烈的批评,我想克里肯定会当选议员。” 克里后来写给捐助者的信中也这样说:“整整两个痛苦的星期里,他们叫我非美国人、新左派反战分子、非爱国者,用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非’、‘反’的贬义字眼儿来称呼我。很难相信一份报纸竟会有如此力量,可他们确实如此。” 这场口诛笔伐的闪电战给克里带来致命的打击。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克里深受“《太阳报》和窃窃私语的伤害”,卡梅伦回忆道。“约翰·克里是那种剪纸人物,”卡梅伦说,“在这样激烈的唇枪舌剑攻击下,第五选区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投票给他。” 朱莉娅被激怒了。“《洛厄尔太阳报》……叫约翰“左”倾人士,”她回忆道,“这简直是造谣。我真不敢相信会有人那么卑劣地中伤克里。” 在大选前四天,克里的竞选再次遭受打击:罗杰·德金,这个独立的候选人和前保守民主党人突然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克罗宁并谴责克里“危险的激进主义”。德金的突然退出真是优雅的一击。就在大选前两星期,《波士顿环球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德金的得票率为13%,名列第三位。克里以27%的得票率领先于克罗宁,而大选前四天他的得票率已经降到了10%。 尽管对于德金的退出没有任何明显证据,但克里坚信尼克松的政治顾问是德金在最后大选来临之际突然退出的幕后主使人。“德金绝不是自动退出的。”克里最近说道,他一直认为他当时陷进了尼克松肮脏的政治圈套。克里说当地的支持者告诉他“总统办公室来的人到了洛厄尔”。 克里认为查尔斯·W.科尔森参与了他所说的阴谋。科尔森在马萨诸塞的温斯罗普长大,是尼克松的红人,他后来也是水门事件的共犯之一并被监禁。科尔森在1993年以及最近接受了《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他承认曾经试图抹黑克里的反战成就,但是断然否认了用阴谋干扰国会选举的这一“无稽之谈”。 德金后来搬到波士顿经商,他也断然否认了自己是共和党人利用的工具。最近接受采访时,他说当他发现他的参选将确保克里的胜利后,他“采取了自杀式行动”。 克里确实是白宫希望击败的目标,至少对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来说是这样。他亲自来到洛厄尔为克罗宁打气助威。但考克斯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少许别扭,因为他是克里的妻子朱莉娅的远亲。考克斯的妹妹梅姿(Mazie)嫁给了朱莉娅的一个表兄。考克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来在洛厄尔的地区检察院实习,他显然要帮助尼克松竞选连任和共和党人克罗宁取得胜利。考克斯说他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暗中破坏克里选举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就是谣言,也不记得尼克松曾经谈论过克里。但当克罗宁胜出时,考克斯相信这对尼克松的对越政策相当有利。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即使在马萨诸塞的洛厄尔,在这个工业萧条的地区,‘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支持总统的。”考克斯说。如果克里无法利用反战纲领取胜,考克斯认为这意味着广大民众还是支持尼克松总统的战争政策的。克里没有在反战情绪高涨的时候赢得议院席位,考克斯说道,等到克里最终赢得选举时,战争也早就结束了。 在竞选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卡梅伦·克里回忆道,他在劳伦斯游说拉选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选举“溜走了”。“很多人对我们有敌意。”他说。毕竟,越战和流产是能够引起强烈支持和极端反对的两极分化议题。 最后,大选结果出来了,结果并不激烈。在207 623张选票中,克罗宁以多出18 123张选票击败了克里,几乎领先了9个百分点。这位共和党人——他死于1997年——在那年的大选中赢得了洛厄尔、劳伦斯以及22个城镇中的19个。克里只赢得了来克星顿、威尔明顿和比尔里卡。 当天晚上,在安多弗饭店挤满了支持者的竞选晚会上,克里回应了科斯特洛以及其他质疑他爱国热忱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会在华盛顿,同越战老兵待在一起。”他说。大卫·索恩——克里在耶鲁的老友以及他1972年竞选管理人回忆当时说:“那是很惨痛的失败,就像美梦轰然破灭一样。我们输了,那本不应该发生。” 30年后,克里能更清楚地看到当年的自己,他承认他在当时作为一个候选人的缺陷。“我没有根基和关系网,没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没有高中母校,没有那些说和我一起踢过球的人。”他有了后见之明。“我所缺少的就是关系。我冒失地闯进来……那是一场基于一个理念的冒险,这个理念就是结束战争。” 克里现在也承认,他当时没能平息《太阳报》对他的中伤也是竞选失败的致命之处。“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克里说,“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这是个深刻的教训。”他知道以后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人民大学出版社精品图书集萃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