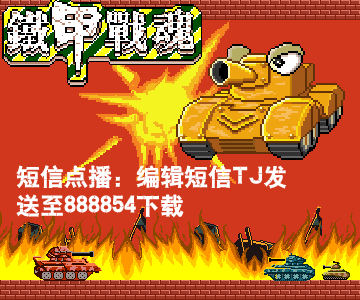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4>
德班楼原是矿主的居所,曾是劳伦斯每周替他父亲取工资的地方,而今天这座仍不失雄伟的建筑改做了博物馆,一进门,我就看见展示屏上大大的字“那是我心灵的故乡”(That’s the country of my heart)
劳伦斯在沃克街住得最久,感情也最深。这是典型的英国民居,一条街上坐落一排连在一起的两层红砖房,从正面看,每家一个大凸窗,门和窗都是白色的,衬着红墙,格外好看。
垫起脚尖,向前望去,眼前是青绿的田园,散布着低矮的灌木和三角的屋顶,一派和谐、宁静与恬适的田园风光。一恍十二年过去了,
他在这儿由不懂事的孩童长成了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六岁到十八岁,这片窗外的田园景致融入了他的灵魂与生命,成了他一生创作的泉源。
我伫立屋前,从窗口可以看见精雕的蕾丝窗纱,窗台上插着一束鲜花,不知这房子已几易其主了。一个世纪前,就是从这个窗口,时常映出劳伦斯年轻的面孔吗?他读书思考,也会时而想念海格斯农场主的女儿杰茜吗?
杰茜回忆到:劳伦斯曾昵称这房子为“荒凉山庄”,因为它迎风而立。那房子有广阔的视野,可以望见小山谷中的房屋和更远处的草地,那是海帕克森林开始的地方,劳伦斯告诉我他曾望着天边的云影拂过田园。
这时天空飘起小雨,小村裹在烟雾中,田野水雾横生,绿烟飘渺。
我恍然悟得他浓烈的乡情,他爱这里的风和日丽,霓红天蓝;也爱这里的风狂雨骤,或者雨止雪霁。更何况桃花雨杨柳风,四季更替,岁岁不同呢。作家透过这扇窗子,看时光在日日晨昏,年年枯荣中流淌,他吐纳天地灵气,触发千万灵感,攫获了惊人的才华。
对故乡的情他经历了童年时完全地接受,青年时批判性地拒绝,和中年时深深的回归与思念。1929年,也就是他44岁病逝于法国南部尼斯的前一年,在一篇忆乡的文章中,他深情地写到:对我而言这是异常美丽的村庄,曾经这么觉得,现在仍是。
我突然触摸到作家的心灵深处,这个笔端惊世骇俗的大作家,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仍是故乡伊斯特伍德。他一生颠沛流离,最终客死他乡,骨灰不能归葬;但是,他的心从未离开过伊斯特伍德这一片芳草田园,因为,那是他心灵的故乡!
<5>
煤矿关闭后,小村渐渐遗忘了近一个世纪的怨恨。他们多少有些惊讶地看到,印象中的浪子劳伦斯已成为了誉满世界的文学家。他的书在不少国家都经历了诋毁——争论——接受——赞叹的过程,比如最开放的美国,比如最传统的中国。溢美的文字从世界各地蜂涌而至,小村第一次脱离了它引以为傲的煤矿,它感到是精神的富盈。小村开始展露笑颜,先是认可了他,接着尊敬他,最后甚至画出蓝线来纪念他、推崇他。他们骄傲地说,这是全英第一条蓝线呢,灵感还取自美国波斯顿的红线。
我在街角看到一个招牌“劳伦斯点心店”,劳伦斯跳进我的眼睛,把后面的点心店漏看了,急急地往里面冲,看见一个老爷爷穿着白色的围裙,赶紧问:“劳伦斯的故居博物馆在哪?”他笑着说:“噢,劳伦斯?出了这门,沿着蓝线,一直走,再往右转,他就在街角出生。”说着亲自为我打开门,道一声“祝你今天愉快!”
寻找劳伦斯在小村最后的住处时,我拿着小纸条核对街名,忽然听到背后一个声音“找劳伦斯?”我立刻回头,见一个油漆工人,穿着一身蓝,上面有斑驳的油漆污点,“过了马路,就是前面那座房子了。”“哦?”我仍不解,他干脆放下手头的活,把我领到门口,喊一声:“嘿,就是这里啦!”
“劳伦斯?”那微微上扬的语调,就像我是向他们打听一个告别家乡的老友,把这名字念得那么亲切。
他当年学习的博维尔寄宿学校(Beanvale Board School)也已更名为格瑞斯里博维尔——戴·赫·劳伦斯幼儿学校了(Greasley Beauvale D.H. Lawrence Infant School)。长长的名字里硬是塞进了劳伦斯的大名。看来,在西方还是不能免俗,就像 宁波溪口镇蒋介石故居旁“蒋介石的邻居周顺发千层饼店”长长的招牌一样良苦用心。
劳伦斯协会,一个拥有国际会员的组织,常在伊斯特伍德开会。伊斯特伍德图书馆里也专门设有一间劳伦斯室,专门存放他的作品、手迹和其他收藏。我还路过一间白孔雀茶屋,想必这取自他的第一部作品《白孔雀》。小村里还有D.H.劳伦斯工艺中心和彩虹画廊,走在街上,也常能见彩虹一号的巴士,也许是取自《虹》吧。百年后,劳伦斯的影子在小村可真无处不见。
至此,我确信,人们早不再怨他了,小村也早不再怨他了。其实,小村与作家,本就彼此融合,作家的文字脱胎于小村的灵气,万物的造化,而小村的美又通过作家才情横溢的笔才生动地复活并不朽。
晚了整整一个世纪啊,伊斯特伍德村才承认劳伦斯是他的杰出的儿子。也许并不晚,因为小村不觉得过了太久,一百年像刚从指尖滑过。
一百年在中国早已翻天覆地,而一百年在英国的小村却步履缓慢。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