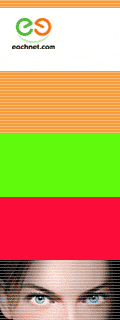|
作者:曾明奇
如果让我参加现在的高考,结果只能是名落孙山。1971年毕业的初中生,语文不知主、谓、宾,数学到一元二次方程,物理到杠杆原理,化学和外语则没有开设。两年半的初中就这样上完,居然被誉为“知识青年”,“光荣”上山下乡,其实最多是个“识字青年”,按现在的标准,半文盲。参加1978年高考,能骗得一纸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实属运气, 偷着乐了许久,有些像时下买2元彩票中了500万特等奖。
记得在高考报名时,就有不少知我底细的人劝我“不要太冒险”,“中专未必能考上,还考大学?”他们的话自有道理。学业因遭遇“文革”而荒废,最厉害的其实不是66-68年初中、高中毕业的“老三届”,因为“老三届”中不少正规完成了高中或初中学业,至少正规完成了小学教育,而69-71年初中毕业的所谓“新三届”,小学四五年级便开始了“闹革命”,实在没学业可言。我当时就正是这样一个仍在农村就业在岗的“新三届”。在这种背景下执意要报考大学,我才发现自己老实的外表下,有一颗贪婪的心。
是多久变得贪婪的,说不大清楚。1971年当“知识青年”时,我不到16岁。因为读不成书了,就愈加向往读书。白天田里背着太阳过西山,晚上就对着煤油灯认字,把一本新华字典翻得差不多了。偶然在一个社员家中看到一本没有封皮的书,便借了回去。一天晚上正读着第X遍,驻生产队的县农水局干部任同志闯进来了。他好奇地把这书翻了翻,问:“这是啥子书?”我答:“好像是《一千零一夜》。”他没听懂:“啥子呢?”我答:“又叫《天方夜谭》。”这下他听懂了。几天后的社员大会上,任同志挥着那本破书,怒不可遏地说:“有的人在毒害知识青年,上面全是黄色的故事!难怪叫天方夜谈,为什么不敢白天谈呢?”我心里发虚,生怕以后让公社干部知道了,印象不好,便连夜写了检讨交上。这是我离开校门后写的第一篇“作文”,三页纸,主要谈白天与夜晚的关系,亦即红太阳的温暖与阶级敌人的阴险,以及红色江山变不变色的问题。这篇检讨深得任同志的好评。因此,我的写作信心大增,心想,将来当作家也未可知。以后,便学着雷锋写革命日记。朝思暮想的是“有志者誓进城”,但日记通篇是“扎根农村闹革命”的豪言壮语,想着万一有机会,这日记是可以见报的,未必比《雷锋日记》或者《金训华日记》的境界低。动机不纯,但造句的能力由此突飞猛进。于是又生出当诗人的野心,把好不容易弄到的一本《宋词选》带在身边,每天进行野蛮装卸,生吞活剥。上了瘾后,只要是铅字的书都读,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马恩列六本原著解读》,以及阶级斗争“小说”《金光大道》等。就这样在农村混了7年多,才突然遭遇高考。
待上了考场,才发现自己与身边的许多考生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那是因为自己“偷跑”了一大截,偷跑了好几年。在那“知识没有力量”甚至“知识就是愚蠢”的年代,我的同龄人忙着干其他的事去了,我则歪打正着学会了写字和造句,记住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识”,虽然学得不系统,正好对付这同样粗糙的考试。记得历史试卷上有一道题,大意是解释“什么是司芬达克之迷”。题虽简单,但复习大纲上没有,教科书上也没有。我一下就想起了《马恩列六本原著解读》的注释上,有人面狮身出谜语的故事,我当时读过好多遍。于是便不厌其详地答,想露一手给阅卷老师,如果其他题答得不好,请看在此题的情面上包涵一点——那时不知老师阅卷是流水作业。我猜想那个考场也许就我一人蒙对了。
“偷跑”的半文盲混进大学,已经是老大不小的23岁了。不过班上还有老大——38岁的老知青,他的孩子与他同年高考。再了解,像我这样混进大学的“新三届”并不鲜见,有一个居然是小学毕业,富农的儿子。问他怎么居然得手,他说是“笨鸟先飞”,也有“偷跑”的意思。他读硕士后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成了教授。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所大学任教。住一个寝室的老陈,是老三届初中生考上北大的。问他诀窍,他说纯属运气,他只是在下乡的三年中,自学完高中数学。回城进厂后,耐着性子读完了4卷本的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我心想,难怪,原来他“偷跑”得更厉害。
77、78级大学生,只是当年考生的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九十九,作了陪衬,他们的大学梦,只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我常常想对他们的孩子说,请原谅和理解你们的父母,如果那时考上大学得力于自身的话,没考上的就有太多非自身的原因。若你今天能代父母“偷跑”一截,快慰的是三代人。
作者简介
曾明奇 四川省彭山县人,1956年1月出生。1971年1月初中毕业后,插队到农村,栽秧打谷,守水碾,当代课教师。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2年分配到西南政法学院任教。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研究生班。1989年调四川省监察厅杂志社工作。1994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8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现在中共四川省纪委研究室工作。
免费试用新浪15M收费邮箱 赶紧行动!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突发事件、重大新闻尽在掌握!
| ![]()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
本网站由北京信息港提供网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