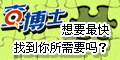| 性 SEX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11/13 18:41 新浪教育 | |
|
我刚到温哥华,就有中国同学问我去过Wreck Beach了没有,叫我很纳闷,因为温哥华有海滩无数,不知为何他偏问起这一个,我一追问,他就含含糊糊地说,你到网上去查查吧,一看就知道了。我忙着搬家,也没顾上打破沙锅问到底。没想到,等我搬完家,又有住邻居的中国同学问,去过Wreck Beach了吗?才知道它居然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问她,那儿有什么稀奇的吗,为什么总听人提起它?她神秘兮兮地一笑,说你自己走一趟不就知道了,不过最好挑一个天气好的时候。 于是,在一个晴好的星期天下午,我就按邻居指的路去找Wreck Beach了。真是不远,穿过马路,走了不足五分钟,就看见了指示牌,但还要沿着石阶往下走一段山路。路上游人不少,很像是底下有什么热闹。快走到底的时候,我眼前突然闪过一片白光,定睛一看,却发现前面居然走着几个赤身露体的男女!我一惊,再往不远处的沙滩上细瞧,更是一片白花花明晃晃。我这才恍然大悟,Wreck Beach原来是个天体海滩!国外的天体海滩早就听说过,但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虽很想去见识一下,可一时要做这么大的决定还是叫我进退两难,鼓了半天勇气,终是掉头回来了。]回来才听住邻居的同学说,那里虽是天体海滩,但“Clothing is optional(穿脱自便)”。我于是提议说,要不咱俩一块儿去,有作伴儿的胆还大点儿。自己不必脱光示人,只是看别人的西洋景,这还算是循序渐进。不过,去之前我还是找了个墨镜戴上了。 躲在墨镜后面看,不仅自己坦然多了,那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肉身也不那么晃眼了。沙滩上果真热闹,除了看书晒太阳的,人们多是三五成群,像是开野餐会,有吹拉弹唱,也有摆摊设点卖各种工艺品的。除了这里的人们少穿了些布片,以及空气中偶尔能闻到的可疑的烟草气味,这样的情形其实跟大多数海滩也差不多。穿着衣服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虽故作镇定可看上去一律鬼鬼祟祟的,令我自己反倒觉出穿衣服的不自在。走了一圈,居然还碰到了班上的两个中国男同学,当然是穿着衣服的,而且也都戴着墨镜。他们说,我们还琢磨着能找见俩儿熟人呢,没想到是你们,还穿戴如此整齐,太失望了!我们自然也用同样的话反唇相讥,于是都哈哈一笑,心领神会。 因为离得近,那里又山青水秀,还是看夕阳的好地方,后来我时常会去Wreck Beach走一走。不是总能见到天体,而且慢慢地,即便见到也习以为常了,有时迎面遇见还会打个招呼。有一次,我居然还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心想:自己不以为然的态度至少能给洋人一个印象——如今的中国人可不比从前了,别以为你光着腚就能把俺们吓跑。 海燕:今天是2002年4月3日,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标题是《大学教授走进中学课堂唠家常,性知识开启全国第一课》,我不妨摘录在这里: “今天上午8时,一节特殊的课程在哈尔滨市太平区嵩山中学初二(9)班的教室里开讲了,同学们发现,今天走上讲台的不是本校老师,而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王忆军教授。而王教授今天所讲授的内容则是中学生们懵懵懂懂的性知识。” 同时,又有消息说:“最近,我国首部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系列教材由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到了21世纪了,性教育才开始在中国起步!海燕,看到这消息,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恨不能跟着孩子们一起从头补补课? 与性相关的知识,包括对人体的认识、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性生活的了解,海燕,如果叫你把从小到大接受过的这方面的教育搜集起来,自学摸索的除外,你能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画吗?实话实说,我不能。真不知我们中有多少人,都是长到老大不小了,还以为男人女人只要在一张床上睡觉就会生出下一代来呢。 要说我对“身体”的最初认识,也不算太晚,但却是很抽象,也很有思想高度。海燕,你还记得吧?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常要写决心书发言稿什么的,表达作为一名红小兵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具体的表现就是要争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有时我功课忙不过来了,我就会央求父亲代写,有一次他在德智之后替我表达在“体”上的发展决心时,大笔写下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虽然年幼的我对“本钱”一无所知,但也发觉了这样表达的新奇,而且居然还能跟革命挂上钩。事实证明,它果然得到了老师的青睐,选了我到少先队全体大会上朗读,这令我对父亲的文采一度很是景仰,至今我还能记起父亲写下那几个大字时迥劲的笔迹。 而对身体的理论认识,海燕,你我都是始于初中的生理卫生课吧?在我们那里,它不属于升学会考科目,一般的学校就不开了,因为我上的是区重点,所以还侥幸有机会听一个女老师给我们讲讲人体构造什么的。这个老师虽是女的,可样子很严厉,讲话又快,课堂上总是她急促促地讲,我们闷着头听,学生提问在任何课上本来就是没有的,但在她的课上我们连被提问的机会也没有。有一次,她匆匆忙忙间反复将“脂肪”口误成了“乳房”,我们几乎都听出来了,但也只有涨红着脸把头低得更深。课本的最后一章讲的是生殖系统,我们原来还私下议论,说是到了这一课肯定得男女生分班上课,没想到,上到学期末,老师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一章由同学回家自学,也不会在考试范围之内,结果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停在了泌尿系统上。还记得,我和一个女同学考试前一起苦背“尿的形成”,被一个男生听到了,就朝我们用手刮着脸,大声斥骂:“不害臊!”由于他是一个被老师同学普遍认定有流氓习气的差生,我们又羞又怕,可也不明白,既然泌尿系统是在考试范围内的,怎么也跟生殖系统一样是不能公开背出来的呢? 至于我对女性的认识,也压根儿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按理说,初潮应该是女性成长中的一个里程碑,但咱们经历时,不要说什么成年礼了,大概都是慌慌张张地以为自己病了吧。我跟母亲说了后,她立即踩了缝纫机做出一条卫生带来交给我,除了交代以后每个月都要用到,也没有多说是为什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那只是我一个人的麻烦。初一时有一阵儿,我同桌的女生坚持说她要死了,说是得了一种不能说的病,现在想想,那极有可能是她来了初潮。她神秘的样子把我紧张得每天都担心身边的座位从此就是空的了,却没能想到同桌也可能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叫我一直苦恼的,还有一天天鼓胀起来的胸脯。母亲给买的衣服从来都是宽腰大摆,不可能有什么紧身衣。有一年去海滨夏令营,我斗胆穿了件缩了水的上衣,回来后见到照片上自己轮廓分明,羞得不敢拿给人看,更不敢拿给母亲看,知道她肯定要说“女孩子这样不好”。所以,每次体检量胸围时,我都尽量含胸,巴望着被大夫大声叫出来的数字能小点。这在今天看来,真成了荒唐。 到了高中,你知道,我是在一个男女分班的学校。我和我的女同学们不要说没有机会在异性面前撒娇发嗲抛媚眼做小女生状,反而因为没有男生在场都撒了欢儿地笑闹成团,而且,到了做卫生擦玻璃的时候,还要登高爬梯地站到窗台上当差,不知不觉中培养了许多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海燕,你还记得邓丽君吧,第一次听到她的歌时,是在高二,从班上的几个男生那里。那时候她的歌是被定性为“靡靡之音”的,看他们把不知转过多少道手、翻录过多少次的一盘盒带传来传去地听,我真不明白,那么嗲声嗲气的一个资产阶级小女人,怎么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无独有偶,最近看到一个当年的傻小子,回忆第一次在学生宿舍听到邓丽君歌曲对他的震撼:“我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正着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或反着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之外,也可以仅仅唱唱风花雪月、卿卿我我、打情骂俏、个人悲欢;我也第一次知道,歌曲除了可以唱得高腔入云、慷慨激昂之外,也可以唱得如诉如泣、哀婉低迷;我也由此第一次悟出,人生并不仅仅是路线斗争、四化建设、国际风云、民族大义,人生还有儿女私情、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生老病死。”足见,不分男女,我们那时都是不解风情地瞎长的。 有一年国庆节,市里组织大型游园活动,我们班干部有幸参加,学校还破天荒地放开统一着装的要求,鼓励我们“把最好看的衣服穿上”。我们几个女同学都决心要充分用好这难得的自由,早早地就开始盘算,可商量来商量去,到头来,我们竟然没想出一个比穿西装打领带更诱人的方案!我自己倒是一咬牙,花掉了多半的积蓄,买回来了平生的第一双高跟鞋,却没想到新鞋夹脚,只好忍着疼游了一天的园。那一天,我们都觉得有必要为我们的崭新形象立此存照,就凑钱在摄影摊儿上照了一张合影,又叫一个同学的妈妈带到美国加印了,才人手一张,那时候彩照还很稀罕,我们都对它珍爱极了。 可是,待十几年过后,我和其中的两个同学在美国碰面了,讲起这段往事我们都一概地哭笑不得,不禁相互埋怨起是谁想出这么个馊主意。而且,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承认,从女生班毕业后,在大学里第一次跟男生跳舞时,谁都是慌张得不知所措。海燕,你想想看,几个花一样的少女,在她们的几乎是平生第一张的彩色照片上,却是穿着不伦不类的西装、打着从爸爸那儿借来的男式领带的模样!是呀,是谁让我们想出这么个馊主意,真应该找他索赔! 说到这,叫我自然联想起我在美国参加过的一个夏令营,我是作为辅导员去教那些十几岁的中学生的。我们的营区是设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小湖边,虽然环境优美,但住的是简陋的小木屋,吃的是几个大学生营员自己做的所谓中国饭,防不胜防的蚊子更叫人苦不堪言。但就是这样,也没挡住女孩子们的爱美之心。有一回我们组织周末饭馆活动,不过是把平常吃饭的木桌用白纸包起来,把饭菜多装几道碗碟,由我们几个辅导员充当服务生罢了,可女营员们无论大小,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分外妖娆。我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还穿上细细的高跟鞋,昂首挺胸地走在土路上,像是去赴豪门盛宴。海燕,毫不夸张地说,这情形真的打倒了我心里的五味瓶,我不由得想起我们小时候,母亲批评我爱打扮的大妹时常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不把这点心思用在学习上?!”海燕,在你过去学习成绩下降的时候,你的老师家长是不是也会找找你“对镜贴花黄”方面的原因?可我根本没理由这么教导我的美国学生,因为打扮得最用心的那个正是我班上学得最好的一个。 如果再说到对性的了解,就更是捉襟见肘了。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上高中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上海女作家写的小说,大概是程乃珊吧,里面有一个细节,说女主人公出门去见一个她喜欢的男人前特意换上了件绣了花的内裤,这叫我纳闷了很长时间才恍然大悟。海燕,是不是你也告诉过我说,你的同学中有一个男生名叫Yang Wei,你以及你的绝大多数同学却始终没有发觉其中的不妥,直到毕业后在街头电线杆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治疗性病的小广告,你才明白是大家的普遍无知才使Yang Wei同学没有因父母的失察而在冷嘲热讽中抬不起头来。 咱们刚参加工作那阵子,有一天,一个新婚不久的朋友找到我,却是一付苦恼得不想活了的样子,说是跟丈夫闹别扭了,他们俩谈恋爱时甜蜜得人见人羡,刚结婚就这样,叫我也不由得跟着泄气。没想到,她吞吞吐吐地绕了半天圈子,终于说是“那事儿”上的问题,她说她害怕极了,根本做不了,丈夫也是断不肯“强奸”她的。我知道这是件多么难为情的事,她说出来肯定是难受到极点了,可我除了诚惶诚恐地听着,生怕自己的哪怕一丁点儿不小心伤了朋友的自尊心,却也真的无计可施,不知怎样做才能帮上她的忙。事后,我突然想起咱班上的一拨同学曾传看过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录像带,里面是讲性如何美好的,我想可能会对我这个苦恼的朋友有帮助,便顺藤摸瓜地追查录像带的下落,发现是到了一个男生手上,就跟他约好了晚上下了班去他那儿取。记得那是个冬天,他住的地方几乎在城边上,我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想到他会到车站来等,我一下公共汽车,就见他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将包在一团报纸里的录像带递到我手上,我下意识地还想打开,“赶紧装包里吧,”他催促着,“我出来等你就是为了不让人看见。” 海燕,你说,怎么那时候交接一盘有性描写的电影录像带也搞得跟贩毒似的?当然,当时的情形可能也没有我今天回想起来这么夸张,大概是那种黑咕隆咚的印象太深刻了的缘故吧。 也许是吸取了这个朋友的教训,后来看到书摊上陆续有卖关于性的书,就都买下来,在咱们几个女友间传阅。其实那大多是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深奥的学术著作,还探讨些女权主义什么的,可咱们照单全收,总算恶补了一下。海燕,你还记得吗?恶补中间,正赶上一位要远嫁,咱们一致决定买了套价格不菲的真丝睡衣给她做礼物,粉红色的低胸款,性感极了,她接过去居然马上就猜到了,立时羞得脸也粉红了。 海燕,除了黄段子,我们中国人通常是不会公开讲性的,即便是在你我这样的朋友甚至姐妹间,都很少会交流关于性的话题。其实,我这里讲到的,还只是些边边角角,也不敢肯定是否就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我最近看到,新近完成的“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发现中国夫妻当中只有27.1%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又有数字显示,在中国近几年的离婚案中,有34.7%的离婚案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我就推测,像我那样在性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成长,到底是不在少数,而且贻害竟如此之大! 所以,当今天还听到有人以“性是无师自通的”为由反对实施性教育,我几乎要拍案而起了——交配可以无师自通,而性却是要启蒙的,美好的性事更是要两个人的学习才能共同完成。海燕呀,对飞飞的性教育,如果学校还不教,你自己也千万要教,否则,耽误的可就是她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生趣了。 人文格言 Love is the answer, but while you are waiting for the answer, sex raises some pretty good questions. 爱情是答案,但当你还在等待爱情的时候,性却提出一些不错的问题。 ——Woody Allen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我们配做父母吗? > 正文 | |
|
| 新 闻 查 询 | |
|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 |
|
| |||||||||||||||||||||||||||||||||||||||||||||||||||||||||||||||||||
企 业 服 务 | |||||
秋意浓浓美妙重重!(京) 心的冬季旅游(豫) 牛皮癣鱼鳞病重大突破 谁说糖尿病无法治愈! | |||||
| 分类信息刊登热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