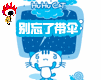| 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3)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7 18:11 新浪教育 | |
|
这个世界怎么了 在市场环境下,个体理性导致群体理性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一样东西被出卖的价格既等于生产它的成本(更精确地讲,是多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即边际成本),也等于它对于消费者的价值(更精确地讲,是消费更多一个单位产品的价值,即边际价值)。当你在竞争性市场中购买了一个苹果或一个小时的劳动时 尽管这样的情形具有普遍性,但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当我的钢铁公司生产出了一吨钢,我支付给工人们的劳动成本,我支付给矿产公司原材料的价格,但我不支付任何东西给那些处于下风口吸入了我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的人们。在决定生产多少钢材和如何生产时,我作出了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的决定,这也是一个使我个人、我的供应商和消费者以及处于上风口的所有人的净收益最大化的决定,但并不是一个使所有人的净收益最大化的决定。 既然我为生产钢材支付的成本小于实际成本,我最终以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出售了钢材。由于人们购买钢材的数量部分取决于它的价格,一些人最后购买了过多的钢材。从涉及到的每个人的价值来计算(包括那些处于下风口的我的邻居),如果我们生产和消费的钢材少一些,并使用其他替代性材料,这些价值的总和会更大。 这些外部成本的存在导致我生产了过多的钢材,同时还导致了我没有对环境污染采取足够的控制措施。有一些方法能够减少我工厂制造的环境污染:如不同的生产程序、更清洁的燃料、更高的工厂烟囱、过滤装置等。如果我在控制污染上花费1美元就可以消除价值2美元的污染损失,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以1美元的成本换取2美元的收益。但是这种成本是由我来支付的,而受益者却是处于下风口的人们,所以从我的利益出发我不会这样做。 问题不仅仅在于污染是有害的。所有的成本都是不好的,这是之所以称它们为成本的原因。我们之所以愿意负担某种成本是因为通过交换我们可以取得收益;我们之所以在非常想玩的情况下也愿意去工作,是因为工作生产出有用的产品。外部成本的问题,如污染,使得我们在计算什么事是值得去做而什么事是不值得去做的过程中忽略了它们的存在,结果既可能导致了有经济效率的污染,即防治的成本要大于污染自身的价值,也可能产生无经济效率的污染。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直接制定法规:一些政府部门,如美国环保署(EPA)制定了一些规定要求钢铁厂过滤它们产生的黑烟,或者修建更高的烟囱,或以其他方式减少污染。虽然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它还是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环保署可能对使效益最大化不感兴趣。钢铁生产者、煤炭生产者、过滤设备和擦洗器的生产者也都是有投票权的人,并且是潜在的活动参与人。没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各种政治活动的效果的总和会与最终控制美国环保署决策权的政客们的利益相一致,从而后者运用权力来产生一个有经济效率的结果。举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例子,如果来自生产高硫煤的州的参议员们掌握了足够的政治势力,那么法律规定就可能被用来鼓励使用擦洗器,即使使用低硫煤是控制污染的更有经济效率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美国环保署意图使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它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通过计算得出何种控制污染的措施是值得或不值得去采取的、考虑到外部成本后计算得出钢铁产量具体应该是多少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不同的钢铁公司提供不同的控制方法的成本和收益的具体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绝大部分控制在钢铁公司的手中,而非规则制定人的手中。如果美国环保署只是简单地询问一个公司它是否知道任何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法来控制它的污染,答案显然是不知道,因为如果美国环保署相信根本没有任何低成本且高效率的控制方式,该公司就可以继续制造污染而不必承担任何控制污染的成本费用。况且,钢铁公司的答案有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如果某种知识只会使你的情形更糟,那有什么理由还去学习它呢?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控制消极的外部性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更倾向于一种不那么直接的规定。规则制定者只需对公司造成的污染收取费用而不必告诉他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如果制造1吨钢将产生20磅的二氧化硫,其损失相当于4美元,这个公司就会为每排放1磅二氧化硫支付20美分。 这种被称为“排污费”(普遍称为庇古税,由经济学家A.C.Pigou提出)的方法在控制污染中相较于使用直接性的法规具有以下优点。首先,规则制定者无须知道任何有关控制污染所需的成本,他完全可以放心地把这个问题交给钢铁公司。如果该公司可以以低于20美分1吨的成本减少污染排放,这样做就符合它的利益。如果公司抗议说根本就没有不产生任何污染而制造钢铁的方法,那美国环保署会礼貌地接受它的陈述并寄给它一张支付排污费的账单。 其次,该方法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计算出正确的污染控制量,而且能得出正确的钢铁产量。现在钢铁公司生产钢的成本包含了其控制污染所需的成本,也包含了如果控制失败它需要付出的成本。所以钢材现在的出售价格代表了生产所需的所有真实成本。当钢材比水泥便宜的时候,人们就会在建筑中使用钢材;反之,则使用水泥。 不幸的是,排污费并不能解决控制污染中的所有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它无法解决规定制定者的利益问题,以使他们永远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们有可能故意将排污费定得过低以换取对立法官员的政治支持或谋求未来的职位;或者他们也有可能将排污费定得过高来惩罚那些支持了错误的候选人的公司。 即使规则制定者力图产生有效率的结果,他们也可能很难计算每一磅多排出的二氧化硫或二氧化碳或其他物质所造成的损害。但至少其中的信息问题较之于直接规定的方法要少,因为规则制定者不再需要知道如何控制污染以及成本是什么。对于有关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依旧存在,也应该可以被减少,因为当决定是根据污染物而不是污染公司作出的时候就很难对你的朋友有特殊优待了。 至此,我已经介绍了美国环保署等立法机关可能采用的庇古税。相同的分析可用于解释侵权法中的大量问题。替代美国环保署征收排污税的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允许处于下风口的人们因钢铁公司排污而对他们的房屋、衣物和内脏器官造成的损害提起诉讼。钢铁公司可以在消除污染、赔偿损失或减少污染并赔偿剩余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中作出选择。 这种分析也可应用于违章停车罚款和超速行驶罚款。如果我驾车过快,我就在制造一项新的成本,即将更多的事故危险加之于其他司机。在我被发现超速时,法律通过罚款强迫我将此计算在自己行为的成本中。 当然,这些例子中也存在差异。因受到侵权所获得的赔偿归受害人及其律师所有。罚款收归国家。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差异,将在以后的几章中讨论到。 但是这三个例子的基本逻辑是相似的。行为人实施了某一行为并将成本加诸于其他人身上,只要该行为可以使他的净收益增加,那么采取该行为就是符合他的利益的,即使这样做会导致其他人的损失。我们通过强迫行为人自己承担外部成本的法律规定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外部性内化。现在行为人的净成本等于所有人的净成本,因而他将在也只有在能产生净收益的情况下才会实施这一行为。个体的理性与群体的理性紧密联系起来。尽管它远非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不失为一种恰当的方式,这一点你会在以下各章中看到。 寻租:如何避免拱手相送我早些时候提到过一种特殊的外部性,即所谓金钱性的外部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没有招致任何净成本,因为其行为作用于其他人的效果互相抵消掉了。不同于其他的外部性,金钱上的外部性并不会导致无效率,因为行为人自身的净成本等于所有净成本的总和,就如同没有外部性一样,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举的例子是当我的邻居在卖房子时,我通过将自己的房子置于市场中出卖来施加到他身上的外部性。 这个例子同时也表明,我的邻居不应该从我这边为其房屋的降价而受到补偿。竞争不应该是,也不是一种侵权行为。普通法中的这一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1410年,当时一个学校的所有人因一个竞争者从他的学校中拉走了学生而起诉那个竞争者,结果败诉了。 一个聪明的并且是淘气的读者可能会建议将此类论证扩大到偷窃的竞争中去。当一个小偷从我身上偷走了50美元,他有了50美元的收益,而我损失了50美元。其结果只是一种转移,因而一个只关心效率的经济学家没有理由提出反对。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说:仅仅因为竞争不构成侵权,那么偷窃也不应该构成犯罪呢? 当然不是。当A的一种行为在B和C之间导致了一种转移,一种金钱性的外部性就产生了。这种情形下的逻辑与A的行为导致了A和B之间的转移是截然不同的。 偷窃并非是一项无成本的行为,它涉及时间、训练和一系列的风险。假设我成功地偷取了你的钱包所付出的总成本,平均来说,是20美元。我以20美元的代价取得了50美元,所以对于我来说,偷你的钱包是值得做的一件事,我会有30美元的收益。但后果是以20美元的代价将50美元由你转移到我,这使得我们净损失了20美元。 进一步讲,请思考一下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如此精明,那么后果会怎样呢?既然花费20美元的努力就可以获得50美元的收入,偷窃就会同样对他们有吸引力。偷窃事件的发生就会迅速增加。 随着数目的增加,这一行业的利润就会下降。一个不小心露富的人马上就会被六个扒手盯上,而其中只有一个人会幸运得手。随着钱包被偷的危险的增加,你采取保护措施的动机也随之加大了。人们开始把钱装在鞋子里,这样偷起来就会比偷口袋里的钱困难得多。 只有在成为扒手不再是有利可图的时候,这样一个过程才会停止。最终会出现很多扒手,他们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而放弃了生产产品或财富的工作而去进行偷窃。受害人失去的大部分金钱用于补偿罪犯的时间和努力,从而使净损失基本等于被偷的钱数,前者可能会比后者少一点,因为一些偷窃高手在这一行当中赚的钱要比他们做其他事情取得的收入多一些。 至此,我们一直对受害人因采取预防措施而产生的成本忽略不计,如一个小变化会使脚走起路来酸疼,时刻留意周围的人会使眼睛发涩。如果我们将这些也包括在内,那偷窃的净成本就增加了,它可能变得比被偷的总钱数更大,而不会是更小。 描述这一现象的通用术语叫“寻租”(rent seeking)。当人们有机会通过花费一定的资源而将别人的财富转移给自己时,寻租便发生了。从接受方的角度看,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这种转移就是值得的。当更多的人竞相成为财富的接受方时,这种收益就会下降。平均看来,处于边缘的财富接受方(最不聪明的扒手)恰好达到收支平衡。而远离边缘的财富接受方(尤其是那些有天份的扒手)就会有所收益,即使其收益要小于受害人的损失(即便是有天份的扒手也会付出一定的成本)。受害者既失去了被转移的钱财也失去了为保护钱财采取预防措施而付出的成本。 寻租在很多场合下都会发生,本书会涉及其中相当一部分。这个词被制造出来用以形容为获得政府优惠而进行的竞争——在最早的进口许可证的例子中,政府在进口业务中允许许可证持有人以表面上低廉的价格去购买外国货币,各个公司通过公共关系、游说、资助竞选及贿赂等各种手段力图争取到这种优惠。只要可以用明显少于100万美元的代价获得100万美元的优惠,就会有其他的公司愿意出更高一点的价格,平均而言,最终获胜的公司就会付出优惠所值的价格。最初使用寻租一词的安·克鲁格(Anne Krueger)曾估算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当时还存在交易控制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的国家里,因为进行这种没有生产效率的竞争而损失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10%。 诉讼是一个不那么明显的例子。诉讼各方都会花钱在雇佣律师、专家证人等事项上来增加胜诉的可能性。原告为了增加从被告方获取转移的机会而花钱,而被告为了降低这种机会而花钱。这种转移本身既不是一种净收益也不是一种净损失,而用于诉讼中的花费是一种净损失。 诉讼之所以是一种不太明显的寻租例子是因为至少花费是有可能产生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如正确判决可能性的增加,或引发制度中其他方面的改善。通过允许处于下风口的人们对排放污染的工厂提起诉讼来控制污染的方法只有在排放污染的工厂比不排放污染的工厂更有可能败诉的情况下才会奏效,换言之,只有在法院至少有一些达到正确裁判的倾向时它才会奏效。而双方在证据和辩论中的花费使这种结果变得更为可能。 错误之产生:市场诉讼中的欺诈一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发表了一篇乐观的演说。六个月后,他们的最新产品被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公司的股价随之下跌。一位有胆识的律师代表所有在演说之后和股票下跌之前购买了公司股票的人提起了集团诉讼。他的论点是:在那篇演说中,该公司隐瞒了可能导致悲观结论的有关事实,欺诈性地诱导人们去以超过其真实价值的代价购进该公司的股票,从而该公司应补偿这些人的损失。此类市场中的欺诈诉讼偶尔有可能获胜。由于潜在的损失极大,所以原告获胜的极小机会都足以促使一些被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选择庭外和解,从而使这类诉讼为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律师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这类案件背后的理论存在诸多问题。首席执行官们与其他人相比并非更加无所不知,从而将一个被证明为错误的乐观声明变成一个可提起诉讼的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自由决定谁的预测是值得相信的。一个将乐观性演说和声明作为福音的投资者最好还是将他的钱锁在抽屉里。 与本章尤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来计算损失。即使我们承认演说是一种故意的欺诈,赔偿责任还是要视损失而定。假设我从你那里以100美元的价格买到一股,后来该股跌至50美元。如果该演说和我的购买行为没有发生,该股还是会下跌;惟一的区别是,是你而不是我在持有它。由于我听信了首席执行官的话而损失了50美元,而你获得了50美元的收益。 至此,该首席执行官的演说仅仅是导致了该股份下跌时持有人的不同,外部性完全是金钱性的因而不应导致任何责任的产生。只有在我从该首席执行官手里买了该股票,从而使他的演讲导致了从他到我的一次转移,而改金钱性的外部性为寻租时,才会有一种纯粹的外部性。 在接受原告有关如何计算损失的理论时,法院已经作出了在经济学上没有效率的判决。其后果之一就是公司的执行人会由于作出了可能错误的预测而受到惩罚,并由此导致了投资人可以得到的总体信息的降低。后果之二就是将用于生产更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资源引向了诉讼。 这一理论的维护者可能会辩称,即使赔偿给付与实际造成的损失无关,它为受害的股票持有人也提供了一种诉讼的动机,从而使公司的执行官员不敢做欺诈性陈述。问题在于可能获得的损害赔偿越高,当事人就越有动机去诉讼,即使只是对一个无充分理由的案子,从而大量的大标的案件导致了高昂的诉讼成本。一个人可能基于同样的理由争辩道,既然我们要阻止非法停车,那任何发现非法停泊车辆的人都应被允许主张对该车辆的所有权。这里如同在许多其他案件中一样,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动机而是正确的动机,这一点在以后章节中还会有所论述。 问题:我刚刚描述了一个既有关金钱性外部性、又有关寻租的案例——而又不是首席执行官作出的,请解释。 建议阅读寻租一词最初是由Anne Krueger 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June 1974 291—303)一文中提出的。然而,Gordon Tullock 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性后果》(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Tariffs, Monopoly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anl 5, June 1967, 224—232) 一文中更早、更广泛地谈到这一概念。服了他们:庇古的分析是错误的,并且错误不只一处而是有三处。首先,外部性的存在并非必然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其次,庇古税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发有效率的结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外部性,而在于交易成本。 我将分三步来介绍科斯的论证:没有起作用的因素,所有因素都起作用和视情况(交易成本)而定。 都不起作用外部成本不仅仅是由一个人产生而由另一个人承受的成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外部成本的产生与大小都是视双方的情况而定的。如果你的钢铁工厂不排放二氧化硫我就不会咳嗽;但是如果不是我恰巧处于你工厂的下风口,你就不会给我造成任何损害。是你排污和我选择在你排污的处所居住的共同决定导致了成本的产生。如果你不对你的排污行为向我负责,那你排污的决定是将一种成本强加于我。如果你承担责任,那么我居住于下风口的决定就向你施加了一种损害赔偿或控制排污的成本。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为自己创业》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