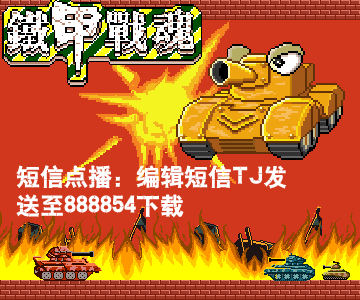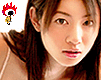结论: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
我们刚刚度过了“千禧年”庆典。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千年,应该说,这一千年是我们今天拥有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
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当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的时候,不要忘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也不要忘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参阅费尔南·布罗代
尔:《十五—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年第一版),第一卷, 第八章。) 当近代大学转而在英国兴起的时候,很快地,英国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的、技术的、艺术的支持。当十九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萌发的时候,德国接着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所或几所著名的大学,那么它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上一定是为邻国所羡慕的。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把欧洲古老大学的好传统综合在一起,又配上了美国本身的特点,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当它把英国的教化型的博雅学院、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专业学院三者融合一体以后,世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美国世纪”。回顾过去的一千年,哪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民族的兴旺、世界一流国家的崛起。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原叫“东京帝国大学”)是最著名的大学,它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成为白人种族社会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我们更不要忘记,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使中国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众多的大学,因为国家的兴起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没有大量的经过高等教育训练的专才,就不可能获得或保持大国的地位。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的竞争力、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些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众多的大学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这里的“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于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不具有这样伟大的大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临终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是创建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倡导者,而不是总统。可见在政治智者的心目中大学的重要性。大经济学家、大思想家熊彼得把现代市场经济方式称为“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说它的破坏是为了创造出更好的东西。(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0, Third Edition), pp.81—86.)大学在我看起来正是为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提供生命力源头之一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有一句话我很欣赏,他说: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很多人都在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参阅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一书中的第十三章,第154—155页。这句话是我在另一个场合下听他说的。)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中国人口占了全世界的将近四分之一,假如不能建成几所乃至十多所世界水平的(worldclass, 不等于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话,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样美丽的梦咱们中国人一个世纪来已经做过许多回了。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两个方面: 一种是“硬的力量”(hard power),大家都能理解,它包括生产力以及看得见的技术的应用,如工厂、码头、高速公路、军事设施,等等; 另一种是“软的力量”(soft power),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软力量显得尤其重要,大学更加成为这种软的力量的发源地,诸如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制度结构,都属于软的力量。它们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上。
我的简短结论就是: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全球化的纪元,资金、技术、人才都是全球化的。处于这样的时代,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而且还沾沾自喜。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我想加一句,愚昧也是力量。根据我的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机构、一所大学,它越是对外封闭,愚昧就越是容易占上风,愚昧就越是有力量;它越是对外开放,知识就越容易占上风,知识就越是有力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然不能再付出1960—1970年代那种愚昧就是力量的成本。要看二十一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的世界水平的大学。
主持人北大张维迎教授:
刚才丁学良先生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我自己听了觉得很受启发。尤其是我们学校目前正在努力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说这场报告很有意义。刚才丁博士讲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成为一流的大国,一定要有一流的大学。现在世界正迈向全球化,全球化以后,就只有一个比赛规则,而没有其他的规则。从每一个学生的角度来讲,你的知识结构能不能适应未来,在国际化竞争中有没有你的一席之地,是很重要的。在座的肯定会有不少问题,尤其是因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而照你(指丁学良)刚才所讲的,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国的附庸,这显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下面请大家提问。
学生提问:我注意到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就是十九世纪中期洪堡把研究引入大学,使之成为大学的重要功能;最近,世界著名大学(比如美国的大学)正在进行第二次革命,如“知识资本化”,把经济目标纳入到大学的功能当中去。也就是说目前大学具备了三种功能,即教学、研究,以及用我们中国的俗语来讲的创收。我不知道您对大学这个创收的功能如何看待?
丁学良答: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参阅对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的基于亲身经验的探讨:Derek Bok,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我觉得在西方国家里——我讲西方国家,因为它们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教育本身的资源来路也比较广——,创收的压力对财源比较丰富的大学来讲,不是太大。而西方一些比较普通的院校,它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最差的,是有一些纯粹为赚钱而开办的大学,人们称之为“野鸡”大学。他们国家有这种“野鸡”大学,对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他们办学本来纯粹就是为了——至少主要是为了——赚外国学生的钱。他们遇到的基本的问题,是一旦外国学生来查他们的学校资格,麻烦就来了,因为这些学校很多是“皮包学校”。它们那样搞下去,不能获得由它们所在的国家教育行业授予的资格。有人开玩笑,说美国的大学就像中国的餐馆一样多。美国的高中以上(postsecondary)的各类学校大约有一万所,但真正得到美国高等教育资格认证机构证书的也不过二千二百来所,即它们可以颁发学士或者更高的学位。资格认证根据的是几个指标,这些指标都是透明的,这些机构必须是独立于商界或者政治机构的。
中国的大学面临的创收任务,在西方研究型大学里不太会遇到,而在一些比较次的学校里存在类似的问题。不过十几年前我听说,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这些理工科很棒的学校里面,却遇到对个人创收的纪律规范问题。有些教授们做出来科研成果后,马上可以找到工业投资的机会。他该不该做,应该怎么做?他加入公司,可以做,但占的时间比重必须远远低于他在学校里的工作。他们毕竟是大学教师,他们到公司里做股东,做咨询,时间上应该有限制,好像不能超过工作时段的五分之一。另外,你在大学以外的工商活动和咨询业务,一定要向校方申报,如果有隐瞒,那就是触犯校规,严重的情况,比方说侵犯了校方的知识产权,校方会提出法律诉讼。还有,如果有一天教员发现自己真的没有足够的精力在学校里从事教学工作的话,学校可以给他们停薪留职的长假,一年或者两年。两年以后,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永久地在外面做下去,还是回到学校?
大学不断地在制度方面改进,既要给教师新的机会,又要给教师合理的新的制约。今天的大学还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有名望的研究型大学里显得更为重要,即知识和技术创新的道德、职业规范。西方现在的生物化学技术的水平,已经同我们早些时候的医学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医学里,有病吃药治病,没病不找医生,而西方越来越多的生物化学新药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主要不是用来治病,而是用它来促成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医学要让人变得更加好看,延缓人的衰老过程,增强人的性感和性欲,还要解决人的情绪问题和生活习惯,比如贪吃、吸毒、抽烟、喝酒。有些研究型大学的教授研制出一些药物,这些药物能不能推上市场,变成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的热门商品,很大程度上又是靠这些名牌大学里的教授专家们的证明——药品的好作用是多少,副作用多少,能不能广泛使用?制药公司为了能够比较顺利地通过这个公证的过程,会想尽各种办法,使这些教授专家们的表态对他们有利。比如,邀请教授专家们当公司的股东,他们的股票的价值就跟新药品上市挂上钩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解决不好的话,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会成为公司的马前马后走卒。前年(1998)哈佛大学校庆的时候,曾当过代校长和教务长(Provost)的著名教育家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提出了三个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在二十一世纪降临之际给研究型大学敲响了警钟。这个问题很复杂,它牵扯到道德、法律、科学研究的多面性,牵扯到大学对社会的责任的演变。
学生提问:刚才您说一流大学的学生的素质是多方面的,我觉得在中国非常看重考试成绩。马上7月就要到了,那么您觉得中国的高考制度应该如何改革,才能把有全面素质的学生录取到大学中来?还有,我们的高中教育,怎样为一流大学预备下更全面的人才?另外,我觉得,每一次高考,在录取了一部分人才的同时,把更多的学生卡在大学的门槛之外。我想问,一流大学如何把这些人纳入进来?
丁学良答:现在中国的大学的容量和要求上大学的青年人之间的供求关系,差距太大了,以至于大学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即使有些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或者教育部的领导干部,想采取比较灵活的措施来录取学生,都很难实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一千多年来都是“一考定终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破这个传统,上大学不考试了,凭推荐。不过,这种激进的思路其实并不是开始于“文化大革命”,至少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有北京大学的学生主张废除校长制度,废除考试和学位制度,废除毕业制度。(参阅苏云峰:《清华校长人选和继承风波:一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南港,1993年6月),第22期,下册,第180页。)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方法只实行了两三年,就暴露出一大堆毛病,因为没有正规考试,推荐又没有一定的标准,开后门就大行其道。所以,在中国社会里,要想使大学新生的录取标准既合理、均衡,又可行,就要把好几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增加多样性。比如,要把社会民间的资源引导出来办大学,只有当大学数量足够多了,有足够多的人能够上大学了,那么中国最好的大学才能在全国统一考试的硬指标之上,再发展出自己的附加标准,这些附加标准着重的是学生的独创力素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主动参与、艺术和体育等等方面的才干。同时,大学的收费也要拉开距离,好的学校、中等的学校和差的学校的收费要不同,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分层的教育市场,在分层的基础上,让招生标准多元化。补充一下,英国从二十一世纪初推动的大学体制改革,其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改变过去将近四十年里对所有的大学一刀切的收费标准和拨款政策,允许最优秀的少数大学提高收费标准(即将试行),并且增加对卓越的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基金投入(当然通过公开竞争)。(参阅Graham Bowley, “Feature: University Challenge.” Financial Times, 15 October 2004.)\
学生提问:您刚才说大学的使命,一是教学,一是研究,一是服务,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研究。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就中国的情况来讲,中国有自然科学院,有社会科学院,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同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在研究经费上存在着竞争。那么,照您讲的,为了实现大学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机构,它们和其他机构之间产生的竞争应该如何看待、处理?也就是说,在世界竞争大潮中,应该如何区别大学和科研机构、使得大学获得独到的地位,我们北京大学也因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真正成为研究型的大学?
丁学良答:今年(2000)二三月份在香港科技大学开了一个科技政策比较的国际会议,涉及到你所提的问题。我们请了美国、欧洲方面的专家,也请了国内的专家,国内是由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人去的。有好几个国家来的与会专家是研究科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的,从他们的论文提供的资料和分析,可以看出很鲜明的区别:一个国家的科研经费和科研活动分布在哪个领域里,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它的基本经济制度。一种是市场经济型的分布,应用研究集中在大中型的企业里,基础研究集中在研究型大学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这样。另一种是指令经济型的分布,科研活动和科研经费大部分集中在国家办的少数几所研究机构里边,而投入到大学、大中型企业里的科研经费则很少,前苏联、东欧、中国都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布?道理很简单,因为后一种体制下科研资源的分布是政府一手促成的,它不是多元的。当年中国科学院只做研究不做教学、把教学和研究截然分开的做法,是直接照搬苏联的。当年咱们科研体制上照搬苏联,就像那时候大学的院系调整一样,都是出于同一个简单的思路:既然落后,就要尽快赶上去。怎样赶上去?就像打仗的时候搞后勤工作一样。中国原来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截然分开的做法、中国高校院系的调整、中国原来的国有企业的配置,实际上都是出于“战时后勤工作”的同一种思维逻辑:每种单位的职能、性质都安排得很单一,单位跟单位之间没有什么自主的互动和常规的联系。这种架构,在当年与中央指令式的发展取向是吻合的。一旦中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了这么远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已经迈开大步的时候,这种架构就越来越起不到好作用了。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全国文理科学院以及全国工程科学院,都不是实体,而是一种荣誉团体,是学术成就的评鉴机构。比如,什么样的学者、做的研究成功到什么水平,才能够成为全国科学院的院士。再如,大学里一项大的研究项目做得怎么样,各研究领域的学术规范如何制定和改进,等等。你当上了院士,从那个科学院里也拿不到工资和研究经费。你的工作单位不是那个科学院,而是你所属的那所大学或研究所。这样,科学院就起着超然的、维系普遍科学规范、学科标准、学术荣誉的功能。我想,中国要想使自己的非常有限的研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的话,就应该把中国科学院变成这样一个非实体的荣誉和规范组织。而且,中国不仅在北京有一个全国性质的社会科学院,北京市自己也有一个社会科学院,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这样浪费了多少资源!其实,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该把这些架床叠屋的社会科学院融合进各地的大学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补充了教师资源, 他们个人也增加了收入。有了这样的机构调整,就不会存在研究型大学与科学院系统争科研经费的问题了。这种状况纯粹是苏联式旧体制延伸出来的问题,我希望中国政府像在经济改革上一样,用有力的方法来甩掉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苏联式旧体制,以此为基础来解决普遍存在的教育和研究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参阅韩福东:《中国社科院改革的是是非非》以及《国外的社科研究体系》,北京:《新闻周刊》,2004年4月5日。
学生提问:请丁先生谈谈韩国的大学的情况,讲一讲韩国的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区别。)
丁学良答:韩国的大学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最了解的是美国的大学,其次是英国式的大学。我所知道的是,韩国对考试也很重视,这是出于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韩国大学里面,近亲繁殖很严重(日本的东京大学也是如此);韩国社会跟大学有关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就是社会里具有高等学位的人太多了。
因为韩国的高考很严格,进他们的好大学很难,加上它在历史上又很敬重中国,于是考不上本国好大学的韩国青年,到中国来留学的很多。(我后来在互联网的一个论坛上读到,2003—2004学年期间在将近八万名来华的外国留学生中,一半是来自韩国。)不过听说韩国教育界对中国大学里的腐败现象,包括卖学位,越来越了解,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对中国大学的评价。
学生提问: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办大学?
丁学良答:多元办学,是一种进步。政府的资源有限,民间的资源越来越多。如果阻止建立民办大学,则是我国国民的普遍损失。中国1950年以前也有很多的私立大学,有些办得挺成功。刚才大家提了许多目前大学里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民办大学的路子必须走得更快、更宽广。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政府只要在这个领域里把手放开就行,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推动建立一套独立的、透明的、公正的高等院校评鉴规则。在中国的民办大学里,肯定有相当的一部分就像从前的“皮包公司”一样,是骗人害人的。中国政府千万不要以为对民办大学放开就削弱了政府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职责,而要认识到,政府在这方面只是改变了职责。对高等教育机构——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还是中外合办的——进行专业的、常规的、独立的、公开的评鉴,这是很关键的,没有了这一点,挂着“大学”的招牌糊弄人的事就会层出不穷。所谓“独立的”评鉴,就是说要独立于行政机关。一旦附属于行政机关,出于机关里个人或机关部门的利益关系,肯定就难以保持评鉴的公正性,这个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美国每一个大区域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资格评审机构,在学位授予权等等方面对本地区的高等院校进行常规的查核。
学生提问: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讲的是美国许多所大学,都把自己的教学内容放在网上。而在国内,很多公司、各色人等都在蠢蠢欲动,打算搞远程教育(主要是通过Internet)。请问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有什么区别?
丁学良答: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视教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议论。那时大家看到,学生可以那么近地看到老师,听得也清楚,又方便,于是就有人担心传统教学会很快消失。可是,电视教学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传统的学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当然,传统的学校本身也在变革。所以说,因特网在教学手段和信息传播方面能够跨越更大的距离,增加间接互动的机会,但它不能取代常规的学校。常规的学校除了把课本里的信息传递给学生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互动的群体,在群体里面智力上、观念上、想象力上、情绪上互相影响和刺激等等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可以看看,过去一千年来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及文艺方面的创新,从来不是一颗明星在孤立地发光,而是群星闪耀。一个伟大的天才,如果把他和外界隔开,他很难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强手在一起面对面地讨论、辩论、竞争,才愈加形成强中之强。我相信,Internet只是一个更新更有力的手段,而不可能取代常规的学校。
学生提问: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息息相关的。以前是英国最强,现在是美国,而目前欧盟的GNP已经超过美国,欧洲的走势是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以前我们中国学生大都到美国去留学,这不太符合目前多元化的趋势,那么我想以后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及其他国家的趋势会不会强一些?
丁学良答: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不太同意你的欧洲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说法,事实上欧洲现在有多所一流的大学,剑桥、牛津、伦敦的帝国大学、巴黎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等这些都是一流大学,只不过它们在有些学科上比不上美国最好的大学。这几年来,欧洲的大学,尤其是英国、德国、法国的大学,已经在开始改变它们几百年的传统了。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牛津已经有工商管理学院了,剑桥也在办,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业训练领域。在这方面,让人觉得牛津、剑桥和美国的名牌大学相比相差蛮远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很注重实用的国家。我想,欧盟成立后,全球化的大潮会使欧洲原来那些古老大学的优势得到再生的机会。但是有一点,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很难和美国相比的,就是它的移民政策。相对来讲,美国是一个土地和人口相比资源特别丰富的国家,很多留学生到了那里求学、找工作,容易留下来。(根据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在1989年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九到了1991年仍然留在美国;十年以后,这个比例增长到百分之七十一。对中国内地的留学生,这个比例是百分之九十六。详阅Jeffrey Mervis,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of the Workplace.” Science, May 28, 2004, p.1285.)而在欧洲,这样的机会要小得多。不过我是很赞成刚才这位同学讲的出国留学要多元化,多元化才会把世界各地的好东西传播回来。这方面的困难在于接受国一方的门对中国学生开多大,而不是我们这一方想去多少人。
学生提问:大学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有自由的要求。我想请教一下丁先生,自由的思想对一所大学的价值意义是怎样的?
丁学良答:毫无疑问,大学的精神本来就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学术自由,大学就会徒有虚名、空有外壳。(法国哲学家Jacques Derrida(雅克·德里达)在他于2001年9月中旬的上海之行所作的《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的大学》的学术演讲里,对“大学是应该把自由地探讨真理作为无条件的原则的唯一机构”有热情澎湃的解释。我手头只有一份张宁翻译的节选,无出版细节。)但是,学术自由,包括大学自主,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它更大程度上和很多制度性的东西有关。每一种自由,如果希望它是稳定的、持续的状态,它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是正面的,那么它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不能今天提倡学术自由,明天又不提倡了,或者只允许主流一方批评非主流一方的自由,没有少数派反批评多数派的自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中国正在搞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也是西方国家的学生运动最激进的时候,哈佛大学部分学生闹罢课,并且占领了教学大楼,别的学生也上不成课了。于是校方出面和学生协商,校长请了哈佛大学里最有声望的、深受学生敬重的三位教授——其中有一位是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来和他们沟通。经过一场充满智慧和感情的讨论,占大楼的学生撤了出来,换了一个方式去表达抗议,愿意上课的学生也能继续学业。这个例子给了我一堂关于大学里面自由、宽容、多元和责任的生动教益。(Geriese S. Akerlind and Carole Kayrooz, “Understanding Academic Freedom: The Views of Social Scientist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ol.22, No. 3, 2003,pp.327—344.)
学生提问:我对您所讲的第四部分有点疑问。您强调大国和大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听完论述后,我觉得您并没有把二者的关系讲清楚,即它们何者在前,何者在后。您举了一个例子,说日本的东京大学在走下坡路,那么按照您的思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也要失去大国的地位呢?我的问题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不是对应着一流的大国?
丁学良答:我在讲这一点的时候,之所以在黑板上画了双箭头,就是考虑到可能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双箭头就是表示大学的兴起和大国的兴起是相辅相成的。从我举的例子中间可以看出一点,就是一般来讲,在过去的一千年里,通常一个国家的发展在有了好的起步的时候,它的大学就能很快地在世界上扬名。同时,如果一所大学已经办成样子了,越来越出人才、出学术成果了,它就会以生气勃勃的影响和引导的力量,领着这个国家进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所以说,就一个国家而言,到底是大国的兴起促成了大学的兴起,还是大学的兴起促成了大国的兴起,是一个双向的街道(a twoway street)。相同的道理,大学的衰落也会促成大国的衰落,因为创新的基本源泉之一枯竭了。比如东京大学,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围内,它算不上是一流大学,它只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而目前亚洲其他国家的大学有些正在努力赶上来,东京大学却在原地踏步,一步一步地老化。如果日本想在这一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保持领先大国的地位的话,它就要彻底改革自己的教育制度。近年来,日本国内已经有了这种呼声,特别是那些在美国留学回到日本的,在大声鼓吹改革。
学生提问:我想提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师生的比例,您好像是说比例小一点好一些,但您没有说到底怎么样的比例合适。比如,北大的师生比例本来很小的,但现在教师人员要精简,师生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我想问: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好?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发掘创造性?我看了达尔文的成长过程,发现他在高中的时候功课都很差,后来他父亲花钱让他上了牛津、剑桥,但他总是不成器,直到二十多岁,他才突然爆发出天才。所以我想,有创造性的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往往被看作是坏学生,一旦考不上大学,老师就贬低他。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被扼杀了。
丁学良答: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我不是研究教育学的,所以我没办法给出一个精确的指标,但是我认为这类问题在两端之间取得平衡为好。哪两端呢?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有上面规定的教员指标,超出这个指标怕是不容易。同时我们又知道,一个教授带一两个、两三个学生最好,一定会有充分的时间教好他们。所以,师生比例始终在这两端之间游移,最终定在哪里还取决于全国整个教育市场竞争状况如何。各个大学应该有自己一定的选择权,但学校也不能做得太离谱,不然学生就不愿意来了。道理很简单,家长会说:我花了大笔的学费把孩子送到你这所大学来,但是孩子一年也见不到教授一面。学生教师的比例,在美国的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学里,大约是五比一到八比一,在一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里,是十二比一到十五比一。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天才并不是在最好的大学里培养出来的,这个问题永远存在。不过总的趋势是“漏网之鱼”的概率愈来愈小,因为上大学的机会愈来愈多。以英国为例,在1960年代初期,百分之五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四十年后的今天,百分之三十五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资料引自“Reforming British Universities. The Best Men Won.” The Economist, January 25th 2003, p.14.)如何解决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两个非常关键的要素。第一,少数非常突出的天才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们并不能够由此及彼,否认一流大学、二流大学在培养数量巨大的学生的素质上的必要性。换句话说,一个人、几个人不上大学也能对科学、技术、文化作出突出的贡献,与一个社会在总体上要不要办正规的高等教育,是两个问题。你能不能举出例子,在最近的五十年里,获得过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奖的人当中,有多大比例的,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第二,如果一个社会在大学的校园之内、校园之外,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在不同的教育水平面上,越是发展出给非常规的各类人才以众多选择的灵活教育机制,那么这个社会里的异常类型的人才得到社会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承认的机会就越多,人才资源浪费的总体现象就越少,这个社会就越是发达进步。最可怕的,是一个社会提供给人才发展的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机制,那就糟糕了。比如爱因斯坦,如果用今天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来衡量,那么他连大学的讲师恐怕也当不上。又比如说陈寅恪,假如纯粹拿学位、拿发表的论著数量来作尺度,今天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的机会也不大。但是你要说你是爱因斯坦或者是陈寅恪,你不能仅仅拿你没有名牌大学的高等学位或者你没有很多论著来作证明,假如是那样的话,遍地都有成千上万的爱先生和陈先生。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社会里面,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提供的机会越是多样化,而不只是一条道路,那么各式各样的人才被埋没的可能性就越小。学生提问:我想问的是,中国在多长时间内会有多少所大学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您是否研究了这个问题?
丁学良答: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类似于市场预测的问题。我想,只要我们中国的“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还比较快的速度,如果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多方面地开放,在这三个大的正面环境因素的刺激下,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步伐将越来越大——客观上一定会是这样。只要中国的教育改革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在很多方面获得一种制度化的保障的话,我想,也许在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有非常好的大学出现,能近似于美国前五十名的公立大学的水准。因为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决不是三年五年能完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有两所大学从几乎是默默无闻的状况,发展成为大家公认的、一流的研究型公立大学,一所是加州的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另一所是得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它们在全美国进不了前十五名,但可以排在第二十五到第五十名。
主持人张维迎教授:
由于时间关系,提问题到此为止。
主持人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先请几位评论人作评论或者提出问题,然后大家展开讨论。
评论人黄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非常荣幸作为评论人,提几个问题,想听一下丁博士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1950年代,冯友兰教授的一篇文章《大学是培养什么人的》,提出大学是要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专业化分工要求人才的专业化,但大学“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理念与这一点之间有一些矛盾,请问丁博士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丁学良答: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来看,以美国最好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为例,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一般来说本科生一年级不选专业,到二、三年级才选,选了以后还允许改。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三年级以前都不让你选专业。这个趋势就是反映了“专业教育”底下的“通识教育”所占的比例在整个高等教育中逐渐上升。当今世界实在变得太快,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知道要变换多少次工作,过早地或者过窄地专业化,会限制一个青年人今后的适应能力。从二十世纪末以降,专业教育更多的是在研究生阶段,而不是在本科生阶段落实,这是与两个基本趋势相适应的——社会变化加速,同时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对中国的大学而言,在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之前,首先应该把大学里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进行一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更新。现在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无用之物,还没有出校门就过期作废了。
黄平:第二个问题是:一流大学与别的高等院校的关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关系如何看待?社会如何在二者之间处理这个关系?剩下的人如何处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分配?
丁学良答: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当然不能仅仅只办好一两所名牌大学,对其他的院校不顾不管。不过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沿海少数几个地区、几个产业着重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我们就不会知道国内产品和人家产品的差距,就没有更高的参照点和刺激源泉,从而也不能给内地更多的企业、行业提供学习和追赶的榜样。所以从发展的远景来看,中国首先应该办好一两所大学,产生领头效应,营造竞争氛围,提供刺激源泉。从最终格局来看,数量众多的高等院校都会受益。以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为例,它既有少数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也有一大批专门的理工大学(polytechnics)、职业学院、技工学校;德国的教育体系对它的工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等教育体系比这又前进了一大步,州政府资助的公立高等院校分层分类,既有一两所世界级的名校,也有全国名列前茅的四五所优秀大学,还有训练大批学生的普通院校(约有三十所)。参阅郑国汉、雷鼎鸣:《加州高等教育体制对香港的启示》,香港:《信报》,2002年7月1日。)
评论人郑也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谈谈感受:自己糊涂了二十年,先后在两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里呆着,最终幸运的是发现大学才是自己应然之所在。曼海姆(Karl Mannheim)说过,传统知识分子相信某种教义,企图创造某种教义,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处于悬置状态,怀疑一切,质问一切。除了现代知识分子,一般只有处于青春期的少年才会有这种心理状态,而现代知识分子则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状态,因此有时就被视为一种怪物而存在。我只有在从研究所、院进入大学以后,在学生之中,我才在心灵和心理上感到安全了。
提一个问题:大学中有两种角色:教授和管理者。二者合一或者分开,利弊何在?
丁学良答: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从制度和个人层面讲都是如此。19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大多数一流大学的校长通常都具有两个素质:第一,校长本人是在某一学科具有突出成就的教授。第二,其人格具有亲和力,能够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具有管理能力和团队精神。到了今天,另一种能力日益重要,那就是经济的能力,即能够募捐到足够的钱来发展大学,以丰富的资源来吸引优秀的教授和学生。这在今后会越来越重要。当然一般而言,在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起码不能是学术上的平庸之辈,必须具有高的社会威望,代表着超越特殊利益的公共道德力量。
评论人杨东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丁教授是海外归来的学者,可以戏称为“海归(海龟)”。你的这个报告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人才竞争,是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面临的问题。办好中国大学缺些什么?现在只知道缺钱,给清华一拨就是十八个亿的人民币。但是还缺一些东西,就是理念、制度。
因此,在这里向丁教授提个问题:对大学而言,除了你已经谈到的标准以外,共有的准则还有哪些?
丁学良答:中国的大学无疑是缺钱的,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办好大学、发展一流高等学府,钱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同类型的大学会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例如:选教员、选校长、选学生、大学预算、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等等。在美国,不同大学之间、不同专业之间教师的收入很不一样,但标准本身必须要趋向公正和透明。同样,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拨款会有多有少,但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标准。现在国内管大学的思路与管国有企业的思路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这样的可能后果是:钱拨得多的,浪费大;钱拨得少的,怨言大。
主持人周孝正:听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找钱锺书先生谈“东西文化比较”, 钱锺书说:拿刀子来,谁跟我谈“文化比较”,我拿刀子扎他。意思是说要了解和把握不同的文化是不容易的,没有深入的研究,空谈尚且不可,何况制度建设!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涉及到大学制度作为制度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比较研究。丁学良博士所作的八十分钟的演讲,是他二十年里在世界好几个地区,在好几所一流大学里面学习、工作、研究的积累。我们只有在广泛地了解今天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构架、规制、精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改进我们的大学制度,使我们的国家的发展有所支撑。下面请听众提问。
听众: 大学自治是否是衡量一流大学的标准之一?
丁学良答: 这关系到大学的法律地位,它本身不是一条标准,但它是所有其他标准的基础保障。在不同的国家里,不同类型的大学的法人地位大概有三种:公立大学——款项来自纳税人、政府财政,所以校董事会中有政府的官员,但比例低,一般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大多数校董是社会贤达。私立大学——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之外,是否会邀请个别的政府官员加入校董会,这由校方决定。政府对学校用土地等等会有一些优惠政策,也会在研究经费方面对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教员,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开竞争方法。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是公私协办大学,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原来是私立的,后来在经费上日益仰赖政府的资助。但无论是哪种类型,大学的运作是独立自主的,包括它的招聘教员、招生、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开办一所大学的法律起步和制度保障,是拟定及通过它的《大学宪章》。作为该大学的管理原则,大学宪章由大学筹备机构反复研究讨论、律师协助拟定,然后正式册立,它乃是大学如何运作的基本法。宪章是公开的,违反这个法律,不管是来自学生、教授、校方行政部门、还是外界的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均可能受到起诉。大学宪章制度是对任何一种强力的任意干涉、操纵的预防和抵制。
听众:关于大学自治,你认为国内与国外的差距何在?
丁学良答: 我对国内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太了解,但这几年我观察到,在我提到的最重要的那几点上,国内还需要切实的改革。总的来讲,大学自主运作就像企业自主经营一样,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周孝正:制度是一种文明。但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如果制度中本身包含了一种检验、评鉴、纠错的机制,结果就会好一些。
听众:在中国的高考中,各地学生录取分数线不一样。对这种差异,你如何看?在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
丁学良答:美国的州立大学对本州学生有一些照顾,主要是在学费上,因为它们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本州居民交的税。在进校的标准上,有些私立大学对本校创始人的后代有一些优惠。你提到的问题,关键是看中国的大学有没有合法、合理的根据,对特定地区的考生应用不一样的录取分数标准。如果不一样,就应该公开不一样的理由,例如说明我们大学的资金中有多少是由北京纳税人交的,所以北京考生才能在高考录取中享受相应的优惠。大学招生至少应该在法律的层面上体现出公平;在实际操作中,美国也有不平等的情况,例如种族歧视问题。
听众:大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应该有禁区,专业的设置应该由学校来决定,还是应该由教育部来批准,研究领域由谁决定?
丁学良答:美国是一个分权的国家,联邦教育部根本管不到公立、私立大学的课程设置,也许只有少数几所军事学院、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学院除外。大学制定课程表和教学大纲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就业市场的反馈,即你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尽快地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反过来影响到招生的生源。二是研究的领域要尽可能求新、求广,例如耶鲁大学原来以人文和法律见长,但现在也开始注重理工科。麻省理工学院最早只有理工学科,因此历史上有几次差一点被临近的哈佛大学吞并,于是就逐步开设政治、经济、管理、语言、哲学等学科,现在它的这些科目也都跻身于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应该顺应乃至领导潮流,而不是抗拒潮流。但是美国的大学一般不会因为专业设置变了、学科结构变了而改校名。校名是学校的无形资产,它联结着一个学校已经毕业了的一代一代的学生,又是一个学校传统的标记。中国的学校改名字太频繁,一点都不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历史(你只要翻阅一下这类资料书,就不会不感叹中国高等院校是多么的不尊重自己的名称传统!季啸风、王显明、徐敦潢主编:《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对校友的召唤力很淡薄。
听众:大学的人文价值和大学以技术科学为核心,二者的关系如何?
丁学良答: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办现代大学的动机首先是技术、科学,这种取向是有限合理的。需要告诫的是,任何技术仅仅是一种工具、手段,如何使它们得到最优化的使用,是靠人文、社会、法律方面来决定的。忘记这些软力量要素,仅仅只以技术为目标,后果只能是培养出来一流的工程师,二流的科学家,三流的公民,四流的管理者。
听众:国内二三流大学之间的横向整合是否必要?二流大学如何吸引一流的学者来工作?
丁学良答:由于当年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存在大量的高等专科学校,虽然很多名字叫“大学”,将它们兼并是必要的。但只运用行政手段来搞合并是不合适的,要参照西方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的架构,要尊重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要尊重专家们的判断。搞得好,合并后的大学是事半功倍;相反,蛮干式的合并,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过不了几年又得重组。这就像咱们很多城市里面的市政建设,刚刚铺好新路面的地方,过几天又得挖开,因为下面的管道在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周到。
最后我想再一次强调一下,中国的大学发展,像世界上所有机构的发展一样,探讨的都是在给定的一组限制条件之下,怎么样找到最优化的方式,达到尽可能好的综合效益(大学的综合效益当然有它的特殊之处),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各级政府现在对一些高校进行重点拨款,是非常必要的,但远非是充分的。要想使纳税人的钱、政府拨的这些专门款项能够产生更好的综合效益,最关键的就是要把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弄清楚。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大学又有自己的制度;不同水平的大学、不同功能的大学,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性架构。但是,只要是正规的大学,就一定会有制度的共同性。比如说,一所大学有了一笔钱怎么用,透明度是非常关键的。在国外,公立大学不用讲,就是私立大学,每年都必须把过去一年的所有预算方面的账,向全校成员乃至历届校友交代得一清二楚。
鉴于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要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全职成员,鉴于二十一世纪是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那就应该尽快地使中国大学的制度跟上这个时代。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很充分的讨论,没有社会的基本公识,没有合乎科学的制度建设,你对大学拨钱越多,浪费就越大。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