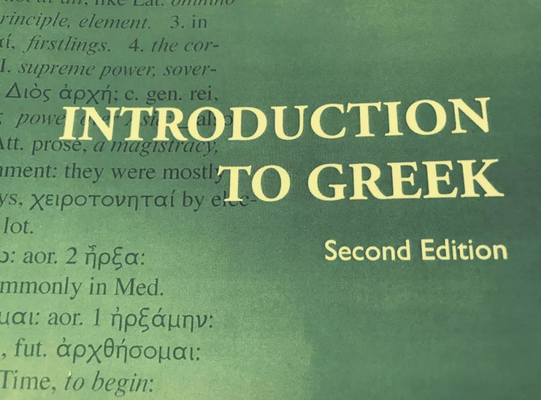
为什么要学古希腊语呢?
这问题,绝不只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的朋友们会问我,我也常常在与自己的对谈中忽而将它抛掷出来。
最简单、粗暴的回答当然是:我的专业是古典研究,想要毕业的话需要修四门古典语言。我喜欢希腊远胜罗马,自然就会抛弃拉丁文而投入古希腊语的怀抱了。
但是不该仅仅是这样的。我跟自己说:“你别躲,别拿专业要求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自己,弄得好像是这个世界要求你学古希腊语——显然其实你是自找的。那么,你总该有点什么更私人的原因吧。”
好吧。我得承认。我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妄念的:我非常、非常希望在这短得犹如叹息般的生命中,能有缘分得见我深爱的那些作品本来的面目:荷马的原文,希罗多德的原文,柏拉图的原文……这种愿望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它太遥远了,遥远得不真实。我现如今,毕竟还只能守着那点可怜的词汇量,依稀辨认出一些“诗人写作,而法官审判”这样的小句子罢了。
但是我确实真诚又小心翼翼地,怀抱着对未来好巨大的希望。
那么再在这之下呢?我还是不死心地问自己。还有什么没有说出来的原因吗?
是有的。我不去讲,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将它们付之语言。那都是些细碎又模糊、甚至于难以捉摸的情绪。
我在这个时代中时常感到紧张。当代生活毕竟是太令人心惊了。于是常常在不知觉中想要逃回那个浩如烟海的古典世界去——那是我的海市蜃楼。

现在教我希腊语的教授是Professor Maurizio,也正是她在最开始的时候,伸出手,把我从一片迷惘中,拉到古典学的世界中去。
我现在回想一年前,大学二年级第一次上她的课时候的事,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其实也才过去十二个月,一轮的春夏秋冬罢了。
那会儿我已经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学不了心理。但是大略是因为种种对于打破安稳生活的恐惧和焦虑吧,虽说已经不舒服极了,仍是停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一下,虚张声势挂着“心理专业”的门面,欲盖弥彰地掩饰着一派平静下渐次脱轨、分崩离析的大学生活。
我当时以为,我或许就会忍耐着,把最后两节课修完,然后在研究生的时候转去学别的专业。
但也就是在那个特别艰难的学期,我上了一节Professor Maurizio教的古希腊艺术。Professor Maurizio和其他的古典系教授一点也不一样——他们都严肃极了,往讲台上一站,自己就堪比一尊古希腊雕塑,说是讲课,倒更像是布道传经。
而Professor Maurizio则是个特别可爱的老奶奶,说起话来语调像是贴着丘陵飞翔,满是笑意和雀跃,有时候甚至带着点儿咋咋呼呼的孩子气。第一节课发下来大纲,就神秘兮兮地跟我们说:“翻到第二页捂眼睛哦!有裸男照片!”我翻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排古希腊雕塑整整齐齐印在中间。不由得扶额,内心默念:“您这样顽皮真不怕祖宗们棺材板按不住吗?”
她在那节课上讲授的内容,如今于我都有些模糊了,但是那些她在课上放的古希腊雕像群魔乱舞的鬼畜动画、那些两倍速播放古希腊语朗诵荷马史诗的奇异音频,仍然历历在目……
那学期某一天的下午,我去办公室找Professor Maurizio谈论文的选题。后来闲聊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太有意思了,我好喜欢。
我说这话,倒绝不是敷衍作态,但也的确有那么一两分客气的社交意味。谁知道Professor Maurizio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当即拉住我的手:“是吧是吧!有意思吧!你现在发现一点儿也不晚啊。你看,你这个心理,就不要学了吧。你来我们古典和中世纪研究专业吧,我给你找找……啊,这个毕业要求,也就只有十来节课,你才大二,啊虽然快结束了,但也是大二。你还有两年,在上个五六七八节课,就可以了!哦对,要上四节古希腊语,啊,你眼睛不要瞪得那么大,也没有很难,学一学就会了,我给你找找啊……那个古希腊语,我有个大词典……”
紧接着她就在我还一脸懵的时候,起身从架子顶端搬下来一本能砸死我的大书:“你看,这个就是古希腊语。啊,我知道看起来很难,但是你也学过数学吧,alpha、beta、gamma你也都听说过不是吗?你看,你这一下子就已经会了三个字母了!你学了这些,你就可以读荷马史诗了,《伊利亚特》的原文哦,《奥德赛》的原文哦。”
也不知道是她游说的技巧太好,还是我那段时间生病烧坏脑子了,这么一段怎么听怎么像传销窝点宣传纲领的演讲,居然听得我晕头转向、热血沸腾,恨不得当时就跑到楼上跟心理教授说我不干了。

我当然没有真的直接去把心理专业销了,在头脑发热的时候报个古典——这听上去太像冲动购物了。
不过Professor Maurizio说得那些话,却真的像颗种子一样,留在了我心里。
我想着这大概就是当局者迷。人对自己的生活其实蛮缺乏想象力的,来来回回总陷在自我的困境中。明明那么多扇不同的门就在眼前,但又好像盲了一样。此时有人过来提一句,可不就如同醍醐灌顶吗?
自己瞻前顾后瞎琢磨了两个多月后,我又一次去找Professor Maurizio。那个时候学期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我去找她,也不再是为了上课的事——我去跟她说,您之前忽悠我来古典系,我现在好像有点儿动心。
那次的谈话,一改平日嘻嘻哈哈的风格,而是又严肃又沉静。Professor Maurizio跟我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刚进普林斯顿的时候,是学数学的。当时想要修拉丁文,结果那节课跟我的一节数学课冲突,我又不想等,干脆报了节古希腊语,琢磨着下学期再去学拉丁语。谁想到,一下子就爱上了,不但没回去学拉丁语,甚至还离开了数学专业,改学了古典,一路读到博士,就来这里教你们了。
下决心做这样大的改变是很难的,就像是要你跳火车,要你离开几乎成为惯性的熟悉而稳定的生活。但是如果火车去往的方向你不喜欢,那为什么要继续停留呢?”

我好喜欢她关于“跳火车”的比喻。
这学期开学,第一天上课前,我去办公室找她。
我说,您还记得“跳火车”那个比喻吗?您当时跳下来,所以会教我们;我现在跳下来,又来上您的课了。

我真喜欢古希腊语。
那门语言复杂极了,但也同时,美得令人心惊。
比方说,古希腊语中所有的人称、关系、主格宾格、单数复数、阴性阳性中性,都是通过变化词语的后缀来表现的。这造成的大不幸是,学一个单词,实际上是学一个大表格,里面有它的无数个亲戚几十种变位。但是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简洁,洋溢着属于古典世界的,内敛而庄重的美。
又比方说,因为后缀把人称和关系表达的很清晰,于是不需要特别依靠词语的顺序表达意思。一个句子中,词语的位置十分灵活,实际上除了少数的固定组合,许多词都可前可后。翻译句子,就像是在做小拼图。
想要表达,“我在房子里给朋友写信”,可以写成
我写 信 在房子里 给朋友
信 我写 给朋友 在房子里
在房子里 给朋友 我写 信
……
那种思维方式有趣极了。像是意识流。空气中漂浮着朋友、信、房子这些温暖的词汇,我像是又回到一周岁的时候,懵懵懂懂,坐在桌子上抓周。
多自由的语言。恰恰因为规矩奇多,所以自由的语言。

2019年2月9日,距离我开始学古希腊语,整整是一个月。也正是在这一天中,第一次读完了一个用这个古老语言写成的完整段落。
说是读完,其实十分勉强,顶多是磕磕绊绊地顺下来。
面对着一门新的语言,犹如努力张大眼睛望外面的世界,却总隔着一层缀满了雨水的毛玻璃。那些陌生的、不属于我的词语在周身漂浮。词语连成细麻绳似的句子,句子又织成网。再如何严阵以待,俯仰四顾之间也难免陷入巨大的迷惘和慌乱,好像在满是浮冰的海域上寒夜行船。
但也不全是陌生。
啃那个段落的时候,我起初只顾得上一边检索着脑中少得可怜的古希腊语词汇库,一边试图辨认时态和句子结构,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应该是Croesus,唔,还有Cyrus,那应该是讲Lydia的事情……行军到波斯……战争没有决出胜负?Cyrus,在援军……是援军还是军队……我的词典呢,啊,援军,到来之前,列阵迎敌……Cyrus用……这个词是骆驼吗?代替了……什么呢……代替了马!因为马害怕骆驼……敌人逃跑……
马,骆驼,居鲁士……我的天呐,这是希罗多德啊,这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啊!!!”
仿佛眼前厚重的帷幔骤然掀开,倾斜下来的天光使我感到晕眩。
那一瞬间,我几乎从自习室角落的小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神经病人一样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念叨,“天呐,刚才那段,那段是希罗多德啊,我读到希罗多德的原文了,啊!”
我没办法去形容那种让人指尖都要颤抖的激烈情绪。在一个十分平常甚至于索然无味的午后,我就这么毫无准备地一头撞进了希罗多德的文字里。我那么喜欢的希罗多德,被罗马人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公元五世纪中,从埃及游荡到黑海,又在雅典温柔的光辉中写出九卷《历史》的希罗多德。
不再是小时候懵懂中读到的中文译本,也不再是这两年来一页一页翻过去的现代英语,是古希腊语,是最原本的、两千五百年前他写作时使用的古希腊语。
我多喜欢《历史》那本书啊。
于是读中文的译本,读英文的译本,听教授讲其中的故事,和朋友聊天时谈其中的词句。我隔着各式各样的、从不知何处垂下的重重帘幕,凝望它的幻影好多年,而今,终于在电光火石之间,侥幸触碰到了一点真实。
真正的希罗多德。
我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友邻说,
“我今天见了好多人,我和他们一个人一个人认真地说,我爱古英语,我想要永远和古英语在一起。”
我看到这句话,心口如同被敲了一下,不由得笑起来: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明白你正体验着的炽烈的快乐。
我去翻了一下她的微博,发现她常常会发一些古英语的小句子,督促自己背诵。不过有一天她忽然说:
“其实根本不用刻意背,因为我一定会翻来覆去读到停不下来,直到它和我长在一起为止。”
这令我想起赫拉巴尔写过的那种感觉:“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直到它和我长在一起为止。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