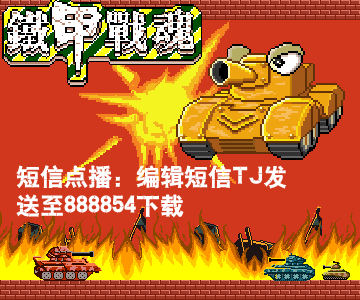这才是我们全家的心愿,是我出国的真正理由。
2003年4月底,我胸怀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背负着爹妈的寄托和不舍,捂着双层大口罩,推着笨重的行李车,穿过现代化的首都机场,告别了被SARS病毒威胁着北京,犹豫不决地走出母亲的“翅膀”,一步一步地朝着海关,朝着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新的生活走去。
起飞——在撕心裂肺的离别痛苦中,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
爸爸妈妈和奶奶,你们对我的句句叮嘱我都记在心中了,它将陪伴我度过留学的日子。奶奶,您一个人去湖边遛弯,千万离水边远着点儿;爸爸,您也要注意身体,少抽点儿烟吧;妈妈,你要多运动运动,我希望你的肚子再小些……
由于SARS的肆虐,北京机场壁垒森严,人人戴着大口罩。除了一些必须出国的留学生以外,几乎无人在此时出行,北京国际机场空荡荡的大厅里只有即将远征孩子和为他们送行的家长。
送行的妈妈们为了尽可能地多嘱咐几句,差不多都忘我地摘下了口罩。是啊,这些孩子在母亲舒适翅膀下呆的时间太长了,现在突然要远走高飞,去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当妈的有多少牵挂和不安啊。
还没飞走呢,我就目睹了人间最伟大的爱——母爱。
看吧,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推着行李车跑回剪票口,喊着:“妈,超重了!人家让交3000元钱。”他妈妈闻声即动,立刻掏腰包;
瞧,一个学生妈妈拿着一张表格在填,边写边叨唠:“连个表都填不好,看你出去再靠谁?”她的孩子在一边呆呆地站着;
再看,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哇哇的哭着,说什么也不想走了,她的妈妈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痛哭,人们在劝这娘俩……
我呢,也没让我妈省心。
在托运行李处,我的箱子里被检查出有“不明物体”,打开箱子发现是一小包金属礼品在捣乱。经过检查,终于同意过关了,可是,我老爸经过科学的计算,反复的实验,精心利用每一公分空间才装好的行李箱,我是没有本事把它关上了。
却怎么也关不上了。我只好把东西掏出来重新装箱,越着急越使不上劲儿,我满身是汗。
“亭亭,怎么这么慢呀,行李还没通过?你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太让我又惊又喜了,老妈从哪冒出来的?在关键时刻,妈妈说服了机场工作人员,象“神仙”一样来到我身边。
“怎么回事?来不及了,快点吧!你起来,我来!”妈妈一边数落着我,一边飞快地忙活起来。
“你这臭孩子,真是笨死了,怎么能叫我放心呢!”我站在一旁,很塌实地看着妈妈帮我收拾乱摊子。
“去往新加坡的A51次航班就要起飞了。”机场的广播员平静地用中文和英文播报了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
没有依依不舍,没有再三叮嘱,甚至连道别都来不及了,妈妈把我推进安检口,我背着书包向前直奔。
“别磕着电脑!”
“别掉了东西!”
“别进错了侯机厅!”
“别慌!”
“……”
妈妈一连串的“别”字在我脑后追着我,我终于赶上了飞机。
飞机冲上云霄,往机窗外看去,一片屋顶的北京城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我突然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我想,地面的那些象积木大小的房子中的某一所就是我的奶奶家——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此时此刻,奶奶说不定正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呢,我的鼻子酸酸的,真没出息,还没出国门就想家了。
我尤其想奶奶。
奶奶是最疼我的,因为是她把我带大的,所以最舍不得我走。我小时候父母去国外留学,奶奶和我经常站在院子里,仰天望着云端里偶尔飞过的飞机,眼巴巴地盼着爸爸妈妈就坐在里面,马上回到家来。
可是今天,又轮到我要远走高飞,奶奶她怎么能受得了?
自从我开始办理手续,奶奶感觉到“留学”真的要把她的宝贝孙女带到遥远的地方时,流了不知道多少眼泪。
我最亲爱的奶奶,试图用各种方法使我留下——她去家附近的“八一湖”畔挖野菜,用她那因风湿而变形的大骨节手,给我做我爱吃的野菜包子;她用不吃不喝向我爸我妈抗议,让他们阻止我出国;她还到处打听“小道消息”——谁家的孩子在国外多么受苦受难啦、受不了跑回来啦;谁家的孩子在北京某大公司工作,可有出息啦……
可惜,我软硬不吃,一心想出国转转。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