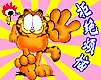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迷失的律师(4)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8 13:30 新浪教育 | |
|
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转变 我不想直接研究这些问题,先暂时不去对政治判断的本质做进一步的探讨,转向个人思考领域。所谓个人思考,我是指一个人想确定自己的利益并决 当我把辩论的重点从政治深思熟虑转向个人思考时,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遵循了苏格拉底在《共和国》中所采取的相反的策略。柏拉图,《共和国》,368c—369b。苏格拉底与他的对话者从探讨作为个人品德的正义——拥有该品德说明一个人具有正义精神——的本质开始。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品德,苏格拉底建议,他与对话者首先大规模地在政治领域探讨正义的含义,他说,在这一领域人们更容易认清正义的本质。苏格拉底是根据以下的理由为他在争论中的迂回战术辩护的,即社会正义(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灵魂正义)在结构上相似,因此,一个人可以用一种方法来理解另一种。我的建议是,我们寻求政治家才能,即政治深思熟虑的杰出才能的含义,首先必须问一下个人思考的情况,我相信,我们更容易了解个人的基本情况。与苏格拉底试图用相似的政治品德来描绘个人品德相反,我建议,通过首先描绘政治家的个人品德来解释其政治品德。 当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我的方法与苏格拉底的方法相类似,因为正如他假定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可以类比一样,我也假定个人思考的智慧可以与政治领域的政治家才能作类比。我认为,这两种才能在结构上相似,理解前者(个人品德)有助于我们理解后者(公共品德)。我要声明的是,这两种品德并非同一种品德——如果相同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同时二者兼有。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些人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很多的聪明才智,但在个人思考中表现出很少的智慧,甚至没有智慧,另一些人恰恰相反。这种明显的有趣的不一致与主张个人判断和政治判断是类似的是一致的,因为类似并非完全一致,而是一种相似关系。接下来的争论是假设这种相似存在。它也试图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这种类似的本质,因而强化了它本身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 那么,在个人思考领域,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思考这些问题呢?像政治问题一样,许多个人问题仅仅是关于手段的争论——确定如何用我们掌握的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多的回报。例如,我也许决定存一笔养老金。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在我能利用的各种投资策略中,哪一种使一定量的储蓄可能产生最大的养老的收益呢?假设个人选择只带来手段的问题,那它可以通过计算来解决,对这些问题思考得好的人一定是善于计算的人。 当然,个人领域如同政治领域一样,手段问题也经常涉及到目的。因此,在考虑如何为我的养老存钱时,我不得不思考我未来的未知的利益是否与我目前的现实利益同样重要。此外,我要问一下利用养老金来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容易导致对我的整个人生重新审视的问题。但是,只要我认为两种相互冲突的个人目标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那么即使我为了它们本身各自利益而对两者都予以重视——尽管没有一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手段——我会把二者之间的冲突看成是与仅仅靠计算就能决定的最佳解决方法的一种权衡。这种方法就好像我看待目前消费利益(储蓄计划使这一利益受到影响)与未来收入中的具有竞争性的利益(这是这一储蓄计划想要获得的目标)的冲突一样。 然而,一些个人决定为我提供了在不具有可比性的目标之间所进行选择——两种目标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二者的冲突看作是与定量的解决方案相权衡的问题,这似乎没有意义。当然,即使在这里,时机与心情等因素使一种选择比另外的选择更加合理。前面我已举了一些例子。但是在个人领域,这些也并不总是带有结论性的因素,这或者是因为它们与所说的选择无关,或者他们本身是这种选择带来的窘境的一部分,所以不能作为中立的解决方法。 无论它们多么使人恼火,并非所有的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都同样地重要。事实上,许多这样的窘境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例如,我暑假是去山里还是去海滩?我对每一种方式所提供的乐趣思考得越多,这两种方式的差异就越明显,在我看来,由于这二者代表着相同的基本乐趣,尽管形式不同,因此,坚持选择一种能给我带来更多快乐的做法是愚蠢的。今年以这种方式过暑假,明年以另一种方式过暑假(我们假设这样),这样比颠倒次序过暑假不会产生更多的意义。就我其他的利益、价值和行为来说,每一个假期与其他的假期一样都或好或坏地适合于它们。而且,虽然我作出选择缺乏理性基础,我不必对此过于忐忑不安。因为它毕竟不涉及到我的真正的深层次的利益,除了几点之外,它不值得更多地操心。也许我应该通过抛硬币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也许是完全实用的做法。 然而,有一些同样缺乏根据的个人选择却要严肃得多。我应该结婚吗?我应该离婚吗?我和配偶应该有孩子吗?我应该放弃职业在家里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吗?我应该继续我现在从事的职业还是放弃它从事另外的职业?我应该从事乐器学习还是从事需要几年努力学习才能掌握的外语呢?我应该参加精神分析吗?我应该把我的时间和金钱——也许整个生命——献给政治事业或是与朋友和家庭一起分享呢?我应该与父母呆在一起还是远离他们?我应该帮助我年迈的父亲实现其死的愿望吗?这些是典型的具有很强的个人意义的问题,对它们作出决定通常缺乏合乎理性的基础。他们通常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计算方案,选择时机经常与此无关,问我作出的不同的选择如何适应我的后半生往往是无用的。因为这些决定本身对我的整个一生往往有着巨大的改造作用,以至于不能把大量的未涉及到的利益和价值作为比较我面对的选择是否和谐和适合的中立的基础。 自然,在得出这些就是结论之前,问一下我所面临的窘境是否可以通过某种理智的方式解决是切合实际的。例如,一个问题不管它起初的表现形式如何,可能最后都有一个计算的解决方法,或者根据时机和心情加以确定;或者它也许可以分成若干个较小的问题,至少很容易论述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把没有合理答案的问题的范围缩小在最大的可能的范围内总是有意义的。然而,这样的问题肯定会继续存在,没有人在其一生中能够完全避免这些问题。 这样的选择与个人身份问题——作为个体的我们是谁,希望是谁——密切相关。这些选择哪一种是因人而异,然而我上面提到的只是一般的例子。这种选择对我们非常重要。它们是对我们一生具有深远意义的身份界定的选择,虽然我们不是每天都面对它们,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却不因其出现的频率和数目的不多而降低。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与那些不断迫使所有的政治共同体正视其身份问题的根本决定相类似。与政治选择一样,这些确定身份的个人选择也可能是最缺乏根据的,因为它们使人对一个人的最深层次的信仰产生疑问——正是这种信仰可能为评价这种选择所呈现的不同方法提供一个共同基础(根据它们的用途、时机或者心情)。总之,我现在所讨论的个人选择正是我对政治家才能的解释中出现的政治困境的对应物。苏格拉底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带到这上面来,我们必须试图加以理解这些内容。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为自己创业》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