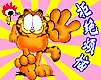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迷失的律师(8)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8 13:30 新浪教育 | |
|
政治博爱 政治博爱的状态是指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尽管观点的不同使他们在关于共同体的目的以及身份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同情的纽带把他们联在一起。这种状态的 一方面,政治博爱不要与大多数紧密团结的人类团体都具有的特征,即情感和信仰的统一相混淆(例如,那些通过某种家庭和宗教而形成的团体)。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完全可能像单独的个人一样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事业的价值和目标的看法是一致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团体拥有其他组织所难以比拟的凝聚力。政治博爱依赖的同情态度并不要求一个团体的成员的关系如此紧密、意见如此地相互一致。事实上,该共同体存在的同时,其成员就认识到在共同体的目标上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也承认这种分歧可能永远无法消除。虽然,有人说只有在一个团体的成员通过同情的相互了解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才有政治博爱这种状态,因此,它所需要的同情必然没有人类的联合最完美的形式所依赖的态度和感情的统一那么完整。 另一方面,政治博爱也必须与现在通常理解的一般的容忍区别开来。容忍是不加以干涉的品德。容忍的人认为干涉别人在法律上或者习惯上受保护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信念以及基于该信念的行为,是以对一个人容忍地允许的行为不同情为前提的。事实上,正如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特别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对别人的事业不但没有同情,而且对它们充满怨恨和厌恶时,容忍的本质及其对容忍的需要才最清楚。许多自由作家指出只有当一个人对正在忍受的事情感到厌恶时,容忍才有必要。约瑟夫·里兹(Joseph Raz)在其重要的著作《自由的道德》(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401—407页中给容忍一个也许是当代最有说服力和最精致的阐述。里兹写道:“容忍意味着一个人以厌恶的方式抑制迫害、折磨、伤害或者反抗的倾向”(第401页)。因此“只有在一个人如果不想这样做时才会容忍”(第402页)。当一个团体的成员在重要性政治性议题上出现分歧,对彼此的观点不能产生任何同情的时候,该团体只有采取容忍这一必不可少的消极的原则才能继续生存。但是,政治博爱的状态在其存在的领域,包含的不止这些。政治博爱当然暗含着互不干涉,与任何容忍的体制一样,但是除此之外,它也包含着愿意接受别人的观点。即使一个人拒绝接受这些观点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他也愿意把别人的价值看作是可能最好的而作出积极的努力,就好像是在维护自己主张的价值一样。容忍本身不需要作出这种努力。因此,与一些团体所显示的更完善的联合形式相比,政治博爱所要求的同情是比较微弱的,如果说它能与这些团体排斥的差异共处的话,它也超出了容忍原则所要求的任何内容,这一原则的最大的要求有时在于它根本不需要同情,而只有冷漠甚至厌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博爱可以贴切地被描绘成是在两个极端状态中的中间状态。 政治博爱一旦消失,共同体的成员可能更难理解他们的对手所关心之事的重点及意义,也更难理解对他们而言政治失败意味着什么。他们更可能不在乎怨恨的重要性,不愿付出努力通过自己的调和行动去避免它。赢者幸灾乐祸,输者含怒不语,嫉妒对手的好运。失败的一方感到受到伤害的不是他们实际失败,而是他们重要的主张受到了无情的对待,他们将时刻关注时来运转的机会,对他们的对手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有政治博爱的共同体内,虽然激烈的冲突不可避免或者会出现几个选项中的关键性的选择被耽搁的情况,然而彼此之间从此形成嫉妒和怨恨的可能性却很小。失败者因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宽宏大量的对待而减轻了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痛苦,胜利者则愿意作出真实的象征性的让步以保持良好的气氛,尽管严格说来这种让步是不必要的。在这方面,具有政治博爱的共同体与缺少政治博爱的共同体有着重要的不同,不管他们所宣称的价值和目的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如何的相似。 政治博爱的价值(一种团体的状态)因此可以比做个人正直的价值(一种个人灵魂的状态)。个人正直不是没有内心的冲突,也不是柏拉图在《共和国》中所想象的从高到低的和谐排列。它是由以下因素产生的完整状态:一个人灵魂的不同部分,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当一个人现在的情感与他过去的情感不相冲突,或者处于压抑与报复的更加微妙的竞争中,尽管灵魂的各个部分存在着使他们分裂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正直是一种善,因为它以一般复合的灵魂所能希望的惟一方式使灵魂成一个整体,与懊悔的离心分化做斗争,缺乏一定程度的心灵和谐,这种和谐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会仍然真诚地追求的。 政治博爱是一种与之类似的善。除了最简单的共同体外,在所有的共同体内,关于其目的和抱负各成员之间的意见总会有分歧,如何解决这些分歧对于该共同体的身份常常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分歧使共同体内部的关系紧张。像一个人灵魂中的强烈冲突一样,这些分歧使共同体趋于分裂,破坏共同体的统一。通过在成员之间建立相互同情的纽带——愿意对别人的利益和关心之事表示同情的基础上的纽带——政治博爱有助于抵消在确定共同体身份的时候破坏性力量。因此,它起着保护共同体不至于分裂的作用,就像个人正是通过类似于自我调节的形式维护个人的灵魂一样。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基伦理学》,1167a22—1167b16,1161a10—1161b11;《政治学》,1262b5—25,1295b23—27。见安索尼·克罗曼(Anthouy Kronman),“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博爱思想”,《美国法理学杂志》,24(1979):114—138页。 当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一系列非常完善的信仰,破坏性的意见分歧永远不会出现。或者他们可以因物质上的相互依赖系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依赖是如此的广泛和强烈以至不管政治分歧是多么深刻都可以被安全地忽略。但是这些情况很少出现。在大多数共同体内,政治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它至少可能不时地考验着即使是最牢固的物质联系。在这些通常的情况下,政治博爱能够为共同体提供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生存希望。只有与政治博爱不同的、没有同情精神的容忍是不够的。这种精神一旦消失,人们就只能是在为了自己的私利时才能容忍,因为从长远来看而不是从近期来看,容忍别人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容忍不管是对获益的赢者(他们可能会认为容忍的原则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对怨恨的反叛的输者(他们总有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为了对他们的压抑合法化的而设计的骗人的借口)都是脆弱的。如果这种容忍的原则要具有真正的力量和持久的影响力,那么它就必须不能仅仅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否则,它就可能沦落为一个只用很小的力量就能把一个分裂团体的各个部分团结起来的脆弱的俗套。只有政治博爱才能提供这种力量。支撑政治博爱的充满感情的亲善精神促进了一种比任何容忍单独创造的更加持久的团结形式,为具有政治博爱的共同体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以避免伴随着每一次严重的政治争论而出现的内部分裂,而不必假称这种争论所产生的分歧没有那么深刻或者更容易妥协。 政治博爱的存在并不要求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根据一些共同的观点对各自不同的价值和目的进行评价。事实上,在争论者的不同意见不能以这种方式比较的情况下我们才最需要政治博爱。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共同体必须从中作出的不同选择是不能比较的,也毕竟有一个评价政治判断的智慧的标准,就像在评价个人于无法比较的个人理想中作出选择的智慧时有一个标准一样。在个人领域作出明智的判断的标志是有利于促进个人的正直。在政治领域,当不同的选择不能用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时,我们可以类似地说,一个人的判断比另一个人的判断之所以更加聪明的是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政治博爱,即个人正直在公共领域相对应的东西。当参与政治争论的人作出促进政治博爱的选择时,我们就有理由称赞他不依赖于我们对他的选择的评价所作出的判断,同样,当他的判断推动了相反的趋势(没有被政治博爱的富有同情心的宽宏大量减弱的党派偏见)时,我们就对其谴责。 任何一个希望成为政治领导,或者是共同体内富有思想的成员的人,当然必须对其共同体的基本目标有一定的哪怕只是暂时的认识。一般说来,大多数政治家在开始参与共同体的深思熟虑的争议时,已经具有某种这样的至少是大概的认识。但是,不管一个人最初形成的观点是多么好,献身于政治及其深思熟虑的过程就意味着接受我在第一章所说的政治自治。它意味着承认一个人自己的观点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可以进行修改,这是政治慎思本身所显示出来的。因此这需要一个人积极地去理解别人的观点,不管它们最初显得多么愚蠢或令人厌恶。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注意别人持有他们的观点这一事实,并把他们的观点所含的主张编成一个附有说明的分类目录是不够的。一个人也有必要把别人关心的事当作是最好的,一种需要与个人慎思相同的想象力的行为。政治思考也需要把同情与超然这两种相反的态度结合起来的能力,想象着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以与他们一样的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们所关心的事,同时又不信奉赋予别人所关心之事以力量的价值和信仰。只有以富有同情心的超然态度审视其共同体内不同成员对其目标的相互冲突的观点的人,才有资格说他自己最初的观点是否应该修正并在他所面对的各种目标中作出有根据的选择。 当然,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做得好,或者因为他们的同情力强,或者他们具有忍受超然所需的暂缓行动的能力要强。那些拥有这两种性格并习惯轻松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人对因争论而使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紧张具有特殊的敏感。那些只从一个党派的立场来看问题的人,不能在想象中超然于自己所关心之事或者说能够容纳别人关心之事,他们很难从对方的观点理解失败的含义。与此相反,那些能够从支持者看问题的物质利益的角度看待关于共同体目标的每一个观点,但对每一个观点都不赞同的人,从各方自己的观点来看,在界定共同体特征的斗争中他们更能理解胜利或者失败意味着什么。他们更能在想象中预计失败者的愤怒和怨恨及胜利者傲慢的冷漠。因此,相比其他人他们能更敏锐地意识到为了保护他们共同体的生存所依赖的同情的纽带而作出的每一种选择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 带着同情的超然慎思的政治家可能不仅仅是对因政治争论而使内部关系紧张更敏感。他或她对减少这种紧张也有较大的兴趣。这一点是心理学的解释。当政治家才能所依靠的情感力量成为习惯的时候——当他们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第二本质的一部分的时候——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儿去维持它,他们的情感的实践本身几乎肯定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这与那些掌握了阅读技巧或者弹奏乐器艺术的人,从积极施展他们掌握的才能中获得乐趣的理由一样。见乔纳森·里尔,《亚里士多德:渴望理解》(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第164—174页;伯尼特(Burnyeat),“亚里士多德论如何学会从善”;谢门,《性格的构造》。我将在第三章进一步讨论内行与快乐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行家资格的关系。那些具有我们称之为政治家才能的深思熟虑的优点的人在施展他们的艺术时可能会找出一种内在的满足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比那些不知这种满足为何物的人可能更喜欢这种才能受到重视 并有机会经常发挥的政治环境,就像喜欢读书的人更喜欢文化受到鼓励的环境一样。 但是我们说政治家被自己的杰出才能所依赖的同情的超然态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和更受到重视的社会制度所吸引,就等于是说他或她被培养政治博爱精神的社会制度所吸引。因为政治博爱只不过是这种态度本身,它是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共同体来扩散的。事实上,有政治博爱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友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弱的政治家才能,它并不需要政治家才能本身那样的杰出才能,不需要那么不同凡响,但与它兼备的情感上相类似。政治博爱是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的政治家才能的一种形式,政治家被政治博爱这一善受到重视并有意识地被认可的大众生活方式所吸引,因为他喜爱深思熟虑及其所带来的快乐。在一个被政治博爱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里,深思熟虑的美德以及与之相关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人参与的共同的善,政治家不由自主地喜爱这一扩大的自我形象。最后,这为我们解释那个普遍的观点的含义是什么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即政治家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公民,不仅仅因为他敏锐的判断力,而且由于他对于大众利益的情感的力量。因为当一个共同体被一个重要得使其身份难以确定的不能比较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分裂时,公共利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政治博爱的保护。 如个人问题一样,政治问题有时在无法比较的价值中也存在着冲突,如果一个共同体要克服这些分歧,那么,它需要的不只是无私的容忍。它所需要的是政治博爱,是容忍与紧密团结的人类团体之间的中间状态,其标志是相同的同情与超然的结合(这是政治家自身所具有的深思熟虑的艺术特征)。政治博爱是非常重要的实际的善,因为最大多数共同体依靠它才能生存。不管他们接受其他什么价值,它是多数共同体因此有理由肯定的善。在这方面,政治博爱类似于个人正直之善。而且,像个人的善一样,公民友谊之善最可能通过那些以富于同情又能超然的某种方式考虑政治问题的人的努力去获得。那些以这种政治家一样的方式思考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对博爱的威胁,更加重视对博爱的保护,在这一大众的善中发现了他们本身重视的个性的概括的表达方式。因此,政治家的智慧既是实体的也是程序的。他之所以英明,是因为他以一定的方式深思熟虑,也因为他的深思熟虑能比别人更稳妥地引向政治博爱。在政治家的特殊智慧中,这些因素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像在那些在个人事务的选择中显现出特别卓越判断力的人其智慧中的那些因素一样。 对政治家才能的这一解释还须加上一点最后的看法。我所做的说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主张之上的,即健全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一种类似于个人的灵魂要健全就必须依赖于正直的内容。但是,在我进行类比的两个东西中间,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显著的区别。政治共同体由单个的个人所组成,因此它们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就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各部分那样联系得那么紧密。因为彼此之间的独立及判断和选择能力的独立性,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必须是典型地通过辩论说服别人参加任何一项政治计划。当然,类似于这样的事在个人的灵魂中也可能会出现。但是,个人思考的过程很少具有两个独立的人的争论所表现出的自我意识的交换的特征。在个人思考中,个人只需说服自己。通常地,在政治争论中,他自己关于共同体利益的观点要压倒别人的话,他就必须说服别人,这就需要有在个人思考领域不需要的另外的艺术:雄辩术,希腊人从一开始就这样称呼它。 政治家英明之处在于他对于实现政治博爱的手段和障碍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并对实现政治博爱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如果要使他的智慧成为共同体生活中的一种力量,要对共同体的政治事务有某种实际的影响,政治家就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他只是众多成员中的一个,他必须通过说服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他不能把自己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必须靠他们能够接受的争论方式赢得他们的支持。史蒂芬·马赛多(Stephen Macedo)在《自由的品德:自由宪政中公民的权利义务、品德和共同体》(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第39—77页中为公开辩论的美德进行了有力的辩解。他说,“公开辩论体现了对人的尊重的复杂的形式。”马赛多也把公开辩论的做法与法官的工作,特别是与司法审查制度联系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他只是用理性的文雅的方式表达他关心的事情是不够的。他也需要用花言巧语的手段在其同伴中唤醒对激发他自己思考的政治博爱的相同的感情。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政治家必须通过雄辩创造出政治博爱存在于其中的同情的感情。在这一意义上说,政治家的论辩必须具有哲学家所说的表演的特征:他们必须通过感情的转化过程,阐明他们辩护的利益(与心理分析学家要想使其疗法有效所讲的话一样)。政治家比其他人能更清楚地看到政治博爱的价值,也更加强烈地热爱它。但是政治博爱的真正的存在要靠他去创造,如果他只是一个政治生活的旁观者,他就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要实现自己的对公众利益的热爱,政治家就必须走进这一充满战斗的领域,努力工作以激发其他人对政治博爱相似的(如果没有自己那么强烈的话)的热情。这种艺术是辩论的艺术,是运用具有抵抗力的人类的材料构筑共同体的艺术,只有当政治家掌握并有效地运用了这一古老的艺术,他的智慧才能结出果实。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为自己创业》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