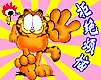第1页:基本信息
第2页:序言
第3页:实践智慧与政治博爱
第4页: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转变
第5页:同情与超然
第6页:懊悔的幽灵
第7页:共同体与妥协
第8页:政治博爱
第9页:卑鄙的手段
第10页:维护秩序的政治
共同体与妥协 本章我从这个地方开始:政治家的才能表现在对公共利益作出判断时具有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在最有分歧的政治争论中——那些涉及共同体身份问题的争论
——我们又很难说这种才能是什么,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缺乏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些地方最需要政治家的才能,但是也正是在此政治家的品德最难界定。
面对这种困境,让我们换个视角,即从政治领域转向个人生活领域,探讨一下在个人生活的领域中在思考个人的自我定位这一问题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意味着什么。我把这一策略看作是与苏格拉底的策略相反的东西,但是与他的策略一样,我的策略也是事先假定在一个领域的解释用来指导另一个领域,那么,其结构和目标是正确的。即,在这一方面,这两个领域是很相似的。说个人思考和政治思考是类似的并不是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做得好在另一方面也做得好。但是,它表明二者在结构上有相似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是类似的。在我解释完个人思考之后,现在可以转向主要的题目——政治家及其所关心的政治问题——来解释我心中的相似或同源(homology)。
在个人思考中,人们经常会问:“我的利益是什么?我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即使一个人得出结论,他自己的利益只有通过与别人一道参加一些共同的事业才能实现。一个人所关心的或者说他(她)的幸福是这类问题的焦点。政治思考的焦点不同,这里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保护或完善某一集体事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政治思考总是意在共同体的利益而不是思考者单个人的利益。正是这一基本的不同点把个人思考和政治思考区别开来,这说明我们把它们比作为两个独立的思想领域是正确的。
虽然个人思考与政治思考强调的是不同的问题,并且是由关注不同的问题所引发,但它们在重要的结构上是相似的。在此之前,我已提到过这一点,现在只需更详细地重复一遍。在政治领域,就像在个人领域一样有一些我称之为确定身份的后果的选择。像个人在确定他的身份一样,这些选择不同程度地确定了共同体的身份。当一个共同体的目标是什么这一问题提出时,不同的参与者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代表着对该共同体本身的目标和它应该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组织安排的不同的理解。这些不同的观念有时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它们可以融合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综合的观点之中。有时其中的某一观念的可以被推迟实现或者被取消。但有时必须在不同的观念中做协调或者说在它们中回避某一选择是不可能的。在此情况下,选择某一观念必然意味着为了一种价值而使其他一些价值处于从属地位或者遭放弃,正如在个人思考领域一样。这就意味着通过对共同体的某一特别的观念的认可,赋予它某些价值而排除其他价值可以使共同体生活的目标更加清晰.共同体像人一样有职业,但也像人一样不可能从事它们所希望的所有职业。因此,就像大多数个人生活一样,大多数共同体的生活一定有这样的时候,即必须作出某种选择,使共同体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有时不可颠倒。这种政治选择等于是共同体身份的一种选择,就像使个人生活呈现独特性的个人选择一样。
而且,与个人在选择的时候相同,一个共同体在此时必须从中作出选择的方法往往是无法相比的。因为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没有大家公认的标准,没有一致同意的解决问题的时机或者心情因素,也不能在确定各成员的位置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中排出一个何者优先的次序来。——因此,当我们只能确认某一种观点时,就没有一个合理标准来判断哪一种观点应该优先。在一特定共同体的具体历史时期,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成员必定都会认为某些观点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他们往往是把它这些观点作为客观真理来谈论或者运用的。我说“必定”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意见的统一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体。例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客观的恶,认为它无论是肉体上还是道德上都是违背人类的真理的。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那些于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共同体最热烈和最重要的争论——对其方向和命运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争论中,各成员之间的看法往往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虽然不同立场的拥护者在这些争论中有时认为他们赞同的价值具有明示的真理的地位,但是他们却找不出有一个大家可以普遍接受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价值。例如,在当代美国,正是这种根本价值的不可比性,形成了这些争论的特征:有人认为堕胎是母亲必要的自由,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谋杀;有人认为死刑虽令人悲痛却是为保持正义的一种必要,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它在道义上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有人把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原始森林看作是神圣的园林,有人则把它看做只具有积木价值的经济资源。今天的美国人面对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们价值观的冲突。这就像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例如面对在两种职业中作出选择或者在家庭和工作中如何分配自己精力这类问题时,各人的看法就会大相径庭。
如果以政治家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往往会说只有通过妥协才能解决如此大的分歧,因此政治家的才能就表现在寻求各方都同意的妥协。这是一个流行的似乎合理的看法,其优点是我们假定政治家协调的这些价值是不可以比较的。因此,妥协这一概念似乎就是我在解释政治家才能时需要克服的以前阻碍它、现在复归原处的障碍。然而,对这一概念本身更仔细的考察表明,事实并非这样。
任何一种妥协在本质上都是交易。某个具有发现潜在的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其他的妥协的才能的人,可以因此被描述为一种具有利用以前未发现的交易机会能力的企业家。如果我们把一个特定团体看做仅仅是满足其成员的预期利益的手段,就容易明白这种机会是怎样地出现以及有关的个人是如何利用它们而使自己的境况变得更好,即使促使不同的成员参加该团体的利益不仅是相互冲突的而且是不能相比的。如果这样去理解,政治只是专业的经济交易形式,它的问题是那种在任何地方交易的各方中都会出现的问题。见安索尼·当斯(Anthony Downs),《民主的经济理论》(纽约:哈伯和罗伍,1957);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个人需求,公共手段》(纽约:基本书目,1970);杰姆士·J·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政治经济论文集》(火努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9)。两个人可能会觉得显然做交易是有利的,即使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不能比较的利益或者抱负。一般说来,每个人都得向另外一个人做点让步才能取得回报。换句话说,两个人必须妥协,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交易利益,即使他们从根本不同的立场来看待这些利益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鉴于我们从经济方面考虑政治,把它看做是追求参加者的预期利益的工具,很明显,妥协在其过程中起着与在经济生活中的其他任何部门中同样重要的作用,那些能够识别对双方均有利的妥协机会的人将会采取有价值的行动,即使假定不存在供参与者的不同利益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的规范或标准。
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治分歧都能这样容易地达成妥协。不同于大多数市场交易——各方认为他们的不同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正视这些差别,试图作出在各方看来都满意的安排——许多政治谈判集中于各方的利益和价值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因此出现了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我们把政治仅作为经济的一个分支)的斗争中一般被掩盖的问题。在这类谈判中,参加者面临着大多数经济交易各方不面对的目的这一问题,不知道妥协在他们回答这一问题中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能起作用的话。
当然,参加者的不同的观点有时证明毕竟是可以兼容的,因此不需要妥协。有时也会出现一个集团把另一个集团认为微不足道的事当成重要的事,或者相反,这使得他们有可能通过其本身可以视为一种交易的相互中立的机制容纳他们相互冲突的主张。如果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合理机会,在得出观点冲突的各方关于他们共同体的目标或价值的不同思想是难以调和的结论之前,先确定是否利用了这些机会显然是明智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各方的观点不仅不同而且彼此对立,以至于不否定另一个的话,哪一个都不能得到肯定时,妥协将是不可能的。这里,如果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必须接受反对方的观点,或者至少放弃自己的观点,这与大多数经济交易形成对照,它不需要这样。许多政治争论,特别是那些涉及共同体身份及与之利害攸关的争论,都属于这一类。这种争论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零和游戏。原文为“zerosum game”,——译者注。说一个人在此情况下通过发现有潜在的妥协的机会而显示出政治才能的话,只有在得出不存在任何妥协的结论之前去寻求妥协总是明智的这一意义上,它才是正确的。然而,这一关于政治家才能的普遍的观点忽视了一些政治争论,包括许多重要的政治争论是参加各方零和游戏这一事实。这里,每一个妥协实际上并不代表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但是,如果政治家才能在此情况下不能界定为妥协的艺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呢?
我的答案是政治家的才能并不表现为妥协的艺术,而是作为有助于获得我将称之为政治博爱的状态能力。政治博爱之于共同体犹如正直之于个人。它保持了共同体内部各成员的统一,使之不至于分裂。没有政治博爱的共同体不再是一个共同体,仅仅是不同部分的集合,就好像没有正直的灵魂只是一套零件而没有自身独立的实在。政治博爱对共同体而言正如正直对个人而言一样的善:存在(existence)自身的善。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认为政治家非凡的判断力——至少在其团体的身份及与之利害攸关的重要的事情上——不表现在能确定什么是正确的(因为可能没有一个评价不同选择的立场)或者具有发现妥协的机会(因为也许不存在这样的机会)的能力,而是表现在具有比别人更有力地推动政治博爱之善的能力。正直在个人生活领域是基本的善,慎思的习惯使得他们或她们更有可能在追求善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智者。我认为在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我想这是在个人思考和政治思考方面进行类比的核心,它是理解公共生活中的实践智慧的含义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