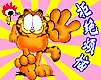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迷失的律师(9)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18 13:30 新浪教育 | |
|
卑鄙的手段 但是对别人没有某种同情,甚至冷酷——与我描绘的杰出的政治家的所必备的同情的超然的特征完全相反的品质——是否有可能成为有影响的政客呢?这是我现 更明确地说,如果一个政客要想获得权力并保持它,他有时就要做出削弱而不是支持政治博爱精神的事情。例如,很典型地,他要必须赢得他所在共同体的某一派别的支持,这经常要求他以更可能加剧冲突而不是抑制冲突的方式漠视甚至压制别人的利益。那些不能忍受它所要求的冷淡有时是冷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成功的政客。他们永远不会获取权力。但是,政治成功所需要的这种冷酷,与我所说的真正的政治家所需具备的态度是对立的。那么,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否提供了否定我对这一美德解释的理由呢? 答案是不。事实上,任何对政治权力的现实有清醒的认识都意味着为政治家的目标一定是维护博爱提供了另外的理由。原因如下: 马基雅维利残忍地坚持认为要想生存下去的君主需要“能够不善良”,对那些从事政治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权力本身的人来说一定感到苦恼的。对于那些把追逐权力当作最终目的的政客来说,当然不会被要获取到权力就得狡猾和冷酷这一要求所困扰。但是,对那些从事政治事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来说一定会被这一事实深感烦恼,即为了取得实现他的目标所需的权力,他就必须采取冷漠和残忍的做法。任何具有广义上的政治理想的人一定会把权力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当他所使用的手段与他政治行为的目标相冲突时,他一定感到忧心忡忡。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那些把权力本身作为最终目标的人才不会感受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其他的想法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它是反对乌托邦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 因此,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所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是政客把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冷酷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的能力问题。只有那些把权力本身当作最终目标的人才不屑于这样做(当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除外)。每一个其他的政客——每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客——都承认为了实现他或她的最终目的,一定程度的冷酷是必要的,但也同时认为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能够避免的话就尽量避免。对于一个理想主义的政客来说,只有在冷酷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其实现的价值超过了冷酷本身所含的任何下流和不道德时才是正当的。 这种理由的主要危险是它们的扩散。一旦一个人像每位政客必须的那样接受一点点冷酷,那么接受更多的冷酷就比较容易。对于从事政治的人来说,习惯于把冷酷行事当作不可避免的工作状态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并能因此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容忍这种行为。这是政治带给那些从事政治的人以及所有生活受其影响的人的最大危险。只有那些非常圣洁和谨慎而不卷入政治领域的人才能免受它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客都同样面临着危险。有一类政客特别容易受到攻击,他们的理想形成于这样的人类生活观念,即理想的实现只有一部分人赞同就可以了,他们认为别人的观点是错的或者是邪恶的。因为如果有人认为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被证明是最好的,那么其他人不同意并走着不同的道路这一事实就只能解释为是错误的结果或者是罪恶了。如果有人把这一他赞成的生活方式作为其政治和个人的理想,那么通过教育或惩罚的手段矫正那些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就可能是他的计划的重要部分。从这一观点来看,大多数共同体内成员之间存在的信仰和行为的分歧一定会被认为是要加以纠正或者克服的缺点。 也许,起初治愈所需的疗法的是温和和慈爱的。但是,在每个这类方案中代之以不断加剧的冷酷作为追求的目标的是危险的。因为那些拒绝放弃误入歧途的生活方式的人,在他们心灰意冷的支持者眼中迟早会变成无能之辈。如果他们继续抵制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执意顽固或者盲目地迟钝,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拒绝的理由对于那些想把他们从无知和罪恶中解放出来的人来说,似乎显得越来越不值得考虑。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他们的拯救者曾经感到对于强有力地压制这种邪恶和罪过之中的固执的任何犹豫也可能慢慢消失。这样,冷酷的道德障碍就减弱了,人类的代价被掩盖了。最终,这些损失会完全无影无踪:失去被压抑的生活方式不再觉得是任何损失。在我们这个世纪——伊赛·伯林说,欧洲历史中最恐怖的世纪——我们看到以至今似乎仍不可思议的规模实施的极端的政治残酷。纳森·伽德尔(Nathan Gardels),“两种国家主义观:伊赛·伯林访问记”,《纽约书评》,第21卷,1991,第19、21页。柏林说:“我已八十二了,实际上已生活了整个世纪,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世纪。在我的一生中所发生的可怕的事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多。甚至我怀疑比匈奴人的时代还要糟糕。”他令人寒心地总结道:“所幸的是我已老了。”也见伊赛·伯林(Isaiah Berlin),“理想的追求”和“西方乌托邦思想的衰落”,载《人性扭曲的素材》,亨利·哈代(Henry Hardy)编(纽约:诺普,1991),第1—48页。但是,这种冷酷的危险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于每一个开始于理想地致力于某些不管多么崇高的狭隘的和排外的人类利益观念的政治行动中,也不仅仅存在于20世纪的极权运动之中。可以清醒地回想,即使柏拉图的宏伟的共和国,也只有在整整一代的孩子首先被放逐或者被消灭的条件下才能建立。柏拉图:《共和国》,541a。 相比而言,如果人们一开始承认人类利益不能比较的多样性,冷酷的危险就会降低。那些相信有实现抱负的不同的途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使它们作出确定的排列的政治家,不会把多样性本身作为需要矫正的道德或者认识的失败的特征。即使他本人赞同其中的一条途径,他也会认为强迫那些不同想法的人与他的想法一致是不合适的。除了承认坚持他的利益观优于他人的利益观缺乏理性基础外,如果他也能看到别人工作的意义,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和价值的力量——不管与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同,他也能同情那些使生活方式充满活力的事情——那么,他就可能认为强迫压制别人的思想和行为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某种人性的宝贵的东西的丧失。他比那些把被压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看作是邪恶或者犯罪的产物的人对这种安排的人类的代价更为敏感。事实上,他的带有情感色彩的政治观多元论不但没有削弱他在采取冷酷的态度时天性的犹豫,反而可能起着恰好相反的效果。如果某种行为的进程可能冒犯别人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自己的价值观会使他更加不情愿地继续进行下去。它们将是冷酷的障碍,而不会受到它的欢迎,它们不同于那些除了在他支持的利益之外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内容的政客的价值观。 政治博爱是带有感情的多元论价值的理想化表达形式,追求这种价值被当作是目的本身。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所有政客中,那些追求这一目的人是最为抵制政治行为都带有的冷酷的危险的。只有乌托邦才会相信这一危险能够消除。“那些寻求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拯救者,不应该沿着政治的道路去寻求,因为完全不同的政治使命只能通过暴力来解决。”见马克斯·韦伯,“作为职业的政治”,《马克斯·韦伯论文集》,第147页。无论我任何时候踏入政治领域,不得不冷酷地对待我的反对者的冒险都是一个危险,每一个政治领导的概念,包括我自己的,都必须诚实地面对这一现实。真正的问题——也是惟一的问题——是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怎样有效地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诱惑,正是它的破坏力(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有自己的性一般的魔力。S·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杰姆士·斯特凯编译(纽约:诺顿,1961),第38—58页。我的主张是一些政治理想比其他理想应当给予更多的保护,而政治博爱理想又是应当给予保护最多的一种。具有这种政治理想,并坚持韦伯所说的主宰一切的价值“多神论”的从政者,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迫使自己放弃政治必然包含的暴力,见马克斯·韦伯:“作为职业的政治”,《马克斯·韦伯论文集》,第147页。并说:“这是我无法容忍的,是我无法达到的。”他对暴力的反感根植于他的性格之中,根植于他看待广泛的相互冲突的人类利益时将同情与超然的习惯性结合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在避开政治中的不可避免的冷酷的膨胀趋势时有了最可靠的保护。某些这类冷酷是无法避免的;它是伴随着领土而产生的。但是,那些把维护政治博爱作为他的主要高目标的政治家,以我们有理由希望所有的政治家都具有的精神严阵以待直面这一恶棍并与之进行战斗。因此,马基雅维利残忍的坦率描绘出的政治权力的现实,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把政治博爱理想作为只有天真的人才赞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幻想而加以拒绝的理由。恰恰相反:勇敢地承认这些现实,我们更有必要坚持这一理想。 无疑,在政治博爱的目的和为了这一目的偶尔必须使用的残酷的手段之间的冲突比其他一些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更为紧张。政治家热爱博爱,但是为了实现其目的有时又必须做出不博爱的事情来——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就是必须“能够不善良”。因此,正如我们试图理解政治博爱自身的含义时一样,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似乎对立的两种品质的结合。然而,一个政治家必须具有这两种品质的结合,否则,他要么是因认为政治是不可救药的腐败的事业而放弃,要么就是被“潜藏在所有暴力之中的恶魔的力量”所卷走。马克斯·韦伯:“作为职业的政治”,第125—126页。这种结合很难比实践智慧内含其中的同情与超然的结合更容易。但是,每一个从政之人要想成为政治家,他就必须以此作为他的目标。如果说在这一努力中成功的要远远少于失败的这一说法不合适的话,那么我们最好用斯宾诺沙的著名的观点来概括,即“凡是高贵的东西像其稀有一样难以获得。”贝尼迪·斯宾诺沙(Benedict Spinoza),《伦理学》,第五部分,命题四十二,见《斯宾诺沙选集》,约翰·韦得(John Wild)编(纽约:查尔斯·史宾勒之子,1930),第400页。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为自己创业》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