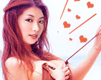| 学校不能变官场 北大教授贺卫方停招抗争旧规则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7/01 10:09 南方都市报 | |||||||||
|
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停招”研究生之举,引起了舆论广泛而热烈的关注。我不赞成有些论者的“一怒之下”之说,而相信贺卫方先生并非一时冲动,乃是掂量再三之后的理性选择;更不赞赏一些人将此举简单地概括为“不与体制合作”,当然也不认为贺教授是什么“消极地逃避”,是“撂挑子、甩手不干”。贺卫方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对他的心迹表露得很明白,因为这样的招生规则使“老师、学生都不爽”,也就是说他要对自己的良知、对学生的前途负责。他的“停招”是出于无奈的反应,也是对现行招生规则
贺教授诉诸舆论后的结果会不会失望呢?不容乐观。因为他面对的不是虚怀若谷,惯于倾听不同意见的教育家或大学管理者,而是我行我素的“教官”: “贺卫方告诉记者,不久前学院里的一次教师座谈会,围绕着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绝大多数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考试模式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6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国情”版) 我搞不明白,既然是决意按既定方针办,还召开教师座谈会讨论个什么劲,是想作“民主办学”秀,还是想听听“领导英明”之类的赞歌?总之,众教师的千言万语,顶不上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一句指示。这样的大学“决策者”,还是“杏坛”的主事人和教育家吗?不过是仰承上峰指令行事的特派员、“监理员”,是“有司”的差人和工具。 北大有如此人和事,清华有如此人和事(清华的陈丹青教授发表过伤心语,即对学校领导人讲话,“我就像对着空屋子讲话”,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会听取我的意见),别的高校呢?6月3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做了一个“聚焦大学校长”的专题,有意味的是,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看来,人们的观察与贺卫方教授的现实遭遇是相当接近的。 可是,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学苑”,它们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怎么能忽视师生的诉求和意见,将它们变成“有司”的附庸?“文革”中搞的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祸国殃民的拆烂污;对所谓“教授治校”,我也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在当代社会,大学的管理与经营也是需要专门知识和人才的,社会、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各方的意愿都不可忽略,需要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寻找一个均衡点。但有一点是铁定的,“杏坛”不能变“衙门”,不能搞“科层制”的下级对上级负责;特别是校长、院长不能变官僚。 当年,蔡元培先生对学校的官僚化强烈不满,愤然写下了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参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网上可搜得此文)《南方周末》这回做的专题中,有丁学良教授谈大学教育的文章,第一条就是讲“大学校长不可‘做官’”。他说:“以官本位的态度,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在价值观念与处理事情的方式上,这样的校长一定不会把大学当作一个社会公共功能很特殊的机构,而只是把它当作衙门,甚至更糟糕的,是衙门的附属物来管理。” ——应当承认,学校不能变官场,或者委婉地说,教育与学术管理不能行政化,本是古往今来、海内海外一切有识之士乃至平民百姓的共识。 这种问题解决好了,陈丹青、贺卫方等教师们的意见得到尊重,教育规律、人才培养规律得到尊重,我想,陈丹青出走、贺卫方罢招之类的事件就不会再出现,至少不会这么引人注目。 丁学良教授、谢泳、余世存等学者问得好:既然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可以转型,淡化行政官员色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条件下向企业家转变,为什么不可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使大学的校长、院长们向教育家转变呢?(作者: 鄢烈山) 更多信息请访问:北大教授停招研究生VS伤痕累累的研招制度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教育时评 > 北大教授停招研究生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教育频道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28888-5227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