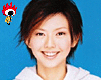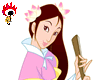| 4/战前训练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6/10 14:1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约翰·克里驾着他的双人座飞机飞过旧金山湾,冲向金门大桥。“我们从桥下穿过去吧!”克里激动地对他惟一的乘客大喊着。他的密友大卫·索恩不敢低头看下面汹涌的波涛,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被吓得尖叫起来。
|
那是1967年夏天,克里前一年6月刚从耶鲁毕业,后来又在罗得岛的海军预备学校受训了六个月,现在则正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为期一年的飞行训练。这几年来,他一直和好友索恩的双胞胎妹妹——美丽的朱莉娅·索恩约会,她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克里酷爱飞行,可是,他的父亲理查德·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后备飞行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战争时期做飞行员会让你以后对飞行索然寡味,于是克里应征当了海军,飞行则仍然是他的业余爱好,今天他就驾机出去兜风冒险。金门大桥已经在视野内了,天很蓝,克里稳稳地控制着租来的T34飞机的操控杆,该型号的飞机只有一个引擎,类似军事训练机。两个年轻人紧张得屏住呼吸,期待着飞机来一个漂亮的转弯然后穿过金门大桥桥洞。
轰隆!
飞机突然开始颠簸起来,左右摇晃着。一只海鸥的双脚卡在了飞机一个机翼上,就像动画片里的惊险镜头一样。几秒钟之后,情景更恐怖了,就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的影片一样,越来越多的小鸟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果小鸟撞到了挡风玻璃上,克里恐怕就要当场丧命了:一个耶鲁毕业生,一个梦想成为总统的青年,就这样在旧金山海湾上方的一次驾机冒险中丧命。
不过,克里很冷静,他拉高了操控杆,飞机逐渐升高,躲过了这群危险的小鸟。
“我们非常担心机翼会掉下来。”索恩回忆道。于是克里驾驶飞机飞离了大桥,驶向附近的飞机场。他驾驶飞机的冒险计划,就这样永远埋藏在他23岁的心中了。
克里与大卫·索恩的关系是终生的友谊。当双方都知道二人在同时与珍妮特·奥金克洛斯约会后,他们都为了朋友放弃了女友,转而去与其他女孩约会,二人则继续做好朋友。一天,就在克里准备进入大二时,他拜访了索恩位于长岛的家。当克里乘坐公共汽车到来时,索恩的双胞胎妹妹朱莉娅正身穿比基尼站在那里,大声唱着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成名歌曲《五百英里》。
“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朱莉娅多年以后回忆道。
二人迅速就产生了好感。两个人都来自显赫的家族,都曾在欧洲居住过。朱莉娅的祖父拥有部分希尔顿海德岛(Hilton Head Island),该岛后来被出售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她的叔祖(great uncle)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争顾问。她也是威廉·布拉福德的后裔,布拉福德签署了《独立宣言》,是美国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长。这样名望之家的后裔显然与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门当户对。他们都对欧洲有同样的感觉,都有双语生长环境,都有一种上等阶级的贵族感觉,两个人迅速坠入了情网。克里尽管言语犀利,能言善辩,可他在异性面前还是个很害羞的人,而朱莉娅却让克里感觉相当自在放松。
朱莉娅没有上大学,主要原因是她富有的父母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大学接受教育。“我是那种上流社会乘私人飞机到处游玩的人,我在上流圈子里长大。”她说,“我母亲的价值观念体系仍然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她清楚地知道那个年代一个上流年轻淑女的生活应是什么样子,而这种生活不包括上大学。其实,对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而言,知道恰当地待人接物是远远不够的;不上大学简直浪费了大脑。”
他们的罗曼史开始了,克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她的男友,还是她的老师。克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和平、政治、历史和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让朱莉娅大开眼界。“我渴求知识,而约翰极大地满足了我。他考虑如此多的事情,他开始了我的教育。”
数月以来,克里和朱莉娅一直约会,可是克里在耶鲁的时候,朱莉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克里毕业了,可是他还要履行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约定。1966年秋天,他来到了位于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履行与海军长达六年的服役承诺。当初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他的一些朋友继续读研究生;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他的女朋友在大洋彼岸,而他却被一个约定牢牢地拴在这里。当时,朱莉娅在欧洲也与其他人约会,不过在她哥哥和克里受训期间,她也定期地回到加利福尼亚。她与克里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1967年初,克里离开罗得岛来到加利福尼亚接受海军循环训练,先是去旧金山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然后去圣地亚哥。越南战争迅速升级。1966年1月1日——当时克里还没有毕业,刚刚决定参加海军,美军在越战中阵亡的人数仅为636人。而到1967年初,阵亡数字翻了十番,高达6644人。到1967年末,阵亡数字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6 021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如“潘兴行动”——大概是以理查德·潘兴的祖父命名——举步维艰,往往要进行一年多。
1967年6月23日,克里和大卫·索恩当时都在南加州,他们听说约翰逊总统要来洛杉矶饭店,而数千名反战者计划届时将举行集会。出于好奇,这两个年轻人脱下军装,换上普通衣服来到世纪广场饭店观望。
当约翰逊在500美元/每位的筹款晚会上对1000多位民主党员讲话时,15 000名反战者组成庞大的游行队伍,围绕饭店大声喊:“嘿!嘿!我们的总统先生,今天又有多少孩子为你丧生?”当反战队伍聚集到饭店门前停下时,约有1300名警察赶来驱散队伍,并以非法集会并拒绝散开为由当场逮捕了51人。
克里和索恩震惊了。“我们在游行队伍的外围,听着他们的口号,彼此交谈着,颇为担心。”克里回忆道。“那看起来是个相当和平的游行,”索恩回忆道,“可是警察很凶狠,开始打人。队伍被驱散了,场面相当混乱。我只记得我震惊极了,约翰也很震惊。”
骷髅会里的另两个好朋友——史密斯和潘兴——几个月后就来到了越南,那是1968年初,那时克里和索恩还在接受训练。这四个骷髅会会友相当亲密,经常彼此写信询问对方的近况。索恩和克里对在越南的好友非常担心。
史密斯在越南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潘兴则作为第101空运分队的少尉努力续写家族的显赫军事历史。潘兴的视力很糟糕,他完全可以免除服役,可是他却设法搞到一份放弃免役的证书。于是,1967年12月,他上了战场,追随祖父和父亲的足迹,他的父亲沃伦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
就在潘兴到达越南后不久,1968年1月31日,北越军队发动了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一系列奇袭令美国和南越军队伤亡惨重。潘兴和他所属的军队迅速投入到战斗中,结果惨不忍睹。“理查德·潘兴就站在那里,”一个人回忆道,“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刚才的战斗让他损失了一半部署,也许是三分之二。现在他要安排埋葬死者,保证把他们的个人物品寄回家中,还要给家属寄阵亡通知单。”
尽管死神就在前方,潘兴仍毅然返回战场。从那时他的一张照片可见,潘兴一身戎装,体格健壮,相当英俊,皮肤被太阳晒得很黑,带着一副厚眼镜。他的衬衫没有系扣子,露出了胸膛;腰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肩上挎着步枪。他一手抓着一瓶百威啤酒,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包裹和一封航空信。
1968年2月17日,就在拍这张照片的几天后,潘兴和他的队员在稻田里遭到了越共的火箭弹袭击。起初,似乎每个人都幸存。可是随后潘兴发现他的一个队员不见了,掉队了或是受伤了。就在他独自回头在稻田里寻找队员时,一枚火箭推动的手榴弹向他飞来。
潘兴死了。
非常巧合,此时弗雷德·史密斯就在距战场约三英里的地方。在耶鲁的时候,史密斯、潘兴和克里一起度过了许多嬉笑打闹的时光,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么快乐,可又那么短暂。现在,史密斯惊闻潘兴阵亡的噩耗。耶鲁的同学之情、骷髅会的兄弟情谊以及两个人的友情驱使弗雷德来到潘兴倒下去的地方凭吊好友。
“那是个很常见的地方,稻田、水坝、村庄,没有什么重要的。可是就因为它完全不重要才显得重要——无数生命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长眠于此。我们正在用美国男孩的生命换越南男孩的生命。
他们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袭击,我们总是伤亡惨重。潘兴和他的排当时正在巡逻,敌人袭击的时候有一两个队员受伤或是阵亡了,潘兴回去想要找回他们,结果也牺牲了。”
大卫·索恩当时正在海上美国军舰Maddox上,舰上官员递给他潘兴阵亡的电报,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友已经长眠于越南了。他愤懑得无以复加。
克里此时也在海上Gridley号军舰上,这是一艘巡航导弹护卫舰,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朝越南东京湾开去。就在这时,好友阵亡的噩耗让克里顿时呆住了。一个军官拿着一封电报来甲板上找克里:“你认识一个叫做理查德·潘兴的人吗?”随后,军官递给他电报,克里颤抖着打开电报,害怕看见最担心的消息。“潘兴,”电报上写道,由于“寻找失踪的队员遭遇敌军火箭弹袭击而受伤阵亡”。
对于克里来说,这场战争不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为了寻找掉队的队员而牺牲。可是克里远在海上,却无法参加他最好的朋友的葬礼。他给朱莉娅、大卫、潘兴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写了信,倾诉心中的苦恼和悲愤。
亲爱的妈妈爸爸:
我能说什么呢?我现在空虚、痛苦、气愤,似乎失去了一切,只有战争、暴力和无穷无尽的战斗。我不知道战争如此残酷,如此不近人情——任何人都可能接近潘兴并夺去他的生命。多么该死!我们做了多少无谓的牺牲!为什么?我原来从来没有这种空虚的感觉……
失去了潘兴,一些东西似乎也离我而去了——他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是与我分享爱、忧愁、欢乐和痛苦的兄弟,是他人永远也无法替代的。
然而他已无法回头。潘兴的骨灰正运回美国,克里正要踏上越南战场。战争就在前方等待着。
就在克里还在太平洋上航行时,约翰逊总统和他的战争内阁也正面临着危机。“春节攻势”让北越付出损失了4万名士兵的代价,重创美军1100人,南越军队2300人。尽管比起敌人来伤亡数字不算惨重,可是北越显示出了在多地点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还短期占领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这大大打击了美军的士气。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这些事情改变了美国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美国和南越联盟与北越就前越南首都顺化展开了长达26天的拉锯战,几番攻占又几番被夺去,双方都伤亡惨重。这更加引发了国内对越战的不满,激发了新一轮反战运动。美国军队指挥官请求国内再增派206万名士兵,群众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越南的最高美国将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被罢免了职位。
就在这一时期,约翰逊总统被越战旋涡弄得晕头转向,几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中输给明尼苏达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沃尔特·克罗凯特从西贡返回,在媒体上宣称他“越来越肯定美国对越南的血腥干涉将以僵局而告终”,这个论断后来被认为是民众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罗伯特·F.肯尼迪宣布他计划竞选总统。3月31日,约翰逊宣布他将不会争取连任。四天后,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各地暴动几乎遍及全国,一些人担心美国也会变成战争前线。
在Gridley号上,克里只能得到关于国内这一系列大事的零星报道。他的航海旅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现实的,奇异地脱离开了在越南和国内的紧张氛围。他乘坐着装满武器的护卫舰,航行在从夏威夷到新西兰相对平静的海面上。该军舰仅在美军的越南基地短暂逗留,在那里克里看见越南人的尸体像木柴一样被堆成了小山。
“我并不知道我们究竟要面临什么该死的东西。”克里数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该文章被收录在《亲历越战:战事回忆》一书中。“我每天要去岘港(Da Nang)待上八小时,看那些战争中的军人配备,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航空母舰上忍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
1968年6月初,克里和美国军舰Gridley号驶回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港口。他坚决拥护罗伯特·F.肯尼迪,就在舰船靠岸那天,肯尼迪正在加利福尼亚参加总统初选。
克里的舰船正要驶进船坞,一个惊人的消息爆炸开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饭店遇刺,他刚刚赢得加州初选。对克里——这个以约翰·肯尼迪为偶像、期待罗伯特·肯尼迪终结战争的年轻人来说,这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
Gridley号进港了,克里最好的朋友大卫·索恩在港口等待他。当索恩远远看见克里时,索恩伸出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就好像举着枪对着自己一样。克里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个手势表示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
朱莉娅也在港口,穿着一身绿松石色的连衣裙在远处等着克里。她的出现对克里来说是个惊喜,朱莉娅数年以后还能想起见到未婚夫一身戎装、跳过来与她拥抱的情景。这是索恩兄妹和克里欢乐的重逢,但也是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悲痛和哀伤的一天。拥有另一个肯尼迪总统的梦想破灭了,整个国家也都笼罩在这种悲伤之中。反战人士聚集起来,嬉皮反正统文化开始在青年人中间盛行,一些大城市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克里请了几天假,回到马萨诸塞看望了父母。然后还被吸引去了波士顿红袜(Red Sox)棒球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不是为了棒球,而是为了政治。1968年7月25日,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也是激烈的反战人士,他仍然打算争取民主党内提名,他来到芬威球场演讲,吸引了多达45 000名民众。
“那是波士顿红袜棒球队赢得冠军以来最疯狂的夜晚。”《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罗伯特·L.特纳写道。这是这个棒球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所有的坐位全都坐满了,5000多名观众不得不站在外面。克里一年前已经在洛杉矶见识过反战场面,现在这位反战总统候选人的演讲让他痴迷,又让他不安。但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一个海军战士,仍然要上战场。“我在军队中,我正在休假,我听着他的演讲,我对政治异常痴迷。”克里回忆当时的感觉时说。
8月,克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从电视上得知芝加哥的反战运动搅乱了民主党全党大会。但是克里无法再在国内的政治混乱中倾注太多的注意力了,在返回越南之前,他还要去圣地亚哥的快艇训练学校,然后还有更残酷的训练——莫哈韦沙漠中的生存训练。
1968年9月,克里前来参加逃生、对抗和躲避训练,在该训练中,海员们被当做战俘对待。他们要忍受嘲弄、辱骂、鞭打以及心理骚扰,这些都是为以后他们不幸被俘而做好准备。生存训练营是一场模拟训练,可是训练结束后,克里就要回到越南,真刀真枪地面对真正的敌人。
在分别之前,克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和朱莉娅见面。他们都知道潘兴离开未婚妻去越南,可再也没有回来见她。现在,就在克里和朱莉娅难舍难分的时刻,他们定好了未来的计划:等到克里从越南回来后他们就结婚。克里并不想让朱莉娅独自承担战时未婚妻的等待之苦和重大压力,于是他们只是将这计划告诉双方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
1968年11月中旬,克里登上了飞往越南的飞机,他将成为管理六个人的“快艇”船长,负责巡逻海岸线。克里离开祖国,心想自己巡逻越南也许相对安全。可是他不知道在西贡,美国海军改变了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