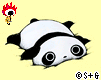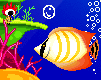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南茜·克鲁塞“植物人”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06 18:12 法律出版社 | |
|
(一)案例简介 案由:一场严重的车祸使南茜·贝丝·克鲁塞变成了植物人。在确信女儿没有机会恢复意识功能后,南茜的父母即监护人勒斯特和焦斯克鲁塞向初审法院请求撤除她的人工饲养和喂水设备,这意味着南茜将会死亡。 初审判决: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初审法院的允许。法院认为宪法赋予了南茜拒绝“苟延生命”的基本权利。但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以有争议的投票否决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密苏里最高法院认为没有清楚的和令人可信的证据表明南茜本人希望结束维持生命的治疗,他的父母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请求。南茜父母提出上诉。 终审判决:联邦最高法院调取该案复审,结果是: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该判决引起了很大争议。 (二)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首席大法官雷昆斯特呈递) 1983年1月11日,当南茜驾车行驶在密苏里州杰斯皮尔郡的爱尔公路上时,汽车失去控制并翻转,南茜被发现脸朝下躺在一个沟里,已经没有呼吸。现场急救人员恢复了她的呼吸和心跳,她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被送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诊断南茜由于严重缺氧而导致脑损伤。通常人体在缺氧6分钟以后会产生永久性脑损伤,据估计,克鲁塞当时已经缺氧12到14分钟。昏迷三周以后,她逐渐可以进一些营养物质,但仍然没有知觉。为了加快克鲁塞的进食和康复,在她当时的丈夫同意之下,医院进行了胃切开术并植入一软管喂水。然而这些康复努力最终都被证明无效。目前,她躺在密苏里州医院成了一位“植物人” :没有任何意识反应,只靠机器维持生命。密苏里州承担医疗费用。 初审法院证实,南茜25岁时曾和她的一位室友谈到:如果生病或受伤到连“半正常”的程度都不能达到,她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推断,如果她知道现在成了“植物人”,肯定会同意终止人工维持生命。 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州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密苏里州生存意愿法”“密苏里州生存意愿法”:Missouri Living Will statute, Mo.Rev.Stat. §459.010 etseq.(1986),公民有权拒绝治疗,但必须(书面)告之其同意,但南茜的父母不能拿出女儿的书面证明。州最高法院还认为,克鲁塞对其室友提起的关于她在如此环境下的生死愿望“不能作为可以代表她选择的可靠依据”, “也不足以支持监护人的请求,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南茜本人的判断”。州最高法院因此拒绝授予克鲁塞父母终止其女儿药物治疗的权利,“在没有按照‘生存意愿法’的要求办理正式文件和出示清晰的、令人可信的证据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假设当事人会作出这样(终止药物治疗)的选择”, 州最高法院还指出,“关于生和死的更宽泛的政策问题应该由议会而不是司法机关来讨论决定。"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联邦宪法是否授予了克鲁塞在“植物人”的状态下仍然有要求医院终止其维持生命的药物治疗的权利。 在普通法中,在没有征得同意或没有合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触碰他人是一种侵犯。早在1891年波兹福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指出,“根据普通法,没有哪种权利比个体拥有和控制自我、不受任何其他人的限制干涉的权利更加神圣和值得悉心捍卫,除非不得不受制于法律的清晰而绝对的权威”. 引自波兹福特案:Union Pacific R. Co. v. Botsford,141 U.S.250,251,11 S.Ct. 1000,1001,35 L.Ed. 734(1891)保护躯体完整的概念体现在药物治疗通常要求(病人的)书面同意。“每一个成年、拥有健全头脑的人都有决定在他的身体上将做些什么的权利;一个医生在没有病人同意的情况下做手术是对病人权利的侵犯,须负赔偿责任。" 引自斯切诺道夫案:Schloendorff v. Society of NewYork Hospital,211 N.Y.125,129-130,105 N.E.92,93(1914)至此,必须征得书面同意的规定被牢固地植入美国侵权法中。 书面同意的逻辑推断是:病人拥有不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15年前,作出拒绝治疗决定的数量非常少。在早期的案例中,病人拒绝治疗大多由于宗教的原因,由此产生第一修正案及普通法对治疗的自我决定权。最近,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对生命的延长已经超过早期自然死亡的界限,于是,拒绝延续生命治疗的案例出现了。例如,在昆兰案昆兰案:In re Quinlan, 70 N.J. at 38-42, 355 A.2d, 647 cert.denied,429 U.S. 922,97 S.Ct. 319,50 L.Ed.2d 289(1976)中,年轻的昆兰由于缺氧而遭受严重的脑损伤成了植物人。昆兰的父亲请求法院同意拆除女儿的呼吸器,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同意了他的请求,认为根据联邦宪法昆兰有终止治疗的权利。然而,这个权利不是绝对的,法院必须将它与国家利益进行平衡。法院注意到,随着(昆兰)肉体受侵害程度的增加以及痊愈可能性的渺茫,个体的权利就随之增加,同时国家利益减弱,这个时候国家利益就必须让位于个人利益,法院最后判定,保护昆兰个人权利不受侵害的“惟一的最现实的方式”是允许她的监护人决定她是否维持目前的状况。之后,多数法院把拒绝治疗的权利或者建立在普通法书面同意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普通法和宪法隐私权的基础之上。 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除非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由此可以推导出:宪法保护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拒绝进行药物治疗的权利。例如,最高法院曾判决了一个拒绝注射天花疫苗的案例,在此案中,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早在第四修正案并入第十四修正案之前宪法就规定,诸如搜身和拘留这种涉及身体的行动必须符合程序公正法条款,因为它关系到人身自由权。 然而受程序公正法保护的自由权利也得接受法庭的质讯,“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应该通过在平衡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得出”. 引自杨伯格案:Youngberg v. Romeo, 457 U.S. 307,321,102 S.Ct. 2452,2461,73 L.Ed.2d 28(1982)申诉人(南茜父母)坚持认为在一般的案例下,决定是否被迫施与维持生命的药物治疗或者人工喂饲食物和水是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自由权利。然而,虽然上述案例从逻辑上包括了这样的自由权利,但由于拒绝治疗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对宪法是否允许剥夺自由权利的问题提起质讯。就本案而言,我们假定美国宪法会赋予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受宪法保护的、拒绝被喂养水和营养品等维持生命物质的权利。申诉人接着声称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如植物人)也应该拥有与有行为能力的人同样的权利。 申诉人的难题在于: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不可能作出书面同意并自愿作出选择,拒绝治疗的权利或者其他的什么权利对她来说完全是假设,而这样的“权利”又必须被她或她的代理人履行。在这里,密苏里州最高法院认为,代理人可以替病人选择撤销水和食物的人工喂饲,最终导致死亡。但是,这种选择必须要有一个程序上的“安全屏障”以确保代理人的选择最好地遵照了病人的愿望,这个愿望通常是病人在有行为能力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密苏里州要求必须要有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病人确实有撤销治疗的愿望。问题是美国联邦宪法是否允许该州提出这种程序上的要求。答案是:允许。 密苏里州所提出的必须出示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要求是否符合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要保护的权益是什么。该州认为是人的生存权,这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国家,包括所有崇敬生命的文明国家,都认为杀戮是严重的犯罪。我国大多数州认为辅助他人自杀也是犯罪,因此,最高法院不会要求一个州在某个成年人自愿要求饿死时保持中立。 在本案中,国家利益更重要。很明显,虽然生或死的选择最终是个人的选择,但密苏里州通过强化证据要求可以合法地捍卫个人的选择。不是所有失去行为能力的人都愿意代理人为其作出决定,哪怕代理人是家庭成员。“自然会出现这样的不幸情况:家庭成员作出的决定不是为了保护病人”. 引自约伯斯案:In re Jobes,108 N.J.394,419,529 A.2d 434,477(1987)在这种情况下,州政府就有权利采取措施防止代理人权利的滥用。同样,州也有权利判断有关司法程序是否考虑到病人的真实愿望。最后,州应该适当拒绝给特殊个体的“生活质量”下判断,同时,在断定哪些权利不能受到宪法保护时应慎重行事。 不言而喻,该案所讨论的有关个体和社会权益的问题更现实地存在于操作程序而不是精疲力竭的争议中。必须提供证据,这个要求不仅反映了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法庭判决的重要性,而且反映了对“错误决定的风险应该如何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分配”这个问题的社会判断。对举证一方的证据要求越严格,它承担错误的风险就越大。可以允许密苏里州把更多的决定错误的风险放在请求终止病人维持生命治疗的一方。因为一个不终止治疗的错误决定导致的结果最多只是维持现状、等待科技发展带来治疗的可能性以及发现新的有关病人意愿的证据、法规的改变、病人的意外死亡等,而且至少还存在纠正错误、减少错误带来损失的可能。然而,一个终止治疗的错误决定无疑是不可纠正的,这个决定是最终的和不可撤销的,它会导致病人的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州都不承认口头证据,虽然重要,但它不能用来决定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在普通法和多数州法规中,有关证据的条令都禁止口头改动书面合同,合同欺诈条款也规定口头合同分配财产无效,遗嘱必须全部以书面形式表达。无疑,这些规定有时可使一些特殊死者的意愿无效,就像本案,密苏里州法律对证据的要求使(在出事前)“没有很好表达其(如果在植物人状态下的)生死愿望”的南茜的意愿无效一样。宪法并不要求所有的法规都完美无缺,事实上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 密苏里州最高法院认为初审法院出示的病人希望终止维持生命治疗的证据不是清楚而令人可信的。因此,它推翻了初审法院“有证据表明南茜不愿意维持目前现状”的判决,在初审中,法院并没有按州最高法院的规定采纳“清楚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标准。初审法院的证据只是出事前一年南茜同她的室友说过:如果“植物人”的情况发生在她的身上,她不会再活下去;以及其他的一些观察,这些观察与终止药物治疗的关系不大。基于此,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判决:不能终止南茜的药物治疗。 申诉人认为法院应该接受最亲密的家庭成员代替病人作出的决定,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意见代表了病人的意见。他们提出迈克尔·H案迈克尔·H案:Michael H. v. Gerald D,491 U.S.-,109 S.Ct.2333,105L.Ed.2d 91(1989)和帕翰案帕翰案:Parham v. J.R., 442 U.S. 584,99 S.Ct. 2493,61 L.Ed.2d 101(1979)作为依据。确实,在迈克尔·H案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加利弗里亚州肯定传统家庭关系的判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要求一个州在处理类似南茜案时必须首先考虑家庭关系。在帕翰案中,病人尚年幼,州法院同意父母可以为患有精神疾病的年幼病人作出决定,最高法院也判定其符合宪法。 无疑,南茜的父母是慈爱而善良的。如果联邦宪法允许该州把“代替决定权”授予什么人的话,这对夫妇当然最符合资格。但是,程序公正法不允许把任何这样的权利授予别人除非是南茜本人。病人的亲属是会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他们不希望目睹他们所爱的人延续一种没有希望的、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屈辱的生活--这种感情没有什么不光彩,也不是毫无价值,但这并不能说明亲属的观点与病人本人的观点绝对一致--如果我们假设病人能够在健康的时候就预见了处于“植物人”状况的前景的话。因此,密苏里州可以尊重家属的意愿但不能把决定权交给他们。 综上所述,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判决。 (三)异议 (大法官布雷兰、大法官马歇尔和大法官布莱克曼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反对意见) “医学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制造出了维持生命的模糊区域--当死亡开始时,生命却在以某种形式延续。然而,一些病人并不希望他们的生命靠药物来维持。他们宁愿按照自然规律尊严地死去”. 引自弗莱明案:Rasmussen v. Fleming, 154 Ariz.207,211,741 P.2d 674,678 (1987) 南茜·克鲁塞处在这样的区域已经6年了。她不能感觉周围的一切,而且以后也不能。她的身体无意识地、生理反射地抽搐着,脑部那片曾经思考、感受的区域现在已经迅速衰退并且还将继续衰退下去。病变留下来的空洞填满了脑积水液体。“大脑皮层的萎缩是不可改变的、永远的、在恶化的、将继续下去的。" “南茜再也不能和她周围的环境做有意义的交流。她将永远成为植物人直到她死。”她不能吞咽,只能通过一根置入胃里的软管得到营养物和水。 南茜在事发时已经是成年人,事前表达过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不想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意愿,她的家人和朋友也相信她会那样做。但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却判定这样的植物人病人必须在药物的维持之下过一种被动的、囚犯一样的生活,对南茜来说,这种生活或许会持续30年。 南茜有拒绝人工维持生命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没有影响国家利益。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不适当的、带有偏见的程序上的障碍阻挠了这个权利,南茜·克鲁塞有权利选择尊严地死去。 (1)决定死亡的时间--曾经由命运决定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由人类自己选择。在每年死亡的两百万人中,有80%死于医院和长期护理院,其中70%的人是在决定终止维持生命治疗后死亡。几乎每一例死亡都涉及到是否采取一些医疗措施延长死亡过程的问题。这样的决定是困难而个人化的。他们必须根据个人对生命价值的判断作出决定,要有医学上的可行性,还必须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之下。而法院应该做的就是定义那个框架并判定政府是否参与这些决定,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摆在联邦最高法院面前的问题是相当清楚的:程序公正法条款是否允许密苏里州要求一个现在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去提供一个严格的、清楚的、令人信服的、表示愿意结束治疗的证据,而不管病人以前所表达过的意愿。如果基本权利有争议,密苏里州对死亡决定权的控制也应该按以前实施过的标准受到严格审查。在本案中,拒绝治疗是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这并不能使受普通法保护的、由自己决定是否治疗的权利无效。南茜虽然成了无行为能力人,但不能被剥夺其可以自由选择死亡的基本权利。 (2)拒绝药物治疗的权利是这样一种权利:某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预先估计继续治疗可能有的好处和拒绝治疗带来的后果,然后作出决定。而对南茜这样的病人来说,继续治疗的惟一好处就是保持躯体的新陈代谢,无论人工饲养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药物治疗都不能治愈或改善她目前的状况。植物人病人毫无思想、情感和知觉,并且永远地、完全地失去了意识。院长委员会院长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当初在同意撤除植物人医疗设备时曾指出:“治疗的目的在于保护生命、减轻痛苦、避免伤残、最大限度地恢复身体的有效功能,使病人能从中受益。但是,如果某种疾病的后果是病人永远的无意识,那么,继续治疗就不会使病人得到任何好处。他们感觉不到痛苦、欢乐、满意和愉快,伤残就是他们的全部,他们再也不能恢复哪怕最小限度的人类或社会功能。”而且,另一些理由也说明了为什么像南茜这样状况的人可以选择拒绝人工维持生命。死亡是深邃的,并且完全是个体的事情。对多数人来说,屈辱的、被腐烂浸泡的死亡结局是非常可恶的,每个人都希望死得宁静、骄傲、躯体完整。 尽管拒绝治疗的权利像其他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一样不是绝对的,但国家利益也不能超过南茜这个个体的权益。无论在维持治疗的判决中密苏里州得到了什么好处,坚持维持治疗对南茜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她本人确实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作为一个整体,该州不会从南茜的治疗中得到好处:既没有一个第三方的处境会得到改善,也没有一个对其他人的伤害会得以避免。在这里,州所宣称的惟一的国家利益是保护生命的普遍权益。然而没有哪个州的关于生活的普遍权益可以从具体过这种生活的人的个人权益中完全抽象出来,更不能由此排除个人的(譬如拒绝治疗)的选择。因此,州的普遍权益必须让位于南茜个人的关于药物治疗的自我抉择。 而且,密苏里州对决定权的控制还会损害而不是有利于州的保护生命的权益。为了拯救生命,当代医学尽可能利用各种医疗手段,哪怕病人还存在一丝康复的机会,这样就使医院可以使用一些现在会对病人有好处,但后来证明没有好处而可以被停止使用的手段。1982年院长委员会在同意撤除植物人医疗设备时解释说:“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出现了:当医护人员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医疗措施在以后撤销起来很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害怕采取一些尽可能的措施以拯救生命。因为这些措施相当有可能对病人没有一点好处,相反成为极大的负担。”新泽西州某法院也认为,家人和医生可能由于担心以后不能撤销一些维持生命的、尝试性的治疗而草率地、过早地让病人死亡。 (3)这里并不是说州就没有合法的权利。多数人认为,密苏里州的一个基本权利就是尽可能使南茜能够在这样的植物人状态下正确实施自己的个人权利。如果南茜想继续治疗,州就可以合法地提供治疗。但在南茜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州的权利只是确保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这里,“正确性”显然是关键。密苏里州作出一些程序上的规定以加强南茜决定的正确性,或者至少与正确性相一致,这是符合宪法的。但州最高法院所支持的“安全屏障”却不符合正确性的标准,因为在本案中,密苏里州法院显然规定了一个显失公平的证据上的要求:申请终止植物人治疗的一方(通常是病人亲属)必须提供病人在健康时特意对该有可能的植物人状况作出的书面陈述作为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还得清楚而令人信服,同时又并不要求认为应该维持治疗的一方提供证据。 除了过于严苛的证据标准,密苏里州法院还绝对排除了相当多的证据,这些证据完全不需要所谓的精确性就可以成立。我们注意到,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州法院维持治疗的判决,但它却要求南茜一方提供终止治疗的清楚的、令人可信的、连贯可靠的证据。法院没有考虑南茜曾经对其家人和亲密朋友所做的陈述,也不考虑南茜的母亲和妹妹肯定南茜不想维持植物人状况的证言--哪怕在知道南茜的家人是仁爱和没有恶意之后。法院并没有特意规定什么样的证据才是清楚而令人可信的,从它的结论来看,它只能是指活人的遗嘱或正式的指令。然而,由于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是如此的小,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立一个正式遗嘱的迫切性,还有一些人也不愿意去想他们身体的衰退与死亡问题。即使那些下决心要立下遗嘱避免发生类似南茜情况的人仍然需要知道一些有关如何立以及如何实施活人遗嘱的问题,他们需要法律援助。 (4)在美国,多达10, 000人正生活在植物人状态中,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大幅度增加。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停止呼吸的人复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完全康复。20多年前,不能吞咽或消化食物的人会死去,静脉注射卡路里也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而现在,各种形式的人工饲喂发展到可以延续人们的新陈代谢几年甚至几十年。除此之外,慢性病或衰退性疾病代替了传染性疾病,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80%死在医院的美国人都有可能“在一种服用了镇静剂的昏迷状态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他们的鼻孔、腹部和静脉都插满了管子,更像一个被操纵的物体而不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有1/5活到80岁的人在死之前都将遭受不断增加的精神失常的折磨。 “现代医学的奇迹给了很多我们以前意想不到的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法律、平等和公正决不能感到害怕和无助。" 引自昆兰案:见本书第30页。新的医学技术可以医治那些几十年前可能死亡的病人,使他们重新康复。但医学却不能医治象南茜这样患有消耗性病症、无法痊愈的病人,等待他们的是死亡的命运。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州政府不能没收受害者这片躯体、情感和记忆的荒芜土地,宪法也不允许去征用它们,不存在类似“父母官”这样一种使州政府能够非常自信地去统治的借口。在长达几年的调查之后,院长委员会得出结论: “当人们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作出判断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领域能够像判断死亡那样多样化和绝对的个人化。例如,对某些人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另一些人来讲,没有精神欲望和身体能力的生命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是负担。同样,适当的痛苦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个人成长和宗教体验的方式,但对另一种人就是恐惧和绝望。" 在本案中,密苏里州法院代替南茜去作关于她死亡的判断。法院抛弃了她的意愿,忽略了她的价值,剥夺了她尽可能自我作出决定的权利。他们的做法很不坦率,并且擅自利用了她的名义,尽管是出于关心。就像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几十年前曾告诫过我们的一样:“经验告诉我们要学会在政府善意的意图之下保护自己的自由……自由最大的危险潜伏在人们的热情及那些我们都不明白的美好的意义之中,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对自由的侵犯。" 因此,我们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反对。 (NANCY CRUZAN v. DIRECTOR,MISSOURI DEPT. OF HEALTH)(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90)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法律出版社系列丛书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