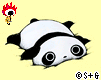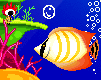| 约西亚儿童虐待案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08/06 18:17 法律出版社 | |
|
(一)案例简介 案由:起诉人是一位被其父亲毒打并造成永久性伤害的男孩。被告是该区社工和地方官员。起诉人指控曾向被告申诉受父亲虐待并有确切事实,但被告却没有采取措施取消其父的监护权,从而剥夺了起诉人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程序公正法条款。 初审判决:地区法院审前裁定被告无罪。 终审判决:原告不服上诉。第七巡回上诉庭维持地区法院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终审仍然维持判决。但最高法院的判决引起了较大争议。 (二)终审判决书 (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由首席大法官雷昆斯特呈递)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案件。约西亚·迪莎利出生于1979年。1980年,约西亚父母离婚,怀俄明州法院把监护权判给了他的父亲兰迪·迪莎利。此后不久,父亲就带着婴儿搬到了威斯康星州温内贝戈县的尼那城。在那里,他第二次结婚又第二次离婚。 温内贝戈法院首次知道约西亚·迪莎利被虐待是1982年1月,兰迪的第二任妻子在他们离婚的时候向警察证实,他“毒打男孩使其伤痕累累,是对孩子的虐待。”温内贝戈县社会工作部温内贝戈县社会工作部:the Winnebago Coun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DSS的工作人员与孩子父亲面谈,但他否认了这项指控,DSS也没有深究。1983年1月,约西亚因多处青肿和擦伤被送往医院,负责检查的医生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并立即通知了DSS, DSS马上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儿童保护组:Child protection Team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DSS负责该案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决定推荐几种保护约西亚的方法,包括让约西亚进学前班,给他父亲提供一定的心理咨询服务,鼓励他父亲的女朋友搬出来住等等。兰迪·迪莎利也自愿与DSS签下协议承诺与他们合作。 由于有“儿童保护组” 的建议,少年法庭撤销了这个案子,把约西亚交还给他的父亲。1个月以后,急救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DSS说怀疑约西亚再次受其父毒打。DSS负责此案的人员认为这不大可能。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DSS 工作人员每月到约西亚家探访一次,在这期间她发现约西亚的头部有些可疑的伤痕;她也注意到约西亚被送进了学校而他父亲的女朋友并没有搬出来住。这位工作人员在她的案卷里如实地记录了这些迹象,包括她怀疑有人在约西亚家里对其进行身体上的虐待等,但她没有做更多的事。1983年11月,急救室再次通知DSS约西亚又受伤了,他们肯定这是由于虐待引起。DSS工作人员又探访了约西亚家2次,但均被告之约西亚生病了不能见她。DSS 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1984年3月,兰迪·迪莎利暴力毒打4岁的约西亚使其陷入威胁生命的昏迷。急救室脑外科大夫诊断说长期的脑外伤引起孩子脑部大面积出血。约西亚没有死,但由于脑部受到严重伤害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有可能在医院度过余生。兰迪·迪莎利被法庭判决犯有虐待儿童罪。 约西亚及其母亲向威斯康星州东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温内贝戈县及其社会服务部以及该部员工没有按照程序公正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约西亚免受其父亲的暴力虐待--他们知道并且应该知道约西亚正在遭受虐待--从而剥夺了他的自由,侵犯了他的权利。 地区法院审前裁定被告无罪。原告提出上诉,第七巡回上诉庭维持地区法院判决。联邦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决。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程序公正法条款规定:“不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各州不得剥夺任何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上诉人认为,该州在约西亚受父亲虐待时没有提供足够的保护从而剥夺了其“个人安全不得受到不公正侵犯”的权利。但这个申诉不属于程序公正法条款的内容,而是关于(宪法)本质的一种要求;因为上诉人并不认为该州没有给予约西亚适当的程序上的保护,而认为它有责任对处于这种受虐待境况下的约西亚给予绝对的无条件的保护。 然而,程序公正法条款并没有在字面上要求州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免受私人的侵犯。条款在对州权利进行限制的同时也没有对公民的安全提供最低保障。它禁止各州非法剥夺个体生命、自由和财产,但从字面上不能推导出各州有责任保证个人的这些权利不会受到其他形式的侵害;它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州的侵犯而不是州去保护人民免于相互侵犯。立法者把政府保护的责任这个问题留到民主政治程序中去规定。 与这些原则相一致,程序公正法没有授予政府援助的权利,即使这种援助在拯救生命、自由、财产时是必须的。如果程序公正法不要求各州为其公民提供特殊保护,那就意味着州不为那些如果提供保护就可以避免的伤害负责。在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认为州不保护个人受私人侵害,这并没有违反程序公正法。 上诉人争辩道:即使程序公正法条款使州可以不对普通公众提供保护,但州对有“特殊关联”的个体还是应该提供保护。在本案中就存在这种情况:该州知道约西亚面临被其父亲虐待的危险,并且又特地从文字和行动上宣称要保护他免遭这种危险,实际上州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保护约西亚--上诉人承认州不是约西亚父亲的同谋--但州却没有强制性地去这样做(保护约西亚)。它的没有尽责是如此“使良知震惊”,实际上已违反了程序公正法条款。 联邦最高法院驳斥了这个论据。确实,宪法规定在某种情况下程序公正法有责任保护一些与州有关系的特殊个体。例如,当州违反某人的意愿使其置于自己的收容监管之下时,就必须相应地承担宪法所规定的保证此人安全和健康的责任。这是因为当州限制某人自由使其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或者不能给自己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如食物、衣服、住所、药物和安全保护时,州就越过了第八修正案和程序公正法所允许的界限。只有当州实施了限制个体自由的行为--如监禁、收容或其他类似行为--时,由于是对自由的剥夺,才可以启动程序公正法条款对个体予以保护,而州的其他行为,如没有保护个体利益等,则不能启动此条款。 与其他人一样,法官和律师也对约西亚深表同情,试图找到一些办法来弥补约西亚所受到的伤害。但情感归情感,我们不得不承认加害于约西亚的不是威斯康星州而是约西亚的父亲。这些州公务员们最可能被指责的是在事情复杂、应该多采取主动的情况下作了旁观者。但他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他们很快取消父亲的监护权,又有可能被指控干涉了父子关系,其法律渊源同样是程序公正法条款。 威斯康星州的人民更宁愿他们的州及其政府官员们在本案这种情况下不要过多采取行动。 维持原判。 (三)异议 (大法官布雷兰、大法官马歇尔和大法官布莱克曼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反对意见) 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州的政府工作人员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当情况发生变化,要求他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却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我认为本案被告只尽了一部分它本应该尽的职责,我相信,宪法本身要求被告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因此,我不认为被告没有责任保护约西亚·迪莎利。 约西亚提出指控最重要的理由是被告的不作为(inaction) ,即被告没有采取行动保护约西亚;同时附带提及了作为(action)的问题,即州对约西亚之类的受虐待孩子的特殊保护条款。本案与其他涉及保护请求的案例惟一的不同之处是威斯康星州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一个旨在保护孩子免遭虐待的条令,法院担心,如果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对约西亚的被虐待负责的话,是不是证明该条令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打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即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威斯康星州到底对象约西亚这样的孩子采取了些什么行动,而不是集中在该州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威斯康星州建立了一个儿童福利体系,专门保护像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威州法律规定各地的社会服务部,如被告(DSS) ,有责任对所知道的虐待儿童事件进行调查。同时,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也有责任报告可能的虐待儿童案件。根据威州法律,各地的社会服务部门应该获取这些报告并进行评估,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甚至当接到虐待儿童案报告的是治安办公室或警察局的时候,也得将报告转给社会服务部,让它们来采取行动;惟一的例外是当举报人对孩子“此刻”的安全感到担忧时,威斯康星才可以直接指令当地的社会服务部,如本案中的被告,采取行动保护孩子免受虐待。 威州的这个规定在本案中得到了体现。因为每次有人报告怀疑约西亚受到了虐待的时候,这些信息都被交给社会部做进一步的调查并采取可能的行动。 因此,根据威州规定,在是否采取行动保护孩子免受虐待的问题上,社会服务部有最终决定权。也就是说,虽然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信息和建议,但只是DSS的人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干涉某个家庭的正常秩序。例如,当约西亚首次因受毒打而去当地医院就诊的时候,正是DSS决定对他进行临时监护并对他的现状进行调查,也正是DSS最后又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不幸的是,DSS的有效干涉到此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公民,甚至一个不在DSS工作的政府官员,都会很自然地认为只要他(她)把孩子受虐待的情况汇报给了DSS就完成任务了。也就是说,威州把采取行动的责任交到了DSS的手上。如果DSS忽略这些虐待儿童的情况,其他的机构就不能弥补。结果是,威州这个儿童保护体系把约西亚这样的孩子牢牢地拴在了那个暴力的家中,直到DSS采取行动将他们解救。因此,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到虐待的孩子的景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州只是“袖手旁观”的说法很明显是掩饰事实。通过州的儿童保护体系,州完全积极地介入了约西亚的生活,这种介入实际上使约西亚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我之所以不赞同最高法院的判决,原因在于它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的“作为”比“不作为”会更加糟糕,当州承担了某种重要责任又不履行这种责任的时候,就会产生专制政治。程序公正条款到这里被解释为:州有权利保护个体,它也承诺去这样做,但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它却可以耸耸肩膀溜之大吉。我认为我们的宪法不允许这样做。 这次,最高法院决意要做一个冷漠的古董,不为“自然的同情心”所动。这种虚伪使它陷入了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使它看不到摆在面前的事实,也不知道应该运用什么法律原则。就像大法官Brennan所指出的那样,事实是,州不是消极地旁观,而是主动地介入了约西亚的生活--正是这个介入使州有责任在约西亚遇到危险的时候给予救助。 最高法院不承认州有这样的责任,因为它试图在“作为”和“不作为”之间划出一条呆板的界限。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推理不符合第十四修正案的条款。我认为这些条款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消除形式主义的法律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在(内)战前深深影响了司法界,已故的罗伯特·卡威尔教授在他的名著《正义被指控》《正义被指控》:见Robert Cover, Justice Accused,1975中对这个问题曾做过详尽分析。 与(内)战前的那些拒绝释放黑奴的法官一样,如今最高法院也声称它的判决无论如何粗糙,总是基于一定的法律条文。但是,本案的问题很复杂,对第十四修正案的理解可宽可窄,就看你如何选择。我宁愿选择“同情心”,这更符合我们对“正义”的理解,而且,法律不一定非得排除情感。如果我们向前跨一步,我们也许会犯错误,但如果什么都不作则会犯更大的错误。道德意识是我们行为的前提。我们一直生活在不确定中,直到我们变成真正的人性的人;我们将挣扎、奋斗,在此过程中,情感是惟一的指引和安慰。 可怜的约西亚!一个受尽其父亲暴力摧残的受害者,一个被社会服务部门抛弃的孩子。被告把这个孩子置于一种危险的处境之中,他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却听之任之,除了“负责任地在卷宗里记录下这些事件。”这是美国人民的悲哀,我们的宪法是如此充满爱国主义,如此为“人人拥有自由和正义”而骄傲,但这个孩子,约西亚,却无端地被正义所抛弃。约西亚和他的母亲,完全有理由寻求宪法的保护,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驳回了这个合理请求。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表示反对。(JOSHUA DESHANEY v. WINNEBAGO DOUNTY DEPT. OF SOCIAL SERVICES) |
| 新浪首页 > 新浪教育 > 法律出版社系列丛书 > 正文 |
|
| 新 闻 查 询 |
|
|
| 热 点 专 题 | ||||
| ||||
|
文化教育意见反馈留言板电话:010-62630930-5178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