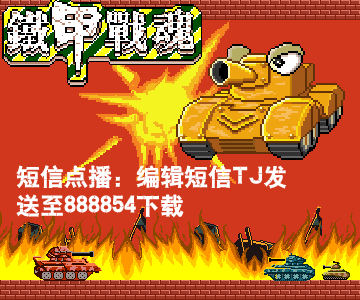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
本文载于《北大未名》2003年7月25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 邓 峰
北京大学2003年所推出的人事制度改革,似乎违背了中国历来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先干后说”的惯例,在全校教职工展开的大讨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局内局外,海内海外,争议、辩论甚至有欠缺理智者上升到人身攻击的谩骂。不辩不能明理,毫无疑问,尽管是改革,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了再说,甚至是不声不响地就制定了新规矩的做法相比,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嗅出,这种争取舆论的做法和明辨的精神还是继承了北大一贯的民主传统。
讨论焦点也日益收敛,这其中涉及到众多的法律问题。在各方祭起“法律”这个番天印的时候,猛然间发现,这场改革的争论,恰恰折射出中国法律和法学思想中若干问题。这倒使我颇有感触,信手“敲”来,并非想论证什么,只是把这场争论中的诸多法学问题,作一梳理和印证,以就教于方家(用BBS上的术语来说,欢迎拍砖)。
一、 变法还是改革:法律背后的合宪性
这场改革合不合法?这个命题可以进一步引申:改革合不合法?所有的改革似乎都是对现状的突破,我们用“变法”来形容大规模的改革。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是改革还是变法?
变法总是有目标、宗旨、依据、对现实的判断的,这种依据是什么?变法之后,要求的是什么法?从一种状态跳跃、转轨到另一种状态,如果都是采用规则,还可以再追问下去,什么是法?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尽管法学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可证实的立法历史有5000年,明确的法学理论可以从亚里士多德起算),但法律是什么很显然是法学中的最具有争议的问题。
既有的教师制度是不是有法律?在这场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是否符合法律的争论中,毫无疑问,成文法中并不存在着明确依据。依据《高等教育法》,实行聘任制度已经存在着法律依据,这已经意味着教师工作并非终身制度,但规则是抽象的,实施和运作则是具体的,高校的治理之复杂,党政关系、聘任关系,甚至还存在行政级别,诸多制度性要素限制着可以实施的选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些实施、运作则都是无形的,没有形成具体的书面规则约束的。我们不禁要问:仅仅是书面上的规则是法律吗?
很不幸,似乎在这场讨论中,无论是法律学者,或者是非专业的法律学者,批评的意见中,都拘泥于《劳动法》、《高等教育法》、《民法通则》甚至《工会法》等已有的书面法律规则来作出解释。其实,首先我们应当问的是,什么是法?既有的规则是不是法?如果是法,那么改革就成了变法;如果不是法,改革衍生于法律条文的空白,现行规则的缝隙。没有法律的依据,究竟是意味着禁止还是授权?
既有的规则是不是法?这个问题难以让我们回答。具文法意味着只有国家制定的才是法,为什么国家就一定会制定地更好,更合适?国家可不可以变法?可不可以改革?如果由此推论,除非宪法修改,否则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不能实施?理念和规矩在先,还是现实在先?
如果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国家制定的法才是法律,是因为国家是最天然的垄断性的权威。这种权威保证了国法的效力、规则来源的正当性。不过,国法和权威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国会通过法律程序认可的;日本向中国的“进入”,是来自最高权威——天皇的授权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平地何故起风波”这种在中国只能算是打油诗的所谓俳句成了侵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美国向伊拉克的“解放”,是在国会的立法下进行的。
显然,法并不等于善法,国家并不等于正当,国家应当受到什么样的约束?立法者应当受到什么样的约束?什么是正当性?这些困扰着我们,也困扰着自古以来的政治体系。
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正是在于权威是不是受到约束,孔子用礼来约束权威,“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孟子直接说,可以推翻暴君,董仲舒说,君王要符合天理,这是所谓的王统。可以说,和韩非、商鞅这些人不同,儒家始终在找一把倚天剑,从这个意义上,法家位于儒家之次,恰恰在于它缺少一个约束君主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君主也是受到道德的约束的。
这种对君主、权威、法律的约束,用现代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合宪性(legitimacy),也被翻译为合法性。究竟是翻译为前者好,还是后者好,在许多学者眼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符合宪政,还是符合法律?两者是不是有区别,和我们上面所探讨的是一致的。合乎宪法,合乎宪政,合乎法律,合乎正义?这些词语的背后,恰恰是我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如果法律规则不好,要不要改?合宪性说白了,就是法律必须符合正义。它是对法律的约束,是对权威者的约束。
因此,理解什么是合宪性,就要回答: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而这常常被一些人所遗忘。恶法为什么得不到遵守?遵守法律,并不是因为某个政权、某个权威天然是正当的,而是在于大家遵守它,可以得到加总的社会利益最大化,更准确地表述是“公共利益”。法律避免了人和人之间行为失度、报复、纠纷的悬而不决,最重要的是,它制约了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为的可预期程度。
在康德传统中,法律被视为是道德的形而上学;在边沁传统中,法律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无论是采用那个制度,法律的价值是输入的,所以它离不开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很明显。“依法治X”的背后,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就会流于空文,成为暴政的工具。缺乏了正确标准的法律,就会变成“苛政”和“恶法”。孔子从“仁”(人和人)出发,将长期进化带来效率的道德形成礼,输入法律,后来的儒家学者即“援礼入法”,形成中国的特色法律;而20世纪以来,庞德(Roscue Pound)将社会利益引入法律,逐步将法律的效率价值突出出来。这些都是对的,不同的合宪性的解释。
当甘阳先生洋洋洒洒、天马行空地在阐述制定《大学改革法》的必要性和先验性的时候,似乎忘记了,制定这样的法律是什么,甚至忘记了法律是什么。“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规定一方面由于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因而是根本“不合法的”,另一方面这些规定与西方同类情况的处理方法相比较则是极端“不合理的”(甘阳:《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前半句的论调,和《没事偷着乐》中的那个试图违约的房地产公司伙计讲的没什么区别,“你懂什么是法治吗?不服就拿法治你”;而后半句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更是体现了“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思想,为什么前半句的情况不和西方同类情况相比呢?
哪个西方国家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不合法呢?很显然,这句话应当翻译一下,“没有法律根据,我反对,所以你是不合法的。”后半句就更有问题,什么是极端不合理的,那么,现在的体制是合理的吗——和西方同类情况的处理方法相比?
甘阳对法律的理解更是危险的。法律首先是对权力的制约,对权利的保护,而不是对强权的维护和权利的限制。如果制定了一部乱七八糟的《大学改革法》,就可以执行下来吗?如果换了希特勒来制定法律,改革就有依据吗?
法律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少数人执行于多数人的。因此,如果丧失了合宪性,人们不愿意遵守它,少数人是不可能反对多数人的,历代的起义、夺权、朝代更替就是一个选择,这是一种变相的“用手投票”,只是形式激烈一些罢了。当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时候,秦王朝已经丧失了合宪性。而当众多的人冒着被“蛇头”痛宰、外国警察“遣送回国”,忍受签证官的无理刁难而更换一个国籍的时候,则是在行使对法律的“用脚投票”权。“法出于仁,成于义”(苏轼:《王振大理少卿》),缺乏正义、效率、自由的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使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的法律也是得不到遵守的,这就是合宪性和服从的关系。前者是法律的输入,后者是法律的产出,有了垄断权威制定的规则,并不意味着就是合理的。
法律是保守的,是对既存利益的认定和保护,法律也不是泥古的,变法从来是历史中的常见之事。“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修宪、司法解释、判例的收缩与扩张,都是寻找和人们的追求相适应的手段。什么是不变的?美国的立法和变法速度毫不逊于任何国家。那些名垂青史的大法官,并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什么新的规则,而是在于他们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推行新的价值。随便举个例子吧,达特茅斯学院案,被认为是树立起合同自由的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最近被学者们发现,其中充满了院外活动,至少判决的作出过程是不公平的(Kermit. L. Hall, eds, Law, Economy, and The Power of Contract: Maj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但是,没有这个案例,今天广泛深入人心的合同自由可能就要晚很多年才能成为主流;但是,绝对的合同自由,在1912年的lonchor一案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衰落了。法律总是变化的,它取决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道德的需要。
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可以看做是一场改革,如果承认法律仅仅来自于国家的垄断性权威,这时候,法律是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这是一个人的品质立场问题,你不能总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宣称法律没有禁止就是个人的自由,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宣称法律没有允许就是得不到授权。这种双重标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中倒是常见,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不过是正义的幌子下的强权。
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可以被看做是变法,如果承认既有的体制规则也是“法”的话。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如果对现状不满,就要改革,如果对既有的规矩不满,就要变法,无论是变法,还是改革,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合宪性,首先我们要追问、反省、反思的是:现行体制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下去?
二、 组织、投票权和法律的功能
衡量一个组织,其中重要的一个尺度,是产权标准。一个公司,如果股东不愿意去挣钱,有权利维持现状甚至衰落下去;一个人的公司,更不用说,愿意怎么处置就可以怎么处置,送给别人,砸烂牌子,那是个人的自由。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共同同意和另外一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或者进入“友邦”关系,这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只要投票权,或者说最终决策权,掌握在组织的成员手中,那么就可以形成组织的意志。
相反,如果投票权不是掌握在全体成员手中,仅仅是少数人的意志,显然就会出现问题。台湾独立,全民公决投票,可以,如果大陆的所有国民也加进去一起投票,这才体现“一个中国”的意志,如果通过了,说明全体同意你独立。台湾人自己投票,就是少数人的意志,因为“海峡两岸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人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这个整体。
大学也是如此,私立大学,投票权掌握在受托人手中,投票可以罢免和选择校长。北大呢,是谁的北大?
公司要改变主要制度,要根据股东制定的章程规定,看看是属于董事会还是股东会的职权,然后由相应的投票人来投票决定。北大的决策也不例外,也是法人制度,也应当由法人的成员来投票决定,或者根据设立北大时候的章程来决定谁有权作出决策。这也是合理的权力配置方式,也决定着合宪性的强弱。北大很显然是一个公共机构,因为它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养活着的,是国家这个全民的代表来拨款的,它不是“北大人”的“北大”。这一点,常常被讨论者、争论者所忽略。
公司的所有决策如果仅仅是对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有利,而不是对所有者负责,就是我们在公司治理中一直讨论的“内部人控制”,如果内部人悄悄地变成了所有人,就是“非法”的“私有化”,就构成了“侵占”。如果公司的董事作出和自己的利益相关的决策,甚至属于应当“回避”的范畴。因此,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决策权,应当是北大的“股东”来作决定,讨论北
大的改革应当实施与否,必须站在“无利害关系当事人”的立场来探讨,讨论对谁有利不利,应当站在北大的公共利益上来考虑。
一个组织成员的民主决策,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这和合同自由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制度中,要尊重当事人自己的决策,尊重他自己对物品价值的评价,尊重他自己的偏好。但之所以组成组织,就是要解决偏好、评价、价值的冲突问题,让多数人的意志成为全体的意志。因此,组织的决策是根据总体最大化的“卡尔—希克斯标准”的,是改革带来的加总利益大于损失的标准,而不是根据“没有人受到损失”的帕累托标准的。所以说,组织是有公共性的,不过是公共性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受损失的价值评价,只能回到市场中,分散的交易下寻找(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着考虑加总利益的情况,而且越来越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仅考虑某些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仅仅举出某些人的预期应当保护,是违反了组织的民主决策的。民主不是个人自由,民主是形成公共意志的方式。
讨论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关注点不应该是照顾某些人的利益,而应当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应该
是考虑短痛,而是考虑长远利益;不应该是内部人的得失,而是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
北大的民主讨论,应当继续扩大,因为现在还是内部人的讨论,还是内部人的决策,应当让全体人民——我们的股东来发言,让他们投票,这才是合理的决策。我们的判断标准也就自不待言,是不是这场改革,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加总利益。
蒋非非的七论(不知道还有没有八论,九论),恐怕是搞错了投票权的问题,也搞错了判断标准的问题。她在洋洋洒洒地批来批去的时候,忘记了谁是北大的股东,谁才是在这场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应当受益的人。站在内部人的利益来讲话,和私分股东的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用内部人的小圈子利益,替代了组织的长远性利益,这才是阉割,是私有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利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义不过是长远的、整体的利,注重北大的长期利益,长期的信誉,“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苏轼:《道德》),公共的大利益,才是判断改革的标准,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良心。仅仅关注短期的利益损失、阵痛、甚至个别性的不公,而不是注重自我推动改革的收益,这样的人,倒是应当考虑一下,算不算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三、 公共性维度对人的要求:兼论知识分子的公共良心
法律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也是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机制和手段。存在着两个人就会有交易,而存在三个人才能谈得上是法律。三人为众,为公,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保护加总的利益,是处理公共性问题的制度。尽管法律规定了种种规则、细则、标准,然而仍然离不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我们更信任法官,就可以给更大一些他的自由裁量权,相反,则要通过更多的规则、程序、复议、司法监督来纠正他。法官是评判别人是非的,要做到一碗水端平,不偏不倚谓之中,才能是公正的。之所以法律要求法官在判断涉及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采取回避制度,就是这个原因。北大的内部人来讨论怎么改革的时候,就产生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问题。
当作出决策的人,投票的人会产生利益冲突而导致可能决策偏颇的时候,如何形成一个富于“合宪性”,“正义”的决策呢?或者说,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为,达到正义、正当、公平的决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罗尔斯(Rawls)提出了最著名的解决方案:无知之幕。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决策的结果对谁更有利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是最合理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或者说,是一种抽象的方式。
法律中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和仅仅需要为自己着想的人不同,而是需要在社会交往中考虑对方和公共的需要。在罗尔斯的理论之中,对人的假设,是公民的意义上来说,即法律中的理性人(reasonable),而不是采用经济学中的理性人(rational),换言之,个人在无知之幕之中,天然地应当具有公共良心,因此,罗尔斯的理论试图将经济学的整体逻辑一贯性和法学的公共性结合起来。不管罗尔斯的理论是否彻底,显然,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命题。对一个普通人,法律要求他是一个社会的、具有理性的、公共意识的人。“理性的人总是替别人着想,谨慎是他的向导,安全第一是他的生活准则”(转引自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5—456页)。
当社会的整合度越高,所需要判断的事情公共性越强,或者说组织的公共性越强(用经济学的广义概念来说,交易中的公共性越强),对参与主体的公共性要求自然就越强。一个君主的私生活可能都要被法律干预,所以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议论克林顿的绯闻,而一个平民百姓的规避税收都被法院视为合理的,因此,董事让股东承担不必要的税收在法治先进的国家都被认为是董事的不当决策。
确定公共性的概念,除了有些学者所使用的“public reason”,在法律中,则使用“common sense”,即公共良心。亚里士多德将其界定为popular minds。在早期社会中,社会整合度很高,法官可以援引“公共良心的义务”(common calling)来纠正合同中的过高价格,这里的common calling,就是公共良心的呼唤。公共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则是在社团制度之中,组成社团的成员必须合理地、出于善意地行使自己的决策权。而当组织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产生分离的时候,作出决策的人,对所代表或者代理的人更应当出于公心来作出决策。
一个董事不能违反自己的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避免作出和社团利益相冲突的行为和决策。公司法和合同法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诸如宪政、公共管理等领域了。所有这些,都是法律对“理性人”的“公心”的要求。如果丧失了理性人的这一基础,我们就无从讨论社会问题。
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所涌现的诸多争论,许多谩骂、指责、攻击,一些人丧失了最起码的公共良心,或者出于自身利益,或者出于自我满足,而并不考虑北大整体的公共利益。拿起法律的招牌来探讨问题,浑然忘记了法律本身是解决公共性问题的机制,在探讨规则的形成中,连起码的公共良心都扔到爪哇国去了。
这场改革,所涉及到的、参与讨论的、参与决策的,都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吃喝拉撒睡,油盐酱醋茶,这些方面没什么不同。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普通人看“北京新闻”,买《北京晚报》,而知识分子则可能更关心“国际新闻”,看《参考消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更多的公共良心,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公共事务的讨论,公共决策的形成,如果没有公共良心作为基础,要么维持原状,要么实行强权政治,换言之,用集中的权威来替代集体决策。避免独裁专制,首先应当是集体、群体具备公共良心才行。
四、 决策权配置、公共责任和正义观念的变化
北大究竟是谁的北大?是北大人的北大,教育家的北大,还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显然,如果是北大人的北大,就变成了内部人控制;如果是教育家的北大,“唯有德者居之”,北大就和一个国家差不多。作为一个公益社团,显然北大既不属于公司、合伙这种盈利性的组织,也不同于政府机关公共性那么强,而是介于之中。在这个公共性的维度中,北大介于公司和政府机关中间。
公共性程度的增强,首先意味着社团的所有者和决策者分离程度的加大。公共性决定着决策者的独立性,当公司的公共性增强,董事在决策中的不受干预性质就要增强,股东只能通过法律或章程制定的程序和途径来行使其权利。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的独立决策权利要大于一个非上市的有限公司。美国公司法律制度中就存在着“业务判断规则”(business judgement rule),只要董事作出的决策具有商业的合理性,就视为其履行了职责。军队组织尽管存在着严格的纪律,但一旦开战,则指挥官的独立指挥权是必须完整保证的。而最高决策者,无论名称是主席还是总统,其决策的独立性更是强大,所有者(选民)只能在几年内一次性地对他表示赞成还是反对。所以,决策者的独立性意味着决策者的权威增强。
之所以权威在公共性组织内增强,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公共性组织的加强,导致公司的治理模式从“股东所有者”(stockholder)向“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转化。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利害关系人的组织(stakeholder corporation)。在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偏好的异质性(一般认为公司股东的目标是同质的,比如利益最大化),北大的行政管理人员、行政服务人员、教员、学生、社会中的人、教育部的管理者,都对北大存在着不同的期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利害关系人的组织。在这种偏好加总的问题上出现了困难,就需要权威来克服不同的主体偏好加总问题。
北大的改革中,纷纷扰扰之中,不同的偏好冲突如此之明显。然而,北大的貌似“民主”的改革,却违反了北大作为公共性机构的特性,即讨论者主要集中在北大的直接利益者之中,
集中在这场改革中的受益者(受益者也可能还没有出现)和受损者之中。作为一个公共机构,一方面应当让所有者来发言,而不是局限于内部人员;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机构的决策,权威决策者的独立性更应当得到尊重。
作为国立大学,毫无疑问,北大并不是教育家的北大,而是全国人民的北大。否则就是混淆了北大的所有权。教育家不过是全国人民的受托人,北大的管理者,而并不是所有者。
不过,这并不妨碍决策的作出。组织的公共性越强,经理人的权限就相对越独立。北大也是这样子,校长作为决策者,对其决策是非的判断也应当遵循“商业判断规则”,只要校长的决策是有合理依据的。当然,北大并不是一个商业机构,因此北大校长作出决策的责任是一种公共性的责任(accountability)。
教育家也好,经理人也好,其负责的对象是“股东”而不是员工,是所有者而不是雇佣者或者债权人。北大的校长向谁负责?是北大的所有者而不是内部员工。一些愤世嫉俗的人,打着“同情弱者”、“人文精神”、“关怀”等等名义,貌似正义的化身,而浑然忘记了:所有的教师,是北大的雇员,而不是所有者。
公共性程度的增强,也意味着正义观念的变化,或者说“合宪性”理论的变化。改革当然需要符合“合宪性”,不过是更为深刻、更为宽广的正义观念。“正义是一种社会美德——它告诉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关系,相互之间怎样行动才是正当的——因此我们必然希望我们能在正义提出的要求上达成共识,每个人都感到他的合法要求得到了满足。”衡量正义的标准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我们的改革中都找不到合理的标准:诸如平等主义的原则(包括比例的平等和抽象的平等,前者包括按需分配,后者则是现代法律中的身份平等);与时间序列相关的标准(先来先到,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排队);与地位相关的原则(资历、学历、年龄、职位);以权力为基础的原则;根据效率来确定的原则(应得、贡献);混合的原则,等等。这些不同的正义观念搞得我们的讨论混乱不堪,筋疲力尽。
然而,只要存在着集体行为,就会存在着不正义的问题,不可否认,任何制度都会存在问题,但北大显然是既存制度问题更大。在集体行为中,我们的正义标准是什么?这首先要判断我们的组织特性,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形成理性的规则。
基于组织、社区、共同体(community)公共性维度而对正义作出判断,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念。这是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在《社会正义原则》中所提出的。根据组织、社区、群体和共同体的结合紧密程度,或者说公共性维度,可以概括性地分为团结性社群,比如家庭、俱乐部、宗教团体、工作小组、职业协会,其实质正义的原则应当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工具性的联合,比如公司、社团等经济性的关系(当然,家庭也会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实质正义的标准是“应得标准”,即所得与贡献相等;第三种则是公民身份联合体,比如国家、民族的,其分配原则应当是平等,每个人享有平等的地位,这是法律上的平等,所对应的是作为“公民”的主体。
北大改革中的正义标准,首先应当是来判断北大作为组织的公共性程度。如果是北大内部人的北大,我们的正义标准当然应当是按需分配,房子、实验室、办公室乃至于工资、福利、职位,大可以高唱“我重要,我需要,我应得”;如果北大是一个公民身份的联合体,就应当平等,谁也不应当因为学历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是博士还是学士,工作年限长还是短,教学时间多还是少,发表文章的杂志是核心的还是一般的,用的是洋文还是国语……而受到不同的待遇。理由很简单,宪法已经规定了,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公共权利的行使不能因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等受到歧视。
但北大恐怕这两者都算不上,一个大学无论学术品位上怎么高尚,也不过是一个工具性组织。如果这个组织的产出下降,总出次品,为什么要花纳税人的钱来养活呢?何况,中央政府在当今只扶持几个著名大学,北大的经费从平等的角度上已经挤占了其他高校的份额,好钢总不能用在刀背上吧?!
要不要改?要看对得起还是对不起所有者;要不要一部分人走人?要看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将北大办成养老院、敬贤堂(这是我们千金买的马骨),那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应不应当名副其实地先改个名字。
如果一个一流大学的教师升不上教授被解聘而找不到工作,养不活自己和家庭,恐怕更要改,我们怎么培养人才的?如果一个历史系的副教授离开学校找不到工作,历史系还要不要招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那些认为离开了北大,一些人就会玩完的想法,恐怕是在诬蔑我们的人文科学,也低估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眼光,或者说,在这些人的眼中,北大不过是一个孤岛,离开了她,就没有着陆点了。这种眼光仅仅相当于提着手电筒或者探照灯摸黑走路的人,一句话,“竖子不足与谋。”
五、 组织的价值和改革的顺序
行政先改,还是教员先改?这甚至被升华到了“柿子先挑软的捏”的境地。谁是软柿子?可以理解,日益官僚化、程序化的管理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服务态度恶劣诸多弊端也是明显存在的。行政改革也势在必行。但我总觉得,在这场讨论中,倒是行政人员,成了软柿子。
他们没有精力、没有兴趣、没有那么强的“北大主人翁精神”,在讨论会上发言,在辩论会上陈词,在BBS上灌水和骂人。谁来替他们辩解?
在猛烈批评行政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忘了这些人的贡献。有人宣称,北大的贡献都是2000多名教师的,这种腔调,和拍马屁有什么两样?中国的改革都是小平同志的?sars的消灭都是医护人员的功劳?房子都是建筑师盖的?时装都是设计师的灵感?原子弹、氢弹就是邓稼先的?法律上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总是需要因果关系的,这包括两段:没有A,就没有B;有了A;就有了B,必须这两部分都符合,才构成行为和结果的合适连接。有了这2000多名教师,就有了北大?那不用改革,统统开除行政人员是最彻底的。
任何一个组织,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分工,这些分工哪一个重要?在一项合作中,一个人承担99%,一个人承担1%,谁对完成工作更重要?一个人画龙,一个人点睛,谁更重要?
先改谁?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从哪里找?我们首先要问,北大的形象是谁塑造的,北大的魅力是谁创造的?和上一个问题类似,对房子不满,先另找建筑师还是先另找建筑工人?时装卖不出去,先换设计师还是先换裁缝?
那些猛烈批评行政人员的人,似乎忘了,改革并不是将全体北大教员赶出去,将改革的主体换成全称对象,和将行政人员的腐败、浪费、低效率换成全称对象,总是让人想起“阶级论”。
为什么要先改教师队伍?很简单,看看我们每年的招生就行了,多少状元、高考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北大,是冲着谁来的?是行政人员,还是教员?先改行政人员的主张者,所犯错误和前面是一样的,就是忘记了谁才是北大的所有者,谁才是北大的评价者,谁才是北大的希望。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