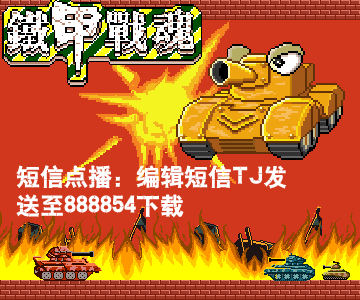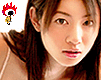记者:你们如何和乡亲们打交道?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最不习惯乡村缓慢的生活节奏,“慢慢来”,成了我们最常听到的词。所有程序必须遵循礼貌的原则。譬如,你只想问路,而对方会说:“等会儿,喝口茶。”总之,大家应当先认识,了解,直到建立起一种友好的感情才能入正题。于是,我们学着先问:“你地里种的是什么?”再问“这玉米长得怎么样?”接着说:“这玉米卖吗?
多少钱一斤?”一来二去熟了,你就可以问:“这附近有旅店吗?”如果没有,就等着对方热情地喊:“来来,在我家里住一晚吧!”
记者:你们付房费吗?
李爱德、马普安:当然,我们每次都给,但对方从来不收。我们只有学老红军,偷偷把钱塞在枕头下面。只有一次在临走前给人家发现了,硬把钱退给了我们。
记者:能说一下你们在野外生活的情况吗?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在野外搭帐篷的时间约占1/10,有时一座大山需要两三天才能翻过,譬如夹金山就用了两天一晚。我们用小煤气罐煮米饭,山上有足够的水。在野外可以吃干粮,印度咖哩蔬菜罐头,加了水就会发起来。我们时刻准备“救生粮”,所以从未饿过肚子。我们往往就地采购吃的,有方便面,面包,饼干,还有豆腐干等。
记者:野外的环境怎么样?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带的净水器没怎么用,因为山间的溪流和瀑布都很干净。但镇上非常脏。河里满是垃圾,人们缺乏环保意识。我们每次翻山越岭,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收集好所有废物。而到了镇上,问人们垃圾筒在那儿?令人惊愕的是,对方往河一指。有时别人答应帮我们扔,谁知还是丢进河里。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遍是一次性泡沫塑料盒,风一吹过,纷纷扬起。
挨村问红军,一程寻访收获多
记者:你们如何寻访老红军的?
李爱德、马普安:每到一处,我们都问:“这儿有人看过红军,参加过长征吗?”村民们就为我们领路。村里人都为这段历史感到骄傲,连孩子都会说:“瞧,这条就是红军走过的路!”对了,孩子容易交流,觉察力强,更感性,而且比父母受过更多的教育。所以,孩子是我们这一路最好的向导和翻译。
记者:你们又如何采访老红军呢?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坐下来,问完问题,就认真倾听。老人们一旦发现我们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就会充满激情地讲起当年的故事。我想正是我们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所以我们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蕴藏深厚感情的资料。我们必须亲走这条路,沿途拜访,这样的收获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电视摄影队无法比拟的。
也许我们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赢得村民的信任。我们是外国人,而他们心中或许还存在着对当年苏联共产国际专家的敬重之情。
记者:能具体谈谈采访的情景吗?
马普安:我们每次采访老红军,半个村的人都会挤来。少说也有一百人。
李爱德:哪里,只有二十多人。
马普安:是吗?至少有五十人。”
李爱德:不,二十多人。
马普安:呵呵,无论如何,这屋子是挤满了,可热闹了。女人抱着孩子,只听到孩子大哭,大人高声聊天,还有好心人不时想当翻译,怕我们听不懂老人说话,这反而使进程变慢。我们在最里面,外面就这么热热闹闹几圈围着。
李爱德:最理想的状态是只有我们和老红军三人,但往往不可能。人太多了,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
记者:会有一些交流障碍吗?
马普安:有些老人耳背了,只能听懂自己家人说话,于是就需要一个家人做翻译。
李爱德: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贵州南部的小村,采访一个家里住过红军的八十岁老婆婆,那时我们有两个翻译。先由老奶奶用传统苗话说出来,再由女儿翻译成现代苗话,最后由孙女儿翻译成普通话。
马普安:还要由我们翻译成英文呢,最后出书时还原成中文。
记者:老人们还能记得以前的事吗?
李爱德、马普安:他们的回忆就像一个钟,我们的问题就像发条,稍微拧动两下,记忆的时钟就能走起来。我们最深的遗憾就是不能拥有更多的时间。
记者:这次长途采访的亮点是什么?
李爱德、马普安:我们全程采访了11位老红军和107位长征见证人。有些老红军受伤留下,就在当地娶妻生子。我们还发现了69岁的熊化芝老人,她很可能就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长征路上出生的女儿。这是当地一个历史学家发现的,他认识这家人,并结合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做这个判断。这里面存在太多巧合了,一样的时间,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收养背景。2001年熊化芝老人知道这个推测时,立刻进了医院,震惊太大了。她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希望她在去世前能获得一个答案。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