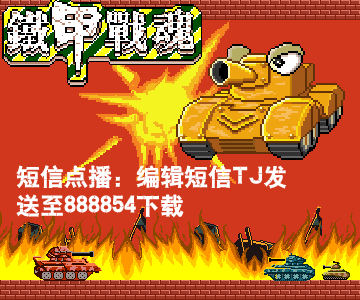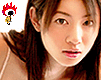总的来说,西方的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将这块山地、山城看成是永恒的,是教徒们得以虔诚不贰的力量的源泉,就是说,只要山存在在那里,他们就会笃信不移,会从这块“圣地”得到无尽的启示。
毫无疑问,在尚无力量揭示自然的秘密、科学处于蒙昧的时代,这种风调雨顺,温和明媚的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富足与快乐使人们以为这是一种超然的力量--一种高于人类
的“神”的存在所至。这个神(上帝与他的儿子基督)代表着庄严、神圣、牢固、有力与永恒,更代表着“希望”。所以这个神是普天下“唯一的父”,主人,服从这个父,向他祈祷,就能实现人们的“希望”。
相比之下,我们华夏的文明发祥于西北高原的黄河中游,自有巢氏至神农氏,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由游猎转为农耕。农耕要靠天吃饭,但是神农氏时代的耕作环境不尽理想--黄河作为中国文化的摇篮,其摇动的幅度与力度都远远地超出栖居其两岸的百姓所能承受的能力。据记载,中国的“防洪的历史可以远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故事”。(1)又据史书上的记载:尧做皇帝时曾“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于是尧帝任用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治了九年都不成,后来被杀了头。到了舜帝时,又有睿水之灾,舜用禹治水,禹在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2)
据水文地理书的记载,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共一千六百余次,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主要是以“夺淮”与“占清”两种形式出现。自公元12世纪起(公元1194年),黄河突然转向东南,夺取淮河的干道,最后流入黄海;这个情况延续了600余年。但是从19世纪中叶,黄河突然改换了兴趣,厌旧喜新,热情澎湃地奔入了北面的大清河而入渤海。这一北一南的河泛荒泽致使我们的辞典上出现了“黄河故道”这个专有名词,那是指海河下游的一个扇形的广大地区。可以这样说,“由于自然地理特点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我国洪涝灾害历来十分频繁,全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其频率和严重程度在世界上是最为突出的。”(3)(当然,不是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经常受到洪水的侵扰的,与中国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南美的巴西等国,埃及的尼罗河等)。
在如此野性十足的母亲河的抚育下,使得我们这些沿河的靠天吃饭、以农耕为生计的诸多省份永无宁日,因而作为中国的历代朝廷都把治水、治黄当成头等正事来做,一个皇帝的政绩常常与治水有关,那有口皆碑的“大禹……过家门不敢入”的好帝王就是一个力证。
由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自古干涸少水,而一旦水来了,又是泥沙俱下、汪洋灭顶式的大灾,久而久之,“水”成了中国文化的图腾;而我们现在所称的上古的“三皇五帝”,无一不同时兼着两个职务,既是酋长,又是巫师;酋长是行政事务,巫师则扮演“与上天感应”的角色。
自古以降,这般的生存环境迫使中国的帝王、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注意水与民生的关系,有很多至理名言都是以水做比,如“民可载舟,亦可复舟”等等。而且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两位思想伟人老子、孔子都是生在这条河的流域,并且正是因为他们自小目睹了这条桀骜不驯的河的威力,也许还亲历了洪水的灾难,所以老子萌生了“道”的思想,他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超自然之力是应该尊崇与效法的,不过这个力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简单、平和的自然--老子是从黄河的浑莽去追索宇宙的博大。孔子则更多地从民生的角度去考虑,面对这般严酷的生存条件,如此频繁的洪灾,他告诉他的学生任何祈祷与迷信都会被下一次袭来的黄浪泥浆击得粉碎;所以孔子的学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还教导他的学生,唯有的希望是老百姓要靠自己,而散沙般的百姓要组织起来,其组织的最小形式应是家庭的团结与互助,这是一个很坚硬的壳。然后才是家庭间的团结与互助,再是村落之间的团结与互助,再后是区域间的合作……直到国家,直达皇帝。孔子的名言“己欲立而立人”(自己先立住,也要帮协别人立住;“而”是然后的意思)--先靠自强,再顾及他人;每个人强了,家庭就强了,家庭强大了,集体就会强大,大家齐心合力就有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总而言之,孔子是把社会秩序的构筑根植于一个严峻的生态环境中的;的确,我们没有耶路撒冷那般的福地,没有山岳的荣光与稳固来启迪我们的心灵。所以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智慧”时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古字“知”与“智”通)--要实实在在地承担起为百姓服务的责任,而敬神最好的方式是与神保持距离!这才可称作“聪明与智慧”。孔子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出了对神的看法--不是我们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帮助不了我们,保护不了我们。是他们(如果存在的话)在与我们保持距离,而不是我们真想疏离他们……孔子的这种敬神而远离神的思想,使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以前得以从尧、舜、禹那种半神半人的“巫术”文化,渐渐地过渡到一种原始的“以人为本”的文化。而到了黄河文明南下的东汉末期,即三国鼎立的魏蜀吴时期,这样的概念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