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蜂一样工作: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调查
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人,占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63.3%。
大学青年教师这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状态呢?本报记者就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态这个话题,对话对外经贸大学廉思和中国人民大学[微博]教授周濂。其中,廉思称这个群体为“工蜂”,他们像工蜂一样,辛勤劳作,从不停歇。廉思和他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五个城市调查了5000多名大学青年教师,分析了全国范围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
对话人物介绍
周濂,浙江人,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微博]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微博]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2009年10月至2010年4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2年4月出版《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廉思,祖籍河北,生于北京,修学经、管、法、政及至博士后出站,下过基层,坐过机关,访学西洋,现在大学任教。近几年推出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等作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和深入探讨,蜚声海内外。
在学术研究和生存压力中挣扎
燕赵都市报:廉思在调查报告中用“工蜂”这个概念形容大学青年教师;现在有许多青年教师也称自己是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周濂:老实说,我既当过“蚁族”,也当过“工蜂”。我是1999年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半地下室租房住了半年,每到周末,不能去办公室,只能留在家里,午后看着阳光慢慢地消失,感觉整个人的生命无所寄托,特别惶惑。
做了三年“蚁族”之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回北京任教。用廉思的话说,就是又做了“工蜂”。
在香港博士生的奖学金是非常高的,我每个月的奖学金是13600块钱。三年博士读完回到北京,我竟然用省下的钱买了一辆汽车,心中还有些得意。2005年11月24日,我正式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一名教师,当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我发现只有1500块钱,这连汽车都养不起。后来我找到学校的教务主任,问为什么只有1500块钱。他说,现在正值寒假,“你放心,过了寒假你的工资就会涨起来。”果不其然,过了寒假,我的工资涨到了2200块钱。
2200块钱对13600块钱是如此大的落差,想起在香港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想到以后的生活会是如此的窘迫。比较香港的三年,与在人大任教的五六年,不可否认,外在物质条件的巨大落差造成了我内心的焦虑不安。
在香港最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可以全力以赴地做自己的论文,以极度专注和高产的状态,每个月可以写一万字到两万字。但是刚回到人大的两三年时间里,我感到了科研以外的巨大压力。这里面有备课的压力,新的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上;有科研的压力;但是更重的是生存的压力。
廉思:周濂老师是我的师兄,我刚入北大的时候,基本工资和周老师也差不多。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许多大学老师刚入职的时候生活十分困难,每年的平均工资以四到六万元为主体。这个群体中许多家庭都是双独(夫妻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买房、买车,他们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很多人的故事是蛮辛酸的。
大学青年教师这个群体的知识储备属于社会的中层,但是他们的收入却在社会的底层。我们发现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发生了倒置。知识分子在这个体制中寻求自己心中的一片净土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个学法律的老师,其他同事在做兼职、培训司法考试等等,唯有他只做科研和教学。他有一个同学在外面做培训老师,因为有事临时去不了,就让他去代课,讲了一次课挣了8000块钱。回来之后这位老师说,以后有这种事情还让我去。他的同学对他说:“你是我们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还有法律理想的人,你要是对命运妥协了,那我们就更没希望了。”
在学术理想和人生价值中踟蹰
燕赵都市报:最近,一位25岁的中科院数学专业博士生与北京市一所中学签约,毕业后将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他的导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学研究所研究员程代展教授在博客上连续发表《昨夜无眠》和《我的反思》两篇文章,表示难以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人才浪费。两位对这件事怎么看?
周濂:这件事我听说了,真实的情况是,中学老师比大学老师待遇好很多。当然应该尊重那位博士生的选择。每个人生在这个世上有自己的责任,像博士毕业生这种天才更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是20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天赋之谓责任》中提出来的。
“天之骄子”这四个字在20年前的大学里是很有分量的,现在再提好像有些笑谈。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就是要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对于这位博士来说,毫无疑问他具有成为一位卓越科学家的天赋,选择去中学教书,虽然会获得更优厚的物质回馈,但就他本人而言,他缺少了很好的机会把天赋发挥到极致。
廉思:我思考更多的是从体制、机制上为什么会造成一个年轻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老师心里,是把知识作为一个最终目的教给学生;而在学生心里,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他觉得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就已经满足了。他需要用这个学位换取更多的利益。
我们在全国做了5400份调查报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我们的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存在着问题。越小的项目越民主,越大的项目越不民主。具体干活的都是博士生、硕士生,却拿不到相应的报酬,而导师都被称作BOSS。为什么学生丧失了对学术的热爱,是目前高等教育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体制教给学生的都是1+1=2的标准答案,却从来不问2等于什么。缺少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宽容、自由的环境。清华大学[微博]的施一公老师说,我们的文化不支持创新,我们从来不鼓励有思想、独立的学生,我们喜欢听话的学生。
当然,中国与西方是有文化落差的,目前进行创新是得不偿失的,去学习西方知识增量很快。现在我们进入了集成创新的阶段,比如说东风汽车、一汽汽车。但当我们的集成创新到达了西方的水平时,就需要原创性的知识了。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原创知识不足,根本问题出在高校里。在美国高校里出现了期刊评比,现在也开始转向专家评比。而中国高校中还在模仿美国的期刊评比,比较发论文的数量、期刊影响因子。
现今高校评价机制难以培养大师
燕赵都市报:当下高校中青年教师的“工蜂”式生存是因为高校中的评价体制吗?
廉思: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一两本有分量的著作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们用这种一年发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衡量,只会制造出一些工匠。
在西方的高校中采取了同行评议,有一个特点是记名投票,如果投票给一个学术水平低的人选上,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把评价权力交给期刊,就必然会造成寻租,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问青年教师,你们认为在科研项目中影响最多的是什么?选择最多的就是人际关系。职称、学校的名气也有些影响。出身于什么门派也很重要,有时候学术圈子也是小圈子。
现在青年教师中还存在一个现象就是重科研、轻教学。教学是一个良心活,没有人进行评价;可是科研却可以进行量化,用最笨最傻的方法来衡量一个人。
周濂:北大的传统是专家评审,梁漱溟、鲁迅都是受益者;如果采取项目评审,或者按照在SSCI、CSSCI发表论文的话,梁漱溟肯定是进不了北大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反省教育、科研的整个制度,它到底是鼓励教师、学生真正地沉淀下来做学术研究,还是在不断地生产各种垃圾。博士生要求毕业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这是十分荒谬的规定。博士研究阶段需要厚积薄发,潜心研究;而且目前的核心期刊总量也无法承载所有的博士生每人在三年里发表两篇论文;这完全是大干猛上、多快好省大跃进思想在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反映。
一篇文章、一本专著更重要的价值不在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而在于它有没有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精神,有没有真正创造一个社会议题,进而实质性地改善一些人的生活。
经历了数年的挣扎后,我现在逐渐摆脱了“工蜂”的那种窘迫的状态。可是我看到不断有新晋职的教师还在苦苦挣扎。在人大,教授每学期要承担8个学分的教学任务、副教授是9个学分,讲师是10个学分。这就造成了越是生存压力大、教学经验不足的教师,承担了越多的教学任务。与此同时,为了晋职,青年教师科研的压力也非常大。而那些年过五旬的教授,没有职称的压力,却有更多发表论文的渠道,所有的资源呈现一个不平等分配的状况。
找到自己的底线并且心存敬畏
燕赵都市报: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一句话写了五六行,怎么也读不懂;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水平不够,就请教我的导师,结果他也看不懂。这其实反映出许多科研人员缺乏严谨的态度,你对现在的科研风气怎么看?
廉思:我们提“工蜂”,契合了现在青年知识分子勤劳的特点。工蜂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知识分子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表达了知识青年对社会的一种影响。
可是在现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现代知识分子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可以按照自身的兴趣爱好思考、写作和发表,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也被分割为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而随着资本的扩张和利益的诱惑,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为稻粱谋”。
周濂:大而化之地讲,现在的科研人员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比如说老师上课,把课程讲得精彩,知识全面,把最新的动态带给学生,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教授写论文不是在制造文字垃圾,而是针对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学生也是这样,上课的时候不刷微博、不玩游戏,这些也是底线。但似乎现在底线的突破非常容易,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老师这样,学生这样,社会也是这样。怎样找到自己的底线并且心存敬畏是一个课题。我们当前社会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有的人都满怀焦虑,不知所往,不知所终,这是最大的问题。高校中的科研风气应当放到这个大环境下来关注。(燕赵都市报驻北京记者 孙磊)
- 武侯外国语学校举办青年教师优质课决赛2012-12-14 15:47
- 六部委:加强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2012-12-13 16:25
- 教育部要求:加强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2012-12-13 15:54
- 大学教师称农村青年娶妻难:劳作4年才担负起2012-11-16 17:00
- 高校青年教师报告引热议 超半数“工蜂”感不公2012-09-18 0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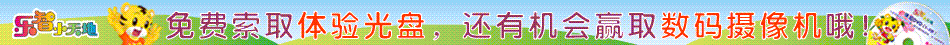


 快速增长3CM秘密
快速增长3CM秘密


